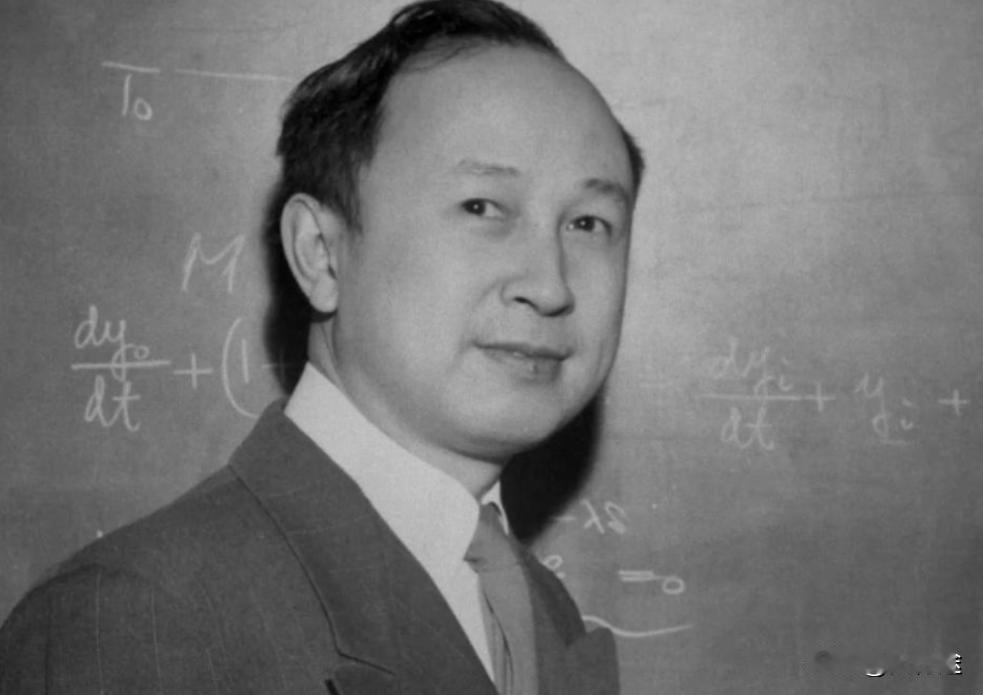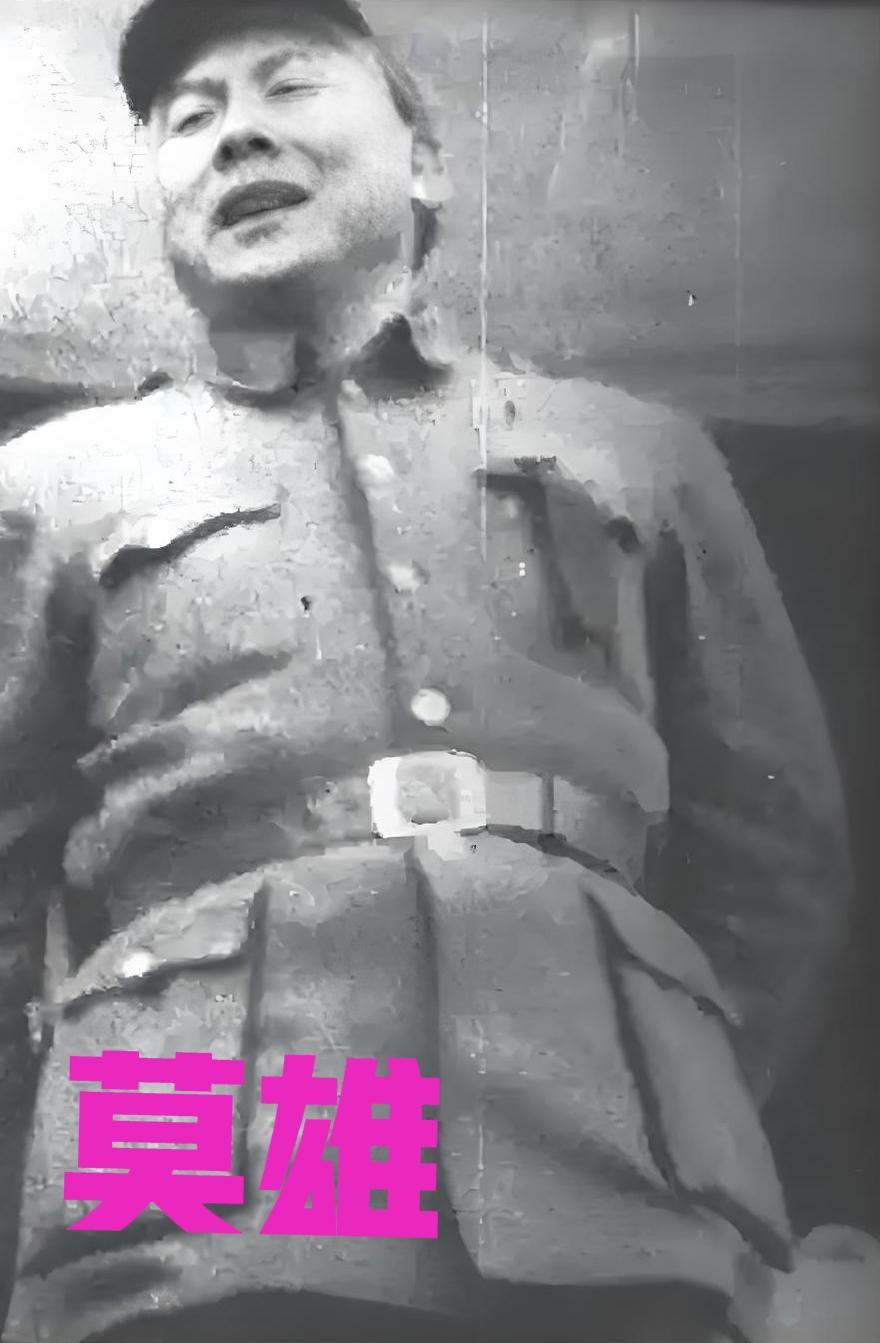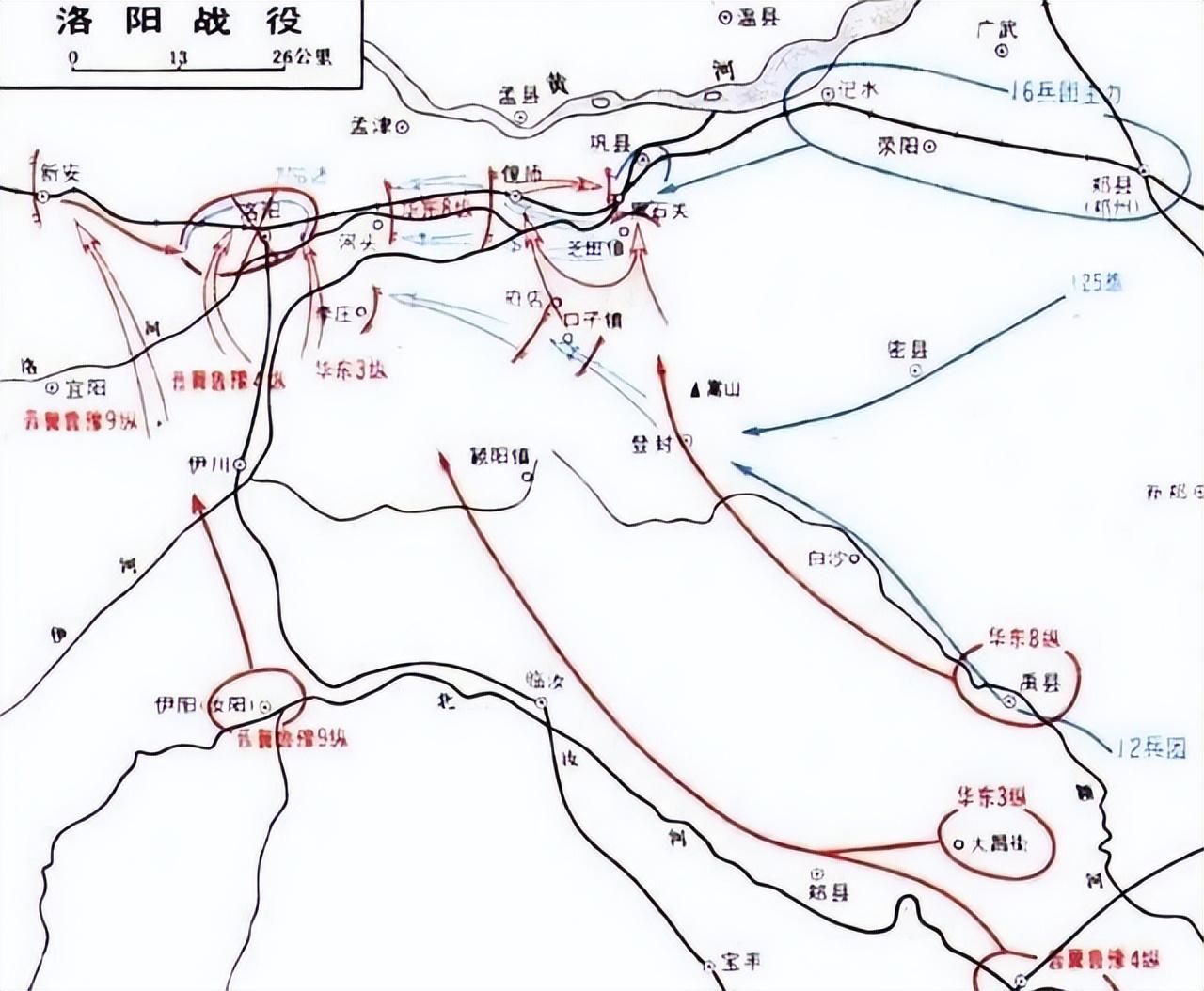1972年,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,谁知,陈春玲红着脸说:“我这病,你娶我就好了!”张援朝父亲听说后,板着脸说:“娶了她,你还能返城吗!” 张援朝记得那年初春,村头的杏花才冒了点粉白的尖儿,地里还是硬邦邦的,锄头下去咣咣响,他从北京来到这个叫红石梁的小地方,路上颠了两天三夜,鞋底粘着黄泥,连眼皮也带着火车的晃,他拎着破布箱站在村口,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觉得风刮得脸疼,肚子也饿得厉害。 那天黄昏,天边红得像烧着,一群人从地里回来,肩上扛着锄头,脚步踩得地皮咚咚响,他站在路边,不知道要去哪,直到春玲从人群里走出来,把他往旁边扯了扯,说那边王婶家炕头空着,他听不清她说的每一个字,但看得出那眼神不冷不热,却也没当他是外人。 最开始的日子,张援朝总是吃不饱,玉米糊糊一碗下肚,撑不到晌午就饿得前胸贴后背,他干活也慢,插秧插得歪歪斜斜,锄地锄出好几个坑,旁人笑他是城里来的绣花枕头,有样儿没用处,春玲没笑,她蹲在地头,把秧苗一根根理顺,分给他最嫩的几把,下工时把自己的饭团掰一半丢进他手里。 有一晚,天上下了雨,连夜的大暴雨,屋顶滴滴答答地漏水,张援朝发了高烧,烧得迷迷糊糊,连水杯都端不稳,醒来时,炕头坐着春玲,她手里捧着一碗姜汤,眼圈红得像刚哭过,衣袖还沾了点泥,他没说话,只觉得那姜汤辣得喉咙发烫,却比家里母亲煮的还暖。 春玲做针线活时最安静,眼睛盯着布料,嘴角有一点点笑意,她给他补的衣服,针脚细密得像一条条爬过布上的小虫子,张援朝坐在窗边看她,一边削铅笔一边偷看那根红头绳在她辫梢晃,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安稳感,他没想过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,但那一刻他知道,有些时候心是会偷偷认下一个人的。 公社的夜校开了,春玲也去了,她握笔姿势怪怪的,写“人民”两个字总是缺胳膊少腿,张援朝看不过去,晚上拉着她练字,用玉米芯当笔杆,写得她手上都是墨点,她说她想当记工员,不想一辈子只在锅台和田里转,他点头,心里却像有人敲了一下,觉得这姑娘比他想象中要坚韧得多。 那年春天,春玲病了,她本来就瘦,咳起来像猫叫,一连几个晚上没下炕,张援朝背着她去了公社卫生院,医生说是肺寒,要静养,他守了一夜,看着她睡觉,听见她呼吸里带着哨音,回村那天,他把那本她练字用的旧本子带回来,纸角都卷了,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“春玲”两个字,他把那本子放进自己包里,压在贴身的地方。 张援朝的父亲来信了,说有人托了关系,明年春天可以调回城里进厂,只是千万不能在农村结婚,否则户口就动不了了,他读完信,坐在麦场边发呆,月光照在麦茬上,影子一片一片地晃,他想起母亲给他做的干粮,想起父亲送他上火车时的眼神,心里像打结的麻绳,扯也扯不开。 春玲康复后,常常来找他,说是帮着修理农具,其实只是坐在旁边搓豆角,他们谁也没说那封信的事,但空气里总有些不明不白的东西在发酵,她手上的茧子没少,脸却比前些日子红润了些,她给他带来一篮子豆角,说是早上刚摘的,还带着露水,他接过来,手指碰到她的指尖,心里一跳。 大队开大会那天,说是返城政策有了新指示,知青可以申请优先返城,张援朝的名字在名单上,大家都说他运气好,终于熬出头了,他没笑,也没说要走,他只是在人群里望了一眼站在墙角的春玲,她低头搓着衣角,肩膀不再那么瘦弱,整个人站得笔挺。 春玲没有问他打算,她只是把那块绣着荷花的枕套塞回了箱底,她娘说,别指望城里人会留下来,可她不信,张援朝也没答应什么,只是第二天带着她一起去了地里,种下两亩向日葵,他说等花开了,就收一地黄灿灿的阳光。 那年秋天,向日葵开得特别旺,花盘比脸还大,整片地像泼了金漆,人们说这是好年景,要多收几袋子瓜子,春玲站在花田边,风一吹,辫子甩到肩膀上,她眯眼看着天,说不出话,张援朝站在她旁边,手插在裤兜里,心里踏实得像踩在厚厚的麦秸上。 后来村里换了队长,知青有的回了城,有的留下盖房娶妻,张援朝没说他要去哪,只是隔几天就去镇上写信,也不知寄给谁,他的包里一直压着那本练字的本子,封面已经磨得发白,但他从来没拿出来给人看。 村里人说,春玲后来当上了妇女队长,夜校也继续办着,她教识字,讲化肥使用,连村支书都说这姑娘有点本事,张援朝种的那块地里,年年都种向日葵,花开的时候,总有人来拍照,有人问他怎么种得这么好,他说,光照足,土壤好,还得有人天天照看着。 再后来,有人说他回了城,也有人说他没走,但不管他人在哪,春玲一直住在那间土房子里,窗台上种着几棵蒲公英,她说那是春天第一种会开的花,风一吹,种子就飞出去,落到哪儿都能发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