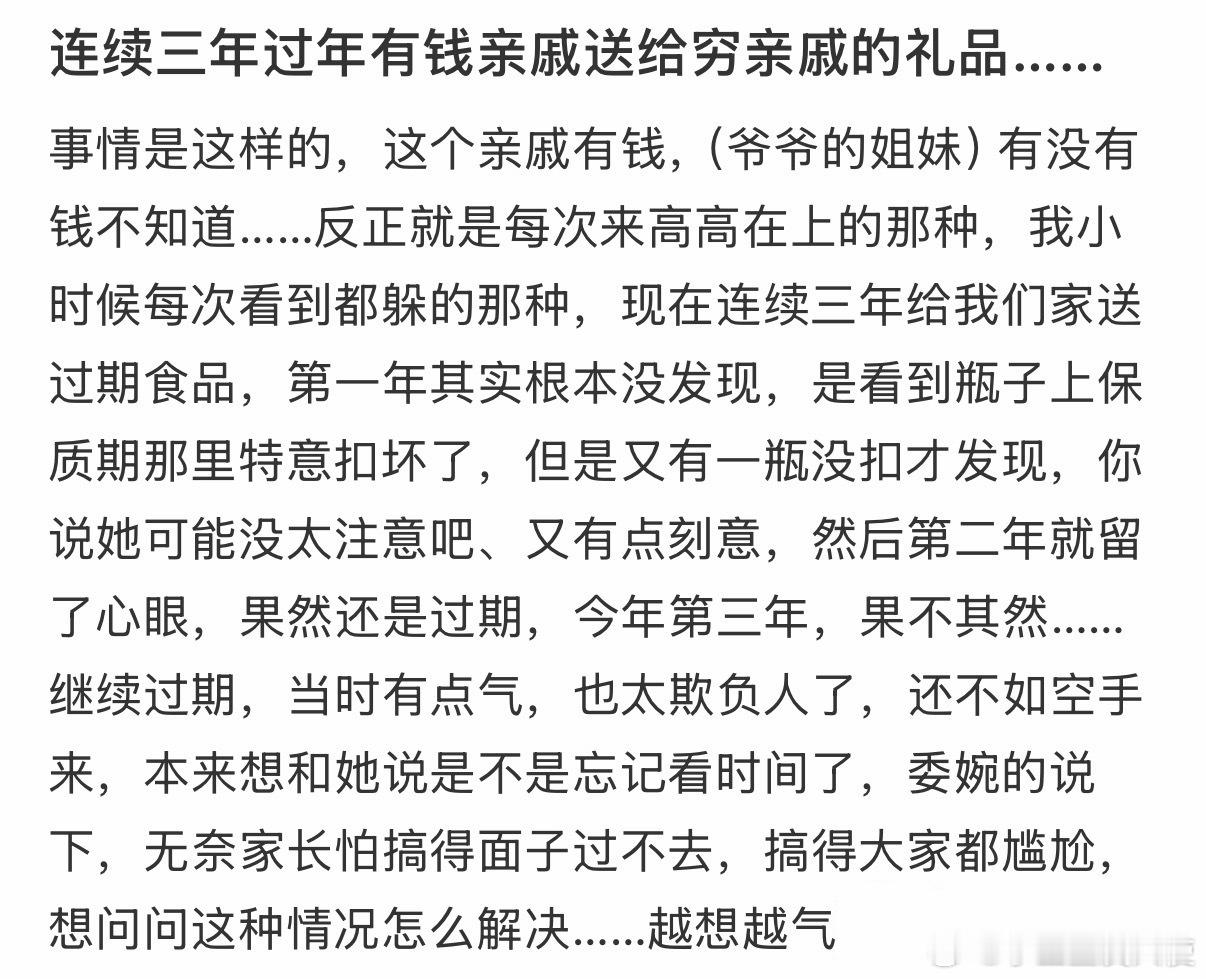回老家过年,红包早已不是小时候那份单纯的欢喜,倒成了一桩沉甸甸的心事。长辈要孝敬,晚辈要打点,一个年过下来,光这红包便能送出好几万。三百是起步价,亲一点的给上千,更有阔绰的,出手便是万儿八千。一年在外辛辛苦苦挣的钱,过一个年,薄薄的红包封出去大半。 这时候便不由想起广东来。听那边的朋友说,广东人过年也发红包,叫“利是”,讲究的是个意头。见面道声恭喜,递上一个红包,里面装的不过是五块十块,至亲至友也不过百来块。收的人不在意多少,给的人不觉得负担,大家图的是个吉利,是份人情味儿。要说有钱,广东的有钱人还少么?可人家硬是把这红包的风俗,守成了礼仪,守成了温情。 反观我们这边,红包倒像是变了味儿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它成了衡量情分的尺子,成了攀比的由头,甚至成了某些人过年的念想——冲的不是那份问候,是那红包里的数目。不光红包,连人情往来也寡淡了。听说有的人生病住院,酒席去不了,便找人代个情;可等病好了,酒席散了,那代情的钱便再没人提起,仿佛从来没这回事似的。你来我往的礼数,渐渐成了有来无往的交易。 说到底,红包本是情的载体,如今情淡了,红包便只剩个红皮。年还是那个年,只是人与人之间,不知什么时候,隔了薄薄的一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