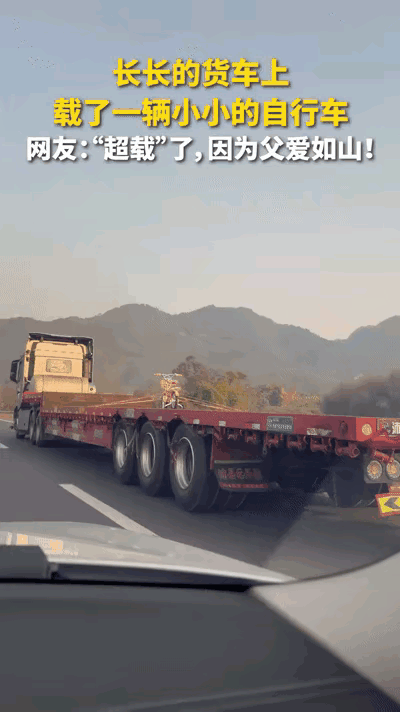她真想一头撞死。被扔进西宁的大仓库里,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来糟蹋她。可是一摸肚子,那里头,是丈夫留下的唯一一点念想,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唯一的骨血,想到这里,她求死的心就暂且放下了…… 说起来,陈淑娥也不是天生就这么能忍的。几年前在四川老家,她还是戏台上那个唱腔清亮、眼波流转的姑娘,十五岁就跟着队伍走了,那时候懂啥叫苦?只觉得穿军装威风,姐妹们在一起热闹 。后来碰上了孙玉清,堂堂军长,在她面前却像个毛头小子,说话都磕巴。肚子里揣上娃那会儿,孙玉清还摸着后脑勺乐:“等打了胜仗,咱就办个像样的婚礼。” 哪知道这一仗,把人打没了,把天也打塌了。 1937年的西宁,那个大仓库里关着的女人不止她一个。有的受不了折磨,一头撞在墙上,当场就没了气儿;有的被糟蹋完,疯了,成天光着身子傻笑。陈淑娥不一样,她变得特别“听话”。不哭不闹,让干啥干啥,眼珠子却天天转悠,不是为了跑,是为了活着。她心里明镜似的:要是现在死了,孙玉清这一脉就彻底断了,那男人在世上连块碑都不会有 。有人说她软骨头,她也不辩,晚上摸着肚子,觉着里头那小东西踹一脚,就觉得这屈辱还能再扛一天。 后来马家军里有个叫牟文斌的参谋,看她长得周正又“老实”,把她弄回家里当小老婆 。陈淑娥没得选,也没法选。那几年过的什么日子?白天干粗活,晚上被人糟蹋,还得陪着笑脸。她学会了喝酒,学会了说脏话,学会了在那些军阀跟前装傻充愣。有一回,她偷偷给关在隔壁的女红军送吃的,被发现了,牟文斌拿皮带抽她,抽得后背没一块好肉。她咬着牙不喊,心里想的却是:只要不打死我,我就还能救一个,还能保住肚子里的娃 。 腊月二十,孩子生在土炕上,是个带把的。她刚抱了一下,还没来得及哭两声,人就闯进来把孩子抢走了 。那一刻陈淑娥像疯了一样扑上去,被一脚踹开。后来她才知道,孩子被送给了姓刘的人家,改名刘龙。她没去认,也不敢认,一个当小妾的妈,认了也是让孩子跟着丢人。 1949年,马步芳跑了,马元海也跑了,陈淑娥被扔下了 。那时候她才三十出头,头发却白了大半。她不回四川,就留在兰州,在纸壳厂叠纸盒子,一个月挣十几块钱 。下班了就去打听,谁家有个腊月二十生的孩子?谁家姓刘?问了好几年,问到人家都烦了,骂她神经病。 好不容易找到刘龙,孩子都七岁了,见了她直往后躲。她不怪孩子,怪自己命硬。那些年,娘俩过得苦,刘龙因为她的“历史问题”上不了大学,只能打零工 。陈淑娥不说啥,就是拼命干活,攒钱,想着有朝一日能给孩子挣个名分。 1983年,王定国来了 。俩人抱头哭了一场,当年那个在舞台上唱歌的小姑娘,如今都是满脸褶子的老太太了。王定国回去就给中央写信,找伍修权、找李先念签字,生生把一桩几十年的冤案翻了过来 。陈淑娥拿到烈士家属证那天,手抖得厉害,眼泪把纸都洇湿了。她说:“玉清,你看见没?咱儿子,咱孙子,往后能挺直腰杆了。” 2005年,陈淑娥在兰州走了,九十多岁 。听说临走前还念叨着一件事,孙玉清的头颅,当年被马步芳割下来送到南京请功,后来就再没找到 。她说,这辈子啥苦都吃了,啥屈辱都受了,就这一件事,闭不上眼。想想也是,一个女人,用一辈子护住了丈夫的骨血,却到头来也凑不齐丈夫一个全尸。这人世间的事,咋就这么不讲理呢?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