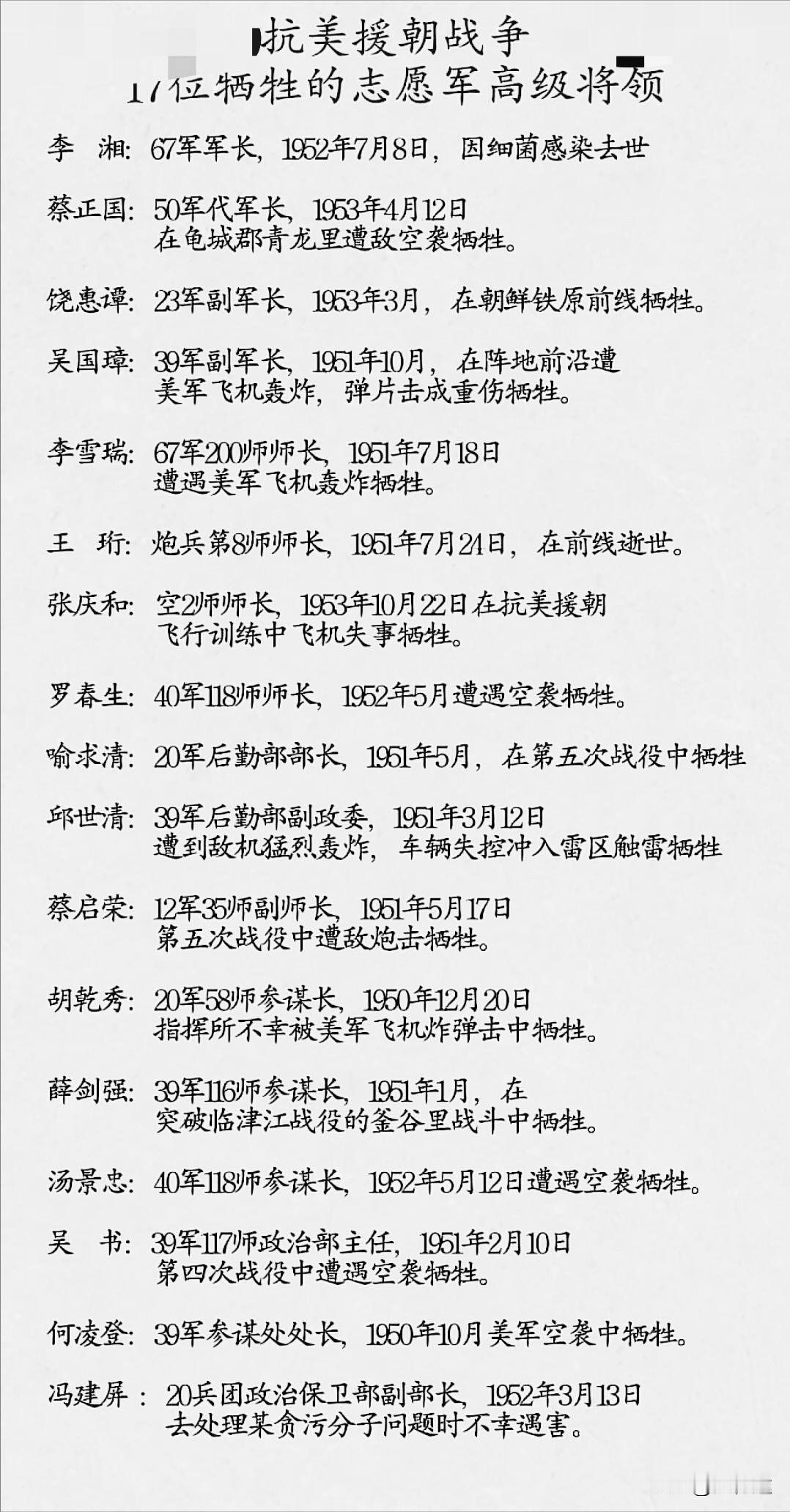1953年10月,朝鲜谷山瓦宇里, 刚立三等功的孙瑞发,和志愿军女战士袁素芬,并肩坐在茅草屋前的砖头上,笑得比阳光还暖——可谁能想到,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现场! 那两块砖头,是战友从废墟里扒拉出来的,还算平整。孙瑞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袁素芬的军装肘部打着补丁,这就是他们的“礼服”。没有红盖头,袁素芬把齐耳短发别到耳后,露出的脖颈被朝鲜的秋阳晒得有些发红。战友们围着他们,口袋里摸出炒面,有个东北兵贡献出珍藏的几块祖国慰问带来的水果糖,就算“喜糖”了。指导员当证婚人,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,最后说:“孙瑞发同志,袁素芬同志,从今天起,你们就是革命夫妻了!要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!”掌声响起来,夹杂着远处隐隐的炮声。 这婚结得急,也有原因。孙瑞发是机枪手,在金城战役里压着敌人打,立了三等功,也挨了弹片。伤不重,但需要休养。袁素芬是卫生员,在师医院工作,孙瑞发送伤员下来时认识的。一来二去,话不多,眼神里有了东西。战地爱情,没时间风花雪月。孙瑞发伤好要归队,归队意味着什么,谁都清楚。那天傍晚,他找到袁素芬,直愣愣地问:“袁同志,要是……要是咱都能活着回去,你愿不愿意跟我过?”袁素芬正给绷带消毒,手停了一下,没抬头:“你现在问这个干啥?”孙瑞发搓着手:“现在不问,我怕没机会了。”袁素芬抬起头,眼睛亮亮的:“那得先打报告。” 报告批得很快。组织上鼓励战士们安心作战,符合条件的婚恋申请,只要政审通过,基本都支持。但条件就那样:一没房子二没床,两人都是军人,各自住集体宿舍。唯一的“新婚福利”,是后勤处特批,把他俩那间当作临时仓库的茅草屋清理出一个小角落,借给他们住三天。屋里堆着麻袋,散发着硝烟和尘土的混合气味。这就是洞房。 三天后,孙瑞发背上枪,回了前沿阵地。袁素芬继续在师医院救护伤员。两人再见,已经是停战以后。1954年,部队分批回国。孙瑞发和袁素芬都在归国名单上,但不在同一趟列车。站台上,人声鼎沸,袁素芬踮着脚在人群里找,终于看见孙瑞发。他跑过来,什么也没说,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她手里。火车开动了,袁素芬打开手帕,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抗美援朝纪念章,还有一小把朝鲜的土。孙瑞发在纸条上写:“功勋章有你一半。土,带回家。” 回家,回哪个家?孙瑞发老家在山东沂蒙山,袁素芬是四川人。按照政策,他们可以选一地安置。两人商量了半宿,决定回山东。孙瑞发是独子,家里有老母亲。袁素芬说:“嫁鸡随鸡,咱回山东。”回到那个贫瘠的山村,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“最可爱的人”。可英雄也要吃饭。孙瑞发把军功章锁进箱子,拿起锄头。袁素芬从卫生员变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,背个药箱,翻山越岭给人看病。 日子苦,但心里踏实。村里人尊重他们,可也有不理解:“在部队立了功,咋不留在城里当干部?”孙瑞发蹲在田埂上,卷着旱烟:“仗打完了,国家建设更需要人。咱有手有脚,种地也是建设。”袁素芬给人接生,半夜被叫醒就走,常常一碗糖水鸡蛋就是出诊费。她从不计较,总说:“从前在朝鲜,命都能舍,现在这点算啥?” 唯一的遗憾,是聚少离多。孙瑞发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,忙集体的事;袁素芬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,更忙。两人有时几天说不上几句话。但每年10月,他们总会抽出时间,坐在自家院子的石墩上——那是他们从老家河边找来的,比朝鲜的砖头平整。泡一壶茶,不说话,就坐着。孙子孙女问:“爷爷奶奶,你们看啥呢?”袁素芬就笑:“看云。”孙瑞发补一句:“看从前。” “从前”是什么?是朝鲜的寒风,是阵地的硝烟,是茅草屋里的麻袋味道,也是两块砖头上,那个决定把后半生交给对方的、简单的笑容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婚后故事,只有复员军人登记表上“孙瑞发,农民”,和“袁素芬,乡村医生”这几个字。可细想想,从战场到田地,从握着枪到握着锄头和听诊器,这种回归平凡的坚韧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战斗”? 他们用一生,实践了当年指导员那句“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”。2018年,孙瑞发老人去世,享年89岁。整理遗物时,家人发现那个锁着的箱子里,抗美援朝纪念章下面,压着一块已经风化酥脆的、用红布包着的砖块碎片。袁素芬老人摸了摸那片砖,轻声说:“从朝鲜带回来的,我都不晓得。”她没哭,只是把那片碎砖,轻轻放在了自己的药箱旁边。 一场战地婚礼,两块砖,三天借来的“洞房”。这就是一代人的爱情和婚姻:没有物质,甚至没有安全,有的只是“活着回来”的渺茫希望,和“跟你过”的朴素决心。他们的浪漫,是硝烟散尽后,愿意陪你回归尘土,在平凡岁月里,把一句承诺守成一生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