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635年,皇太极下令扒光亲姐姐莽古济的衣服,并且让刽子手处以凌迟极刑。每剐一刀,削下一片肉,就会有一声痛苦的惨叫响彻云霄,足足剐了3600刀,莽古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。 莽古济生在一个看似风光、实则冰冷的时代。1590年前后,努尔哈赤正在女真诸部之间纵横捭阖,作为他与继妃富察氏衮代所生的女儿,莽古济一出生就被写进了政治账本。和同母弟皇太极、莽古尔泰相比,她缺少的不是血缘,而是掌握命运的资格。 大约12岁时,她被送往哈达部,嫁给首领吴尔古代。这桩婚事对外是联姻喜讯,对内却是努尔哈赤稳住哈达的手段。 年纪尚小的公主离开本族,落脚陌生部落,身份再尊贵,也难改变自己只是政治纽带的本质。吴尔古代在世时,她始终像个外来者,直到丈夫去世,也没等来真正的喘息。 很快,皇太极接过父辈的棋盘,将她再次推向草原。为了巩固与蒙古的关系,他把莽古济嫁给敖汉贵族琐诺木杜凌。 杜凌家中早有旧爱,她这个远嫁而来的宗女既无主导权,也无感情基础,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时常受到挤压。 她曾把希望寄托在皇太极身上,请求弟弟帮忙扫除隐患,可在皇太极眼里,稳住蒙古各部远比姐姐的婚姻重要,这些求告最终都沉入权力运算的暗流之中。 与此相伴的,是宗室内部越来越残酷的博弈。莽古尔泰身为四大贝勒之一,握有兵权,长期与皇太极政见不合,先被削去贝勒称号,随后又与德格类先后暴亡,死因模糊不清。 更早些年的流言,甚至把母亲衮代与代善牵扯进私情与谋划之中。莽古济身在其间,早就明白这个家族里,父子兄弟可以因为权力彼此算计,亲情随时可以被牺牲。 1635年,一场看似偶然的控告,让她彻底失去了翻身可能。家奴冷僧机站出来指称她与莽古尔泰勾结谋反,琐诺木杜凌也顺势出面作证。 仆人和丈夫,一个地位低微、一个心属他人,却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。就证据本身而言,漏洞并不少,可对急于清除异己的皇太极来说,已经足够用来做文章。 兄弟既亡,夫家倒戈,莽古济被推上了权力清洗的风口浪尖。皇太极很快给这位同母姐姐扣上谋逆的帽子,下令施以凌迟。刑场上,闲人尽数驱散,只留下皇亲与近侍见证。 她被剥去衣物,跪在血泊之中哀求,换来的只有皇太极冷如铁石的眼神。刀起刀落,一刀接一刀,从肉体到尊严被一点点剥离。史书记载3600刀,数字或许带着象征成分,却无疑昭示这是用极刑向宗室和诸部发出的警告。 这场血案的后果很快显现。莽古尔泰一系被连根拔起,家产尽数抄没,旧部被打散归入各旗。代善等贝勒被贬为郡王,并坐议政的格局土崩瓦解,权力进一步集中到皇极个人之手。 八旗制度在这种洗牌中被强化,中央集权结构逐渐成形,蒙古各部陆续归附,边疆局势趋稳,大清入关的根基也在这期间打下。 莽古济的死亡,从权力视角看,是一块被翻面的棋子,从个人角度看,则是一条被反复出卖直至撕碎的生命。 把三段命运串起来看,莽古济的人生仿佛被三次写进权力账簿。 第一次是12岁远嫁哈达,用婚姻换来部落的臣服;第二次是再嫁蒙古,用自己的幸福填补联盟的缝隙;第三次则是在宗室清洗中被当作谋反证据的一部分,用血肉为皇权立威。 她既是女真崛起过程中的联姻工具,也是皇太极削藩集权的祭品。 在那个皇权压倒一切的年代,皇室女子看似锦衣玉食,却往往连生死都掌握在他人一句话中。莽古济并非唯一的牺牲者,只是无数被写进族谱、却被权力吞噬的名字之一。 她的故事提醒后人,若没有制度约束与对个体生命起码的尊重,再显赫的出身也挡不住沦为工具的命运,而那些记录在史书里的辉煌成就背后,往往压着许多这样无处申辩的血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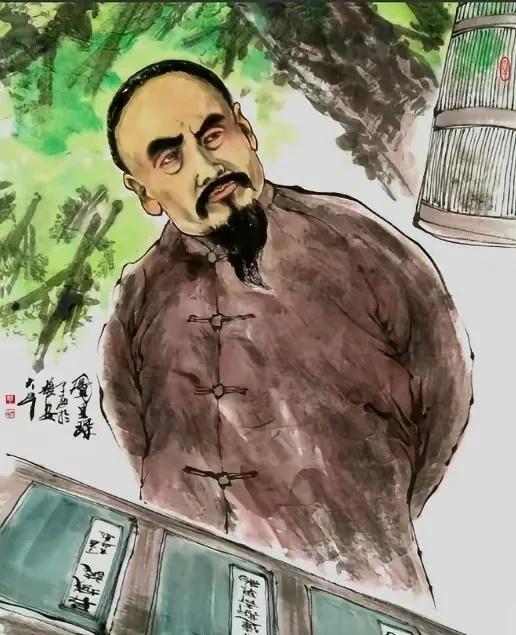

![多尔衮早就给过答案了[吃瓜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8325882357688007920.jpg?id=0)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