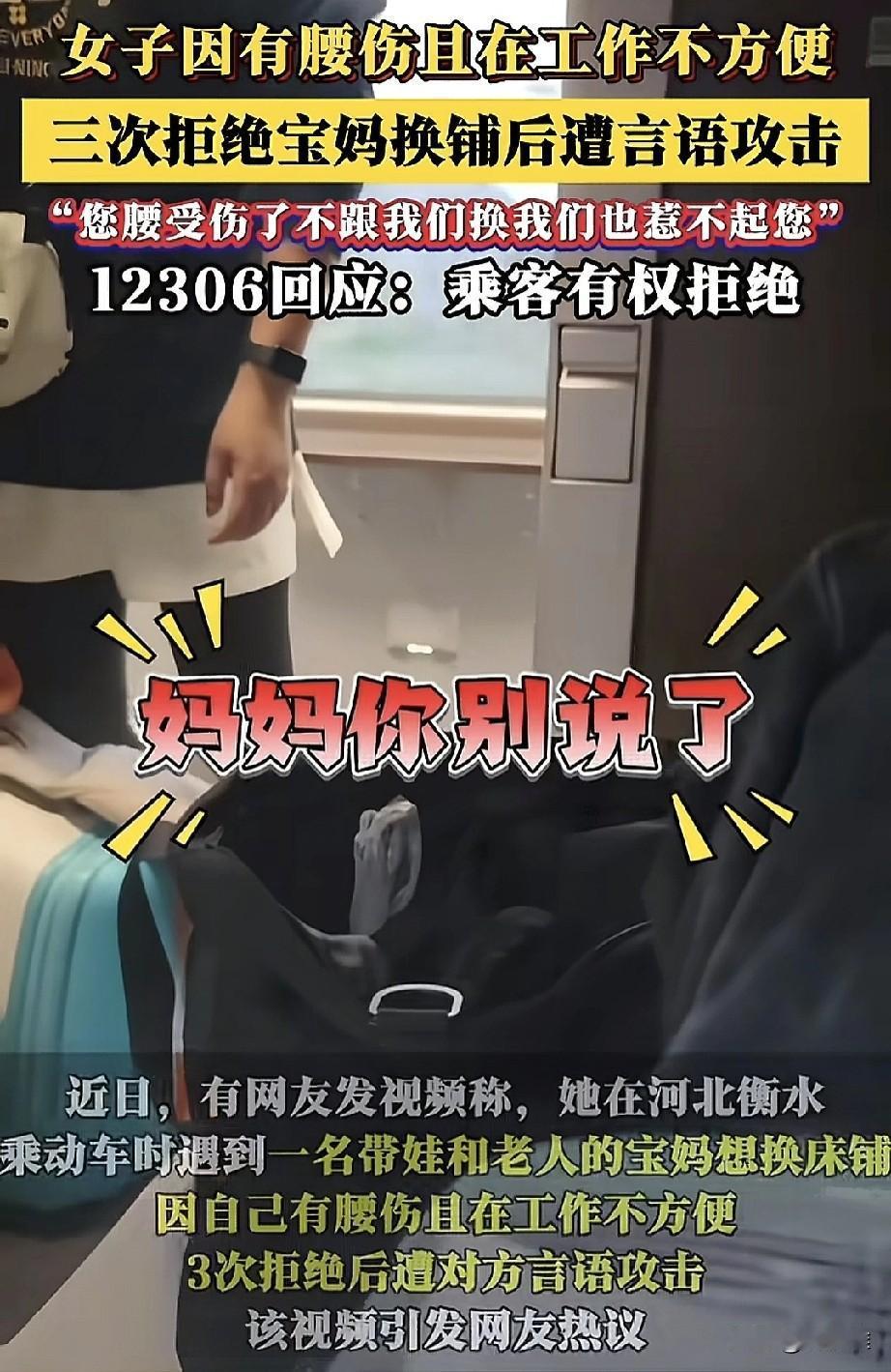他摸了摸口袋,这回是真的一分都不剩了。 那年春天,绿皮火车上人挤人,他刚被下放,胳膊还戴着红袖标,手却本能地往兜里一探——钱没了。不是小偷,是饿极了的娘俩,孩子烧得说胡话,女人抖着手把钱塞进蓝布褂里。 36.5元,够昆明工人干一个月,够他在红河农场挑三十天粪。他认出了她踢人那下虚晃的力气,也认出了她护着布包时手指的裂口。 她掏出信封那刻,他数得一毛不差:“三十张一块,六张五毛,一枚五分。”没记账,没立案,只塞回去两个窝头、一小块红糖。 后来他喝稀糊糊,借了五块钱,三个月还清。写信骗老妈说“吃得饱”,笔尖顿了三次。 再没人提这事,账本上没这笔,档案里没这案。 他摸了摸口袋,这回是真的一分都不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