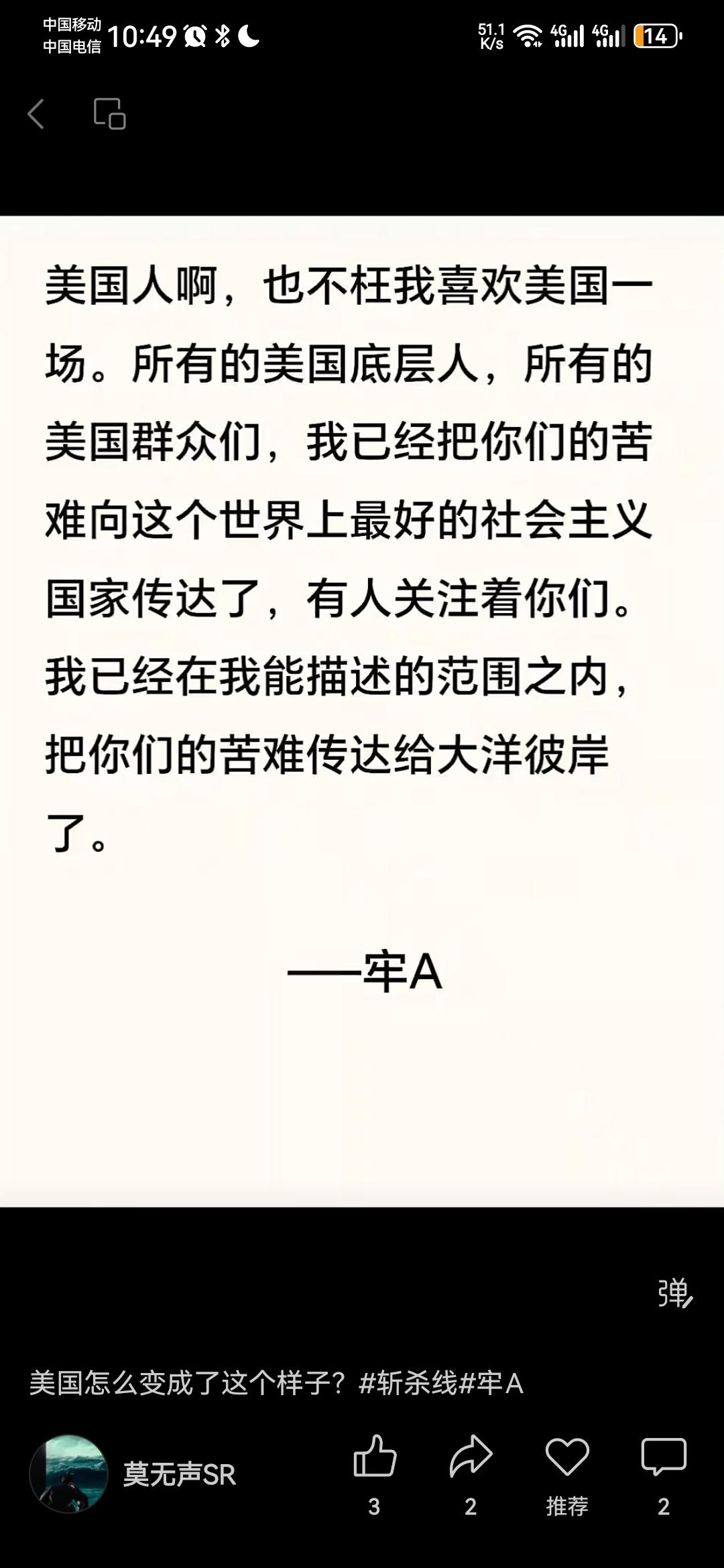2018年,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,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,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,他却突然开口说话,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...... 到2026年再回头看,很多人仍会想起2018年5月,发生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幕。 那是一场被全球媒体围观的离世,但现场的氛围并不喧闹,也不像一般人想象中的“告别”。 房间干净、简单,工作人员按流程操作,背景音乐是他自己选的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,与其说像葬礼,更像一次严格按清单执行的医疗程序。 当事人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·古德尔(David Goodall),104岁,外界对他的印象很统一:头脑清醒、表达直接、逻辑很强。 问题在于,认知还能保持,但身体已经明显跟不上了,按照瑞士协助自杀的规则,最后一步必须由本人亲手完成,医护人员不能替代“启动”。 可他手部力量不足,连常规装置都难以操作,现场于是改用更容易触发的开关,让他用尽量小的动作也能完成确认。 药物开始进入体内后,房间里安静得出奇,亲属、医护人员、旁观的媒体都在等那个“自然的终点”。 但几秒、十几秒过去,他居然还睁着眼,等到大家以为他应该已经昏过去时,他皱着眉说了一句:“这也太慢了(This is taking too long)。” 那一刻,紧张感突然被打断——有人忍不住笑出来,笑完又红了眼,它不是搞笑桥段,而是一个人到最后一刻,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表达方式:不煽情,不配合“悲壮叙事”,甚至对过程的效率都有意见。 很多人把这件事简单归为“自杀”或“厌世”,但古德尔的情况更像是“理性止损”,他不是因为突然抑郁,也不是因为短期情绪崩溃。 相反,他一直强调自己并非绝望,而是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到无法接受,尤其是“尊严”这件事,被消耗得太厉害。 他此前的人生并不灰暗,相当长时间里,他一直在工作、写作、组织学术项目,在学术界也有地位和成就。 正因为如此,当他在晚年遇到一系列限制时,那种落差对他冲击更大,比如学校以健康为由,收回他的办公室、限制他继续参与一些活动,这对很多人可能只是“不方便”。 但对一个把工作当作日常核心的人来说,是一种被动的剥夺:你还活着,但你被挪出了你熟悉的位置。 真正压垮他的细节,是2018年初那次摔倒,他在家里跌倒后无法起身,长时间无人发现,独自躺在地板上两天两夜。 对于一个高龄老人来说,这不仅是疼痛和危险,更是赤裸裸的无助——你突然意识到,哪怕你拥有再多成就,在身体失控的那一刻,你的世界,就会缩成一块冰冷的地面。 这种经历在他的描述里被反复提及,因为它让他确认:接下来等待自己的,可能是一次次重复的失能、依赖和羞辱,而不是他能接受的“晚年生活”。 当时澳大利亚的法律,也限制了他的选择,维多利亚州虽然已经推动相关立法,但要求十分严格,主要面向绝症患者。 古德尔并不是“病到马上要死”,他的问题是“老到无法忍受继续活”,在法律框架里,这并不构成许可条件。 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可能性,最后选择瑞士——因为瑞士在特定条件下,允许协助自杀,并且对外国人也开放相关服务。 他从珀斯出发去瑞士的那趟旅程,本质上是一场“为了合法结束生命而迁徙”的行动,到了瑞士后,他仍然保持一贯的表达风格。 在公开告别场合,他穿过印着“Ageing Disgracefully”(大意是“丢脸地老去”)字样的衣服,带着自嘲,也带着对制度限制的抗议意味:他不想把最后几年,活成自己无法控制的样子。 临终前一晚,他吃了炸鱼薯条和芝士蛋糕,算是给自己留的一点“正常人味”,第二天执行程序前,医护人员按照规定,多次确认他是否具备清晰意识、是否理解后果、是否为本人真实意愿,并让他反复表达决定。 古德尔回答得很清楚,意思就是:他希望心脏停止跳动,这不是冲动,是选择。 他离开后,房间里音乐还在放,争议也一直没停:有人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坚持,有人认为这在伦理上无法接受。 古德尔用自己的方式,把问题摆到公众面前——“生命长度”和“生命质量”之间如何取舍,社会、法律和个体意愿应该怎么平衡。 至于他本人,或许正如他生前多次表达的那样:他要的不是别人同意,而是别人承认,他有权对自己的结局做决定。 信源:104岁老人一心赴死,安乐死中途睁开眼留下7个字,令人哭笑不得-腾讯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