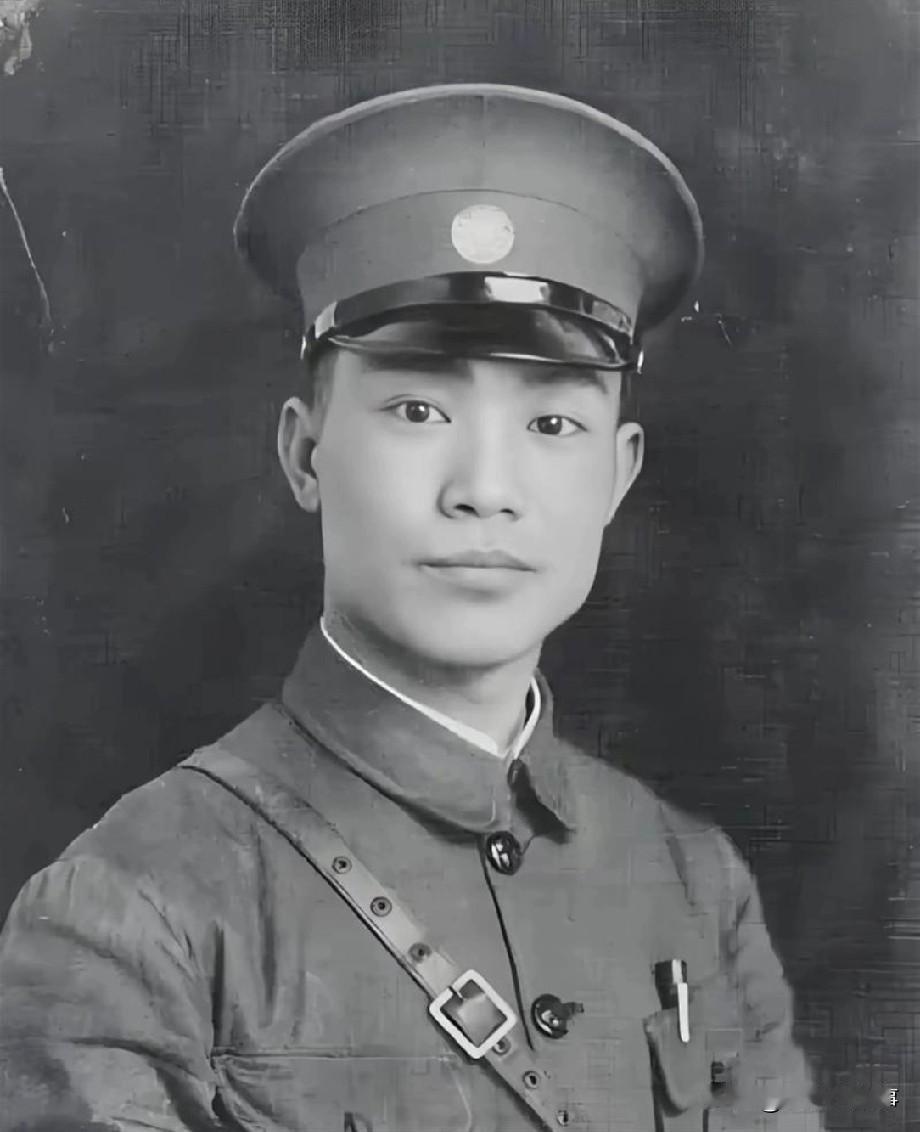1938年春,滕县北门城楼上,王铭章将军的望远镜牢牢锁定了远处那个耀武扬威的日军军官。 一千多米外的土坡上,龟尾寿三正勒马四顾,指挥着部队架设迫击炮。 "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?"将军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战场特有的沙哑。 身旁的副官没有应声,默默摘下背上的汉阳造步枪,三发子弹在枪膛里压得咔咔作响。 城墙上的风卷着硝烟味掠过耳边,川军士兵们趴在垛口后屏住呼吸。 这杆用了十年的老枪没有瞄准镜,枪管上甚至还留着山西战场的弹痕。 副官眯起眼睛,左手稳稳托住枪身,右手食指缓缓扣动扳机。 三声枪响几乎连成一线,远处的日军骑兵突然栽下马来,马队瞬间炸开了锅。 此时的滕县城墙早已千疮百孔。 自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发动进攻以来,这座徐州北大门就没消停过。 王铭章带着川军122师守在这里,手里的家伙什实在拿不出手士兵们大多扛着四川造的单打一步枪,有的枪膛里甚至还生着锈,手榴弹是土作坊里灌的黑火药,扔出去能不能炸响全看运气。 城外的日军却像潮水般一波波涌来。 坦克撞开了东门的缺口,步兵端着三八大盖嗷嗷叫着往里冲。 王铭章在指挥部里来回踱步,桌上的电报叠了厚厚一摞,全是请求增援的急件。 可他心里清楚,李宗仁手里的预备队还在台儿庄布防,能指望的只有自己这帮川娃子。 城破那天,十字街口的指挥部成了孤岛。 日军的机枪扫穿了墙壁,弹片在青砖上溅起火星。 王铭章腹部中弹倒在血泊里,警卫员要背他撤退,被他一把推开。 "弟兄们还在巷战,我怎么走?"他掏出怀表看了最后一眼,表盖内侧贴着的小照片上,妻子和三个孩子笑得正甜。 这只银壳怀表后来被打扫战场的卫生兵捡到,表盘上的弹孔还留着焦黑的痕迹。 这场仗打得有多惨烈?后来清理战场时,人们发现川军士兵的棉军装都被硝烟熏成了黑色,冻裂的手指还死死抠着步枪扳机。 原本计划三天拿下滕县的日军,硬生生被拖了五天五夜。 正是这多出的几十个小时,让李宗仁有时间把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调到台儿庄,为后来的大捷埋下伏笔。 我觉得最让人动容的,是那些川军士兵口袋里的家书。 有的信纸上还沾着泥浆,字迹却工工整整:"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,儿已抵前线,枪好粮足,勿念..."其实他们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穿了,冻得发紫的脚脖子上缠着破布条。 这些来自四川盆地的汉子,穿着单衣在北方的寒风里作战,到死都没见过坦克长什么样。 现在滕州革命烈士陵园里,王铭章将军的纪念碑前总放着新鲜的野菊花。 去年清明我去的时候,看见一位老兵颤巍巍地把一枚生锈的汉阳造子弹放在碑基上。 那子弹的口径,和当年副官击毙龟尾寿三的步枪正好吻合。 守陵的老人说,每年都有川籍游客来这里,对着纪念碑喊一声"军长,我们接你回家了"。 那三声枪响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风里,但城墙上留下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。 正是这些带着体温的弹壳,这些染血的家书,这些永远停在1938年的年轻生命,把"杂牌军"的标签碾碎在滕县的土地里。 后来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里专门提到这场战役,说川军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,这话一点不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