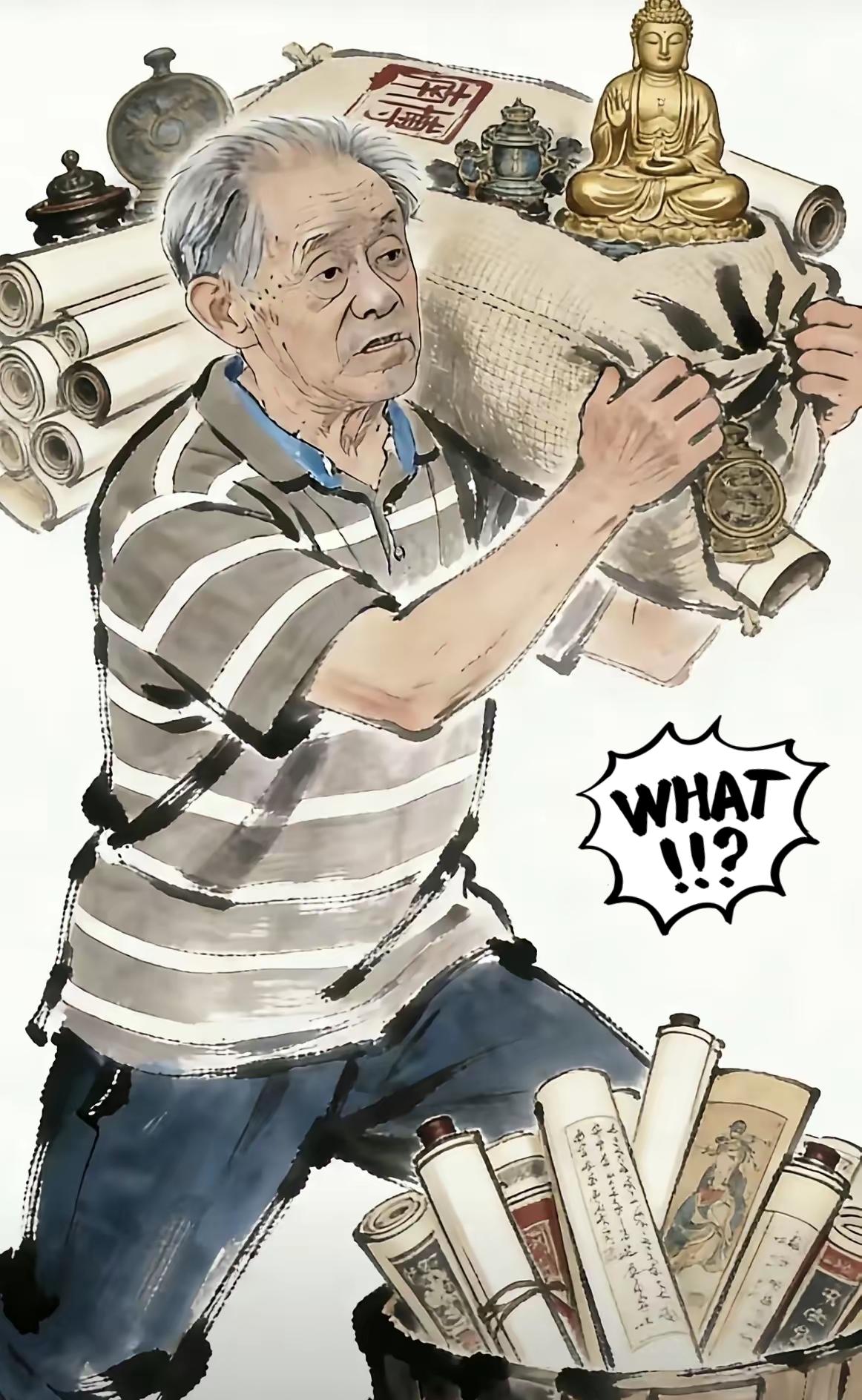戏子在古代陪侍权贵上床是惯例,像梅兰芳都是被冯耿光,从相光堂子赎出来的,甚至不断花费重金给梅兰芳买大别墅,请名师。 要知道当时的北京城,戏子被称为“伶人”,社会地位低下。 他们虽能登台表演,却难逃被权贵玩弄的命运。 而冯耿光作为留日归来的新派银行家,本可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,却偏偏对京剧情有独钟。 当时梅兰芳所在的“云和堂”,并非寻常人想象的风月场所。 而这里是清末民初北京城常见的戏曲私寓,既是学戏的地方,也兼营接待宾客。 那会儿年幼的梅兰芳在这里学戏,不仅要练就一身本领,还要应对各式各样的客人。 冯耿光第一次见到梅兰芳时,这个少年正在师傅的监督下练习基本功。 虽然年纪小,但梅兰芳的表演已经显露出过人天赋。 冯耿光后来回忆说:“他那双眼睛会说话,身段如流水,一看就是吃这碗饭的料。” 当时冯耿光月入四百两银子,但是却拿出一半来支持梅兰芳。 要知道这在当时是笔巨款,足以让梅兰芳从云和堂搬出来,拥有自己的住处。 而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证实:“冯幼伟爱护梅兰芳……月入银四百两,以其半助兰芳成名。” 当然了冯耿光不是简单地砸钱捧角,而是展现出了银行家特有的战略眼光。 他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,形成了后来闻名遐迩的“梅党”。 而这个团体包括留日同学、银行界同仁和文人雅士,他们各展所长,为梅兰芳的艺术发展出谋划策。 “梅党”为梅兰芳建立了名为“缀玉轩”的后援会,其狂热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粉丝后援会。 他们采用“集体编制”的方法创作新戏:先收集有意义的剧本素材,再由专人起草分场提纲,最后集体打磨。 当时这种创作模式在当时颇为新颖,使得梅兰芳的剧目始终保持创新活力。 而就连梅兰芳自己也说: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观众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。 我不愿意站在这个旧圈子里不动,我要向新的道路上寻求发展。 冯耿光对梅兰芳的支持体现在方方面面。 在排演《太真外传》时,他斥资1000块大洋为梅兰芳购置孔雀翎褂子,就为了戏中那件“羽衣”能更加逼真。 而这种投入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,但是却体现了冯耿光对艺术极致的追求。 1922年2月15日,《霸王别姬》在北京首演大获成功。 而这部戏的背后是冯耿光和他银行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。 当吴震修与齐如山在剧本创作上产生分歧时,正是冯耿光居中调和,最终成就了这部传世经典。 梅兰芳的国际化道路也离不开冯耿光的筹划。 在1919年访日、1930年访美、1935年访苏,这些国际巡演的经费大半由冯耿光筹措。 特别是在筹备赴美演出时,当原本的10万经费出现缺口,冯耿光甚至打算变卖自己的房产来填补。 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,梅兰芳面临人生最艰难的抉择。 当时小日本威逼利诱,希望他登台演出为“皇军”助兴。 而这时,冯耿光坚定地支持梅兰芳“蓄须明志”,拒绝为日伪政权表演。 然梅兰芳罢演期间失去了经济来源,一家老小生活陷入困境。 之后冯耿光建议他通过卖画维持生计,并通过中国银行的程慕灏等人,于1945年为梅兰芳在上海举办画展。 当时画展大获成功,也成功的帮助梅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 这段经历充分证明,冯耿光对梅兰芳的支持绝非简单的利益交换。 在民族大义面前,他们共同选择了坚守气节,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。 在新中国成立后,梅兰芳与冯耿光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。 记得一次政协会议上,冯耿光招呼梅兰芳说:“梅兰芳同志,你身体可好?” 而这个称呼让梅兰芳一时感到陌生,甚至有些酸楚:“六哥和我生分了。” 但这份情谊始终未变。 1959年,梅兰芳排练最后一部新戏《穆桂英挂帅》时,年近八十的冯耿光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指导。 当时导演郑亦秋征求意见时,而梅兰芳总是说:“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。” 1961年梅兰芳住院期间,冯耿光几乎每天都要从上海往北京打长途电话询问病情。 这种牵挂持续了半个多世纪,直到生命的终点。 梅兰芳曾深情地说:“我少年的时候,很多人爱我,但无人知我,唯有六爷,爱我又知我。” 这句话道出了这段关系的真谛,它超越了简单的赞助与被赞助,而是基于对艺术的共同热爱和对人格的相互尊重。 从1907年云和堂初遇,到1961年生死相隔,这段跨越54年的情谊证明:最成功的投资,不是赚了多少钱,而是成就了什么样的人。 在戏子被视为玩物的年代,冯耿光用资本托起了艺术家的尊严。 而在民族危亡之际,梅兰芳用气节回报了这份知遇之恩。 这段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证明,真正的支持不是占有,而是成就;不是施舍,而是相互成全。 真正的文化赞助,从来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,而是灵魂的共鸣与共同成长。 冯耿光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"成人之美",而梅兰芳用艺术生命证明了这种价值的永恒。 主要信源:(冯耿光诞辰140周年:梅兰芳背后的银行家.北京妇女网,从留日学者到抗日斗士.人民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