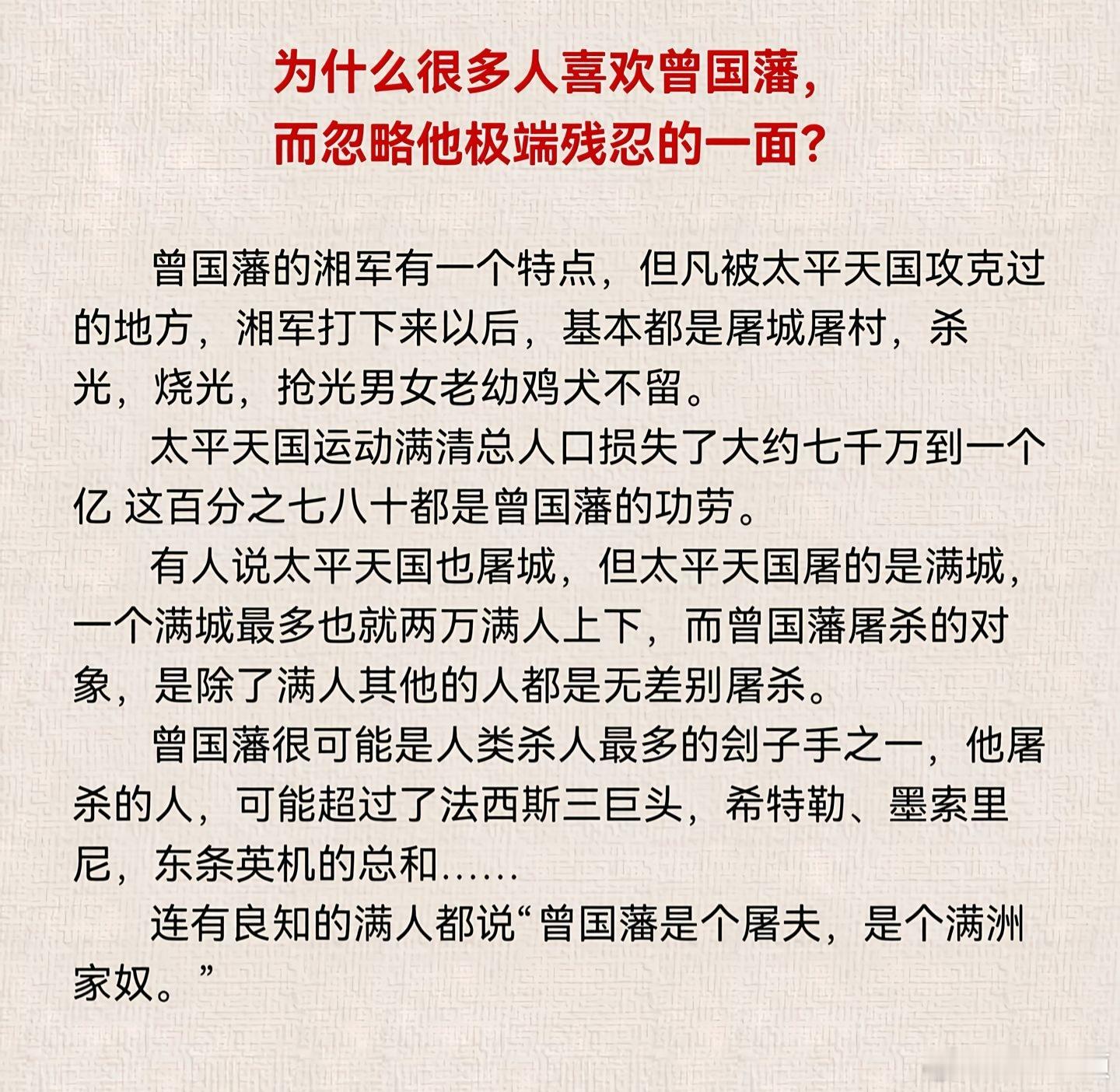1901年,19岁的马一浮丧妻,他发誓不再续娶,岳父同情他,便问他:“我三女 岳父推门进来,看着这个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的女婿,心疼地叹了口气。 "一浮啊," 岳父的声音带着哽咽, "我三女儿今年十四了,模样性格都像极了她姐姐...你要是愿意,就让她来照顾你吧。" 马一浮缓缓抬起头,眼睛里布满血丝。 他望着灵位上妻子的名字,轻轻摇头: "爹,谢谢您的好意。可仪儿在我心里的位置,谁也代替不了。" 这话说得平静,却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,在他往后六十多年的人生里漾开层层涟漪。 马一浮与汤仪的缘分,始于最传统的"父母之命"。 那年他十六岁,还是个在绍兴老家埋头读书的少年郎。 汤家是当地望族,岳父汤寿潜第一次见到马一浮的文章,就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青眼有加。 婚礼办得热热闹闹,新娘盖头掀开时,马一浮看见的是一张温婉秀气的脸。 汤仪不识字,却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 新婚燕尔的日子甜得像蜜。马一浮在书房读书时,汤仪总会轻手轻脚地端来一盅冰糖炖梨; 夜里写字手冷,她就把手炉悄悄塞进他怀里。 可惜这样的温馨太短暂,为了求学,马一浮不得不告别妻子,独自前往上海。 离别那天,汤仪送他到村口的桂花树下,强忍着眼泪往他行囊里塞自己绣的帕子。 "好好念书,家里有我。" 她说得轻松,可马一浮回头时,分明看见她用袖子在擦眼睛。 谁也没想到,这一别竟是永诀。 汤仪染病的消息传来时,马一浮正在上海租界的阁楼上啃德文词典。 他连夜赶回绍兴,见到的已是妻子最后一面。 汤仪瘦得脱了形,见到他却还努力挤出个笑,气若游丝地说: "你回来啦..." 丧妻之痛像一把钝刀子,日日夜夜磨着马一浮的心。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,对着汤仪生前用过的绣架发呆。 岳父提亲那天之后,说媒的人依然络绎不绝,都被他一一回绝了。 有个远房亲戚不死心,带着姑娘的画像上门,马一浮直接挥毫在画像背面题了首诗: "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" 1903年春天,马一浮登上了去美国的邮轮。 甲板上海风猎猎,他望着渐行渐远的海岸线,忽然想起离家的那个清晨, 汤仪站在桂花树下朝他挥手的样子。 在异国他乡,他把自己埋进图书馆,像块海绵般饥渴地吸收新知识。 可夜深人静时,他总会点亮油灯,展开随身带着的那方绣帕——上面一对鸳鸯还是新婚时汤仪一针一线绣的。 游学归来后,马一浮像是换了个人。 他脱下西装换上长衫,在西湖边租了个小院,过起了隐士般的生活。 院子里有株老梅树,开花时暗香浮动,他常在树下读书写字。 有人说他孤僻,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守护心里那片最干净的角落。 抗战爆发那年,马一浮已经名满天下。 日军逼近杭州时,朋友劝他一起去重庆避祸。 他摇摇头,带着几箱书躲进了深山。 炮火连天的岁月里,他在煤油灯下写完了《泰和宜山会语》。 有次敌机轰炸,他第一反应是扑过去护住书稿,碎瓦片把手臂划得鲜血淋漓却浑然不觉。 晚年时,有个年轻学生鼓起勇气问他: "先生一生治学,可曾后悔过终身不娶?" 马一浮正在沏茶的手顿了顿,茶水在杯中漾开细细的涟漪。 他望向窗外一树开得正盛的梅花,缓缓道: "学问之道,求其放心而已。心能安处,便是归宿。" 他去世那天,书桌上还摊着未完成的《尔雅台答问》。 最后一页的留白处,隐约能看到用淡墨写的"仪"字,像是无意间留下的笔痕。 前来整理遗物的学生发现,先生枕头下还压着那方褪色的绣帕,鸳鸯的轮廓已经模糊,但依然保存得平平整整。 马一浮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"曾经沧海"。 他不是活在回忆里,而是把那份深情化作了更浩大的慈悲——对文化的坚守,对后学的栽培,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。 就像他在诗里写的: "此身已作孤山鹤,不向人间觅旧巢。" 主要信源:(中国能源报——马一浮的旷世爱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