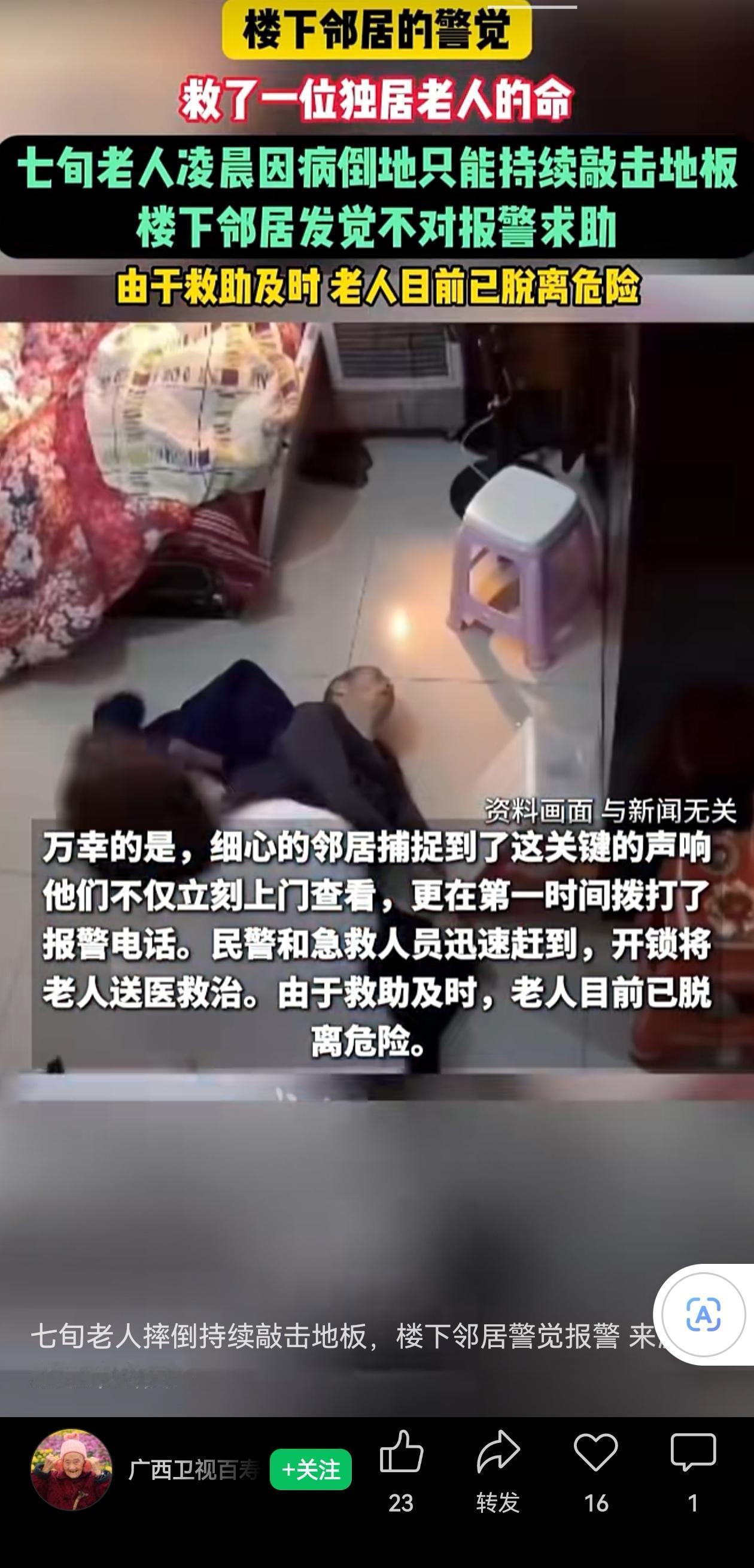老公送儿子上学回来后感叹:“校门口的打印店,今天赚死了。几千个人要打印啊!” 我没出声。不想回应。任何时候都有人发财,有人破产。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老公换了鞋,把公文包搁在玄关柜上,又絮叨了两句。他说打印店门口排了长队,从校门口一直绕到街角,老板雇了两个临时工帮忙,打印机嗡嗡响个不停,一张 A4 纸收两块钱,光早上这波就能净赚好几千。我在阳台收衣服,把儿子的校服叠整齐放进衣柜,没接他的话。 老公推门进来时,玄关的感应灯晃了晃,带着外面初秋的凉。 他换鞋的动作比平时急,帆布公文包“咚”地砸在柜上,拉链没拉严,露出半本卷边的笔记本。 “校门口打印店,今天赚死了!”他扯着嗓子喊,声音撞在瓷砖墙上,又弹回来,闷闷的。 我在阳台收衣服,晾衣杆举到一半停住——儿子的校服外套还滴着水,水珠砸在水泥地上,洇出小小的圆。 他凑过来,倚着阳台门框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墙皮上那道去年搬花盆蹭出的印子。 “排老长的队,从校门口绕到街角那家卖烤肠的店,老板雇了俩临时工,手忙脚乱的。” “一张A4纸两块,你算算,几千个人呢——光早上这波,净赚好几千!”他眼睛发亮,像发现新大陆的孩子。 我没接话,把湿衣服抖了抖,水珠子溅到他裤脚,他“呀”了一声,却没挪步。 晾衣架咯吱响着转了半圈,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,刚好照在他鬓角那根新冒出来的白头发上。 “你说咱当初……”他话说一半顿住,我正把儿子的小内裤叠成方块,指甲掐着布料边缘,没抬头。 去年这个时候,我们的打印店也这样排过队,家长会前夜,家长们挤在门口,为一张准考证复印件吵吵嚷嚷,我和他轮流守着两台打印机,从早上六点忙到半夜,累得倒在地上就能睡。 后来呢?后来教育局说“电子化存档”,一夜之间,排队的人没了,打印机蒙了灰,最后那台陪了我们三年的惠普,五十块钱卖给了收废品的——他当时蹲在地上擦机器,手指关节捏得发白,说“早知道不囤那么多A4纸了”。 他现在说的“赚死了”,是真的羡慕吗?还是只是想找个话题,打破我这两天的沉默? 毕竟上周儿子班主任打电话,说孩子数学又考砸了,我挂了电话就蹲在厨房哭,他在客厅来回走,最后泡了杯红糖水放在我手边,没说一句重话。 他看见的是打印机嗡嗡转着吐钱,我听见的是三年前那台机器最后一声卡顿——卡纸了,卡在进纸口,像我们当时卡在“房租要交”和“没人来印”之间的日子。 所以他絮叨时,我只能盯着儿子校服上的小熊图案发呆,那是他去年求了我好久才买的,说“妈妈,别的同学都有带图案的校服”,现在图案边角磨得起了毛,像极了我们被生活磨掉的那些“早知道”。 我想起收废品的来拉机器那天,也是个初秋的早上,太阳刚出来,照在打印机的塑料外壳上,反射出一道晃眼的光,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说“没事,大不了我再去跑外卖”,掌心的茧子蹭得我虎口发麻,可那天的风,比今天凉多了。 人是不是都这样?看见别人的热闹,就忘了自己也曾在热闹里焦头烂额过? 他没再往下说,转身进了厨房,水龙头哗哗响起来,我听见他在洗番茄——是儿子爱吃的。 有些钱,赚的时候是热闹,赔的时候是冷清,中间隔着的,可能只是一张通知,或者一阵风。 日子不是比谁赚得多,是比谁能在赚不到的时候,还能笑着问“晚上吃番茄炒蛋好不好”。 叠完最后一件衣服,我走到厨房门口,从背后轻轻抱住他,他正在剥蒜,手一抖,蒜皮掉在地上——“吓我一跳”,他笑着回头,眼睛里的光,比刚才说“赚死了”时柔和多了。 阳台的风卷着刚晒好的床单边角,轻轻扫过手背——和那天关店时,最后一张没印完的A4纸边缘一样凉,却又好像,多了点什么暖烘烘的东西。
老公送儿子上学回来后感叹:“校门口的打印店,今天赚死了。几千个人要打印啊!”我
小依自强不息
2025-12-22 11:23:02
0
阅读: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