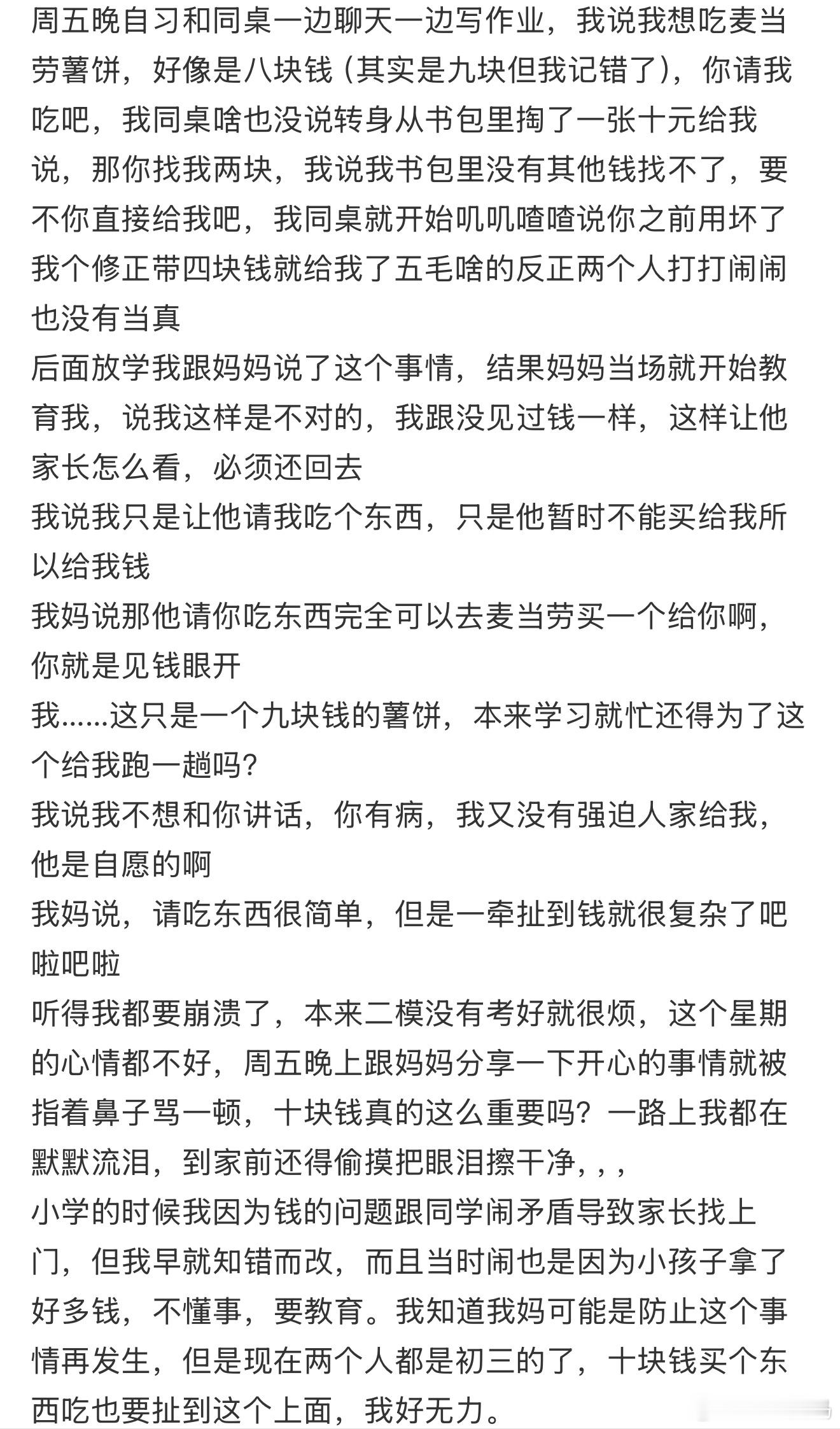一个被贴上反革命子女标签的女知青,下放第三年就开始对着山沟唱歌,唱完哭,哭完笑 队里怕她出事,给她开了返城条,可城里没有单位敢收疯子 她叫苏晚,爹是曾经的大学教授,1966年那场风波来的时候,一夜之间被冠上罪名,关进牛棚再没出来。娘受不了打击,吞了安眠药,留给她的只有一箱子书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。那年苏晚刚满十六岁,背上铺盖卷跟着知青队伍往陕北走,火车开的时候,她没哭,只是死死攥着全家福的一角,指节泛白。 陕北的山沟沟,风硬得能刮掉一层皮。苏晚被分在最偏远的生产小队,窑洞漏风,炕席底下全是跳蚤。队里的人看她眼神都带着提防,没人愿意跟她搭话,都怕沾染上反革命的晦气。她每天跟着社员下地,割麦子、挑大粪,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茧子,脚底的水泡破了又起。收工之后,别人聚在一起唱样板戏、侃大山,她就躲在窑洞的角落里,翻着那箱没被没收的书,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,一字一句地读。那些诗和散文,是她唯一的念想。 下放的第一年,苏晚还抱着希望,她给城里的街道办事处写了无数封信,问爹的消息,问能不能回城。信寄出去,石沉大海。第二年,她不再写信了,只是沉默地干活,沉默地吃饭,脸被晒得黝黑,眼神越来越黯淡。第三年开春,队里种的洋芋出苗那天,她突然跑到山梁上,对着空荡荡的山沟唱歌。她唱的不是样板戏,是爹教她的那些老歌,调子婉转,歌词带着江南的温柔。唱着唱着,她就蹲在地上哭,哭得撕心裂肺,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哭够了,她又突然笑起来,笑着笑着,眼泪又掉下来。 队里的人慌了,都说这女娃是被磋磨疯了。队长看着她单薄的身子,心里不是滋味。苏晚干活从不偷懒,队里的重活累活她都抢着干,分粮食的时候,她总是挑最少的那份。队长叹了口气,托人开了张返城条,塞到她手里。苏晚捏着那张纸,看了半天,没哭没笑,只是把它折好,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 她回了城,可城里早就没了她的家。曾经的房子被分给了别人,街道办事处的人见了她,都绕着走。她拿着返城条去各个工厂、街道找工作,人家一看她的档案,看见那行“反革命子女”的字样,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有人指着她的鼻子说,疯子就该滚回山沟里去,别在城里碍眼。苏晚没争辩,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。她走在空荡荡的街上,看着车水马龙,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。 走投无路的时候,她想起了爹留下的书。她抱着书,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又开始唱歌。路过的人都以为她是疯子,对着她指指点点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停下脚步,静静地听她唱完。老人是曾经爹的同事,也是那场风波里的受害者。老人认出了她,叹了口气,把她带回了家。老人告诉她,爹早就不在了,娘的骨灰,还是老人偷偷收起来的。 苏晚抱着娘的骨灰盒,终于哭出了声。这么多年的委屈、痛苦、绝望,在这一刻全都爆发出来。哭过之后,她擦干眼泪,眼神里有了光。她跟着老人一起,偷偷地整理爹的手稿,那些关于文学、关于历史的文字,是爹毕生的心血。她不再对着山沟唱歌,而是对着那些手稿唱,唱爹教她的歌,唱那些被遗忘的岁月。 后来,高考恢复了。苏晚握着笔,走进了考场。她把这么多年的苦、这么多年的念,全都融进了笔尖。放榜那天,她看着自己的名字,笑了,笑着笑着,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她考上了大学,学的是文学,和爹当年一样。毕业后,她留校任教,站在讲台上,她给学生们讲爹的故事,讲那些在山沟里唱歌的日子。 没人再叫她疯子,人们叫她苏老师。她依旧喜欢唱歌,只是不再哭了。她知道,那些哭过笑过的岁月,不是疯癫,是一个女孩在绝境里,死死抓住的一点光。那点光,是爹的教诲,是娘的牵挂,是文字的力量,是从未熄灭的希望。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无数像苏晚一样的人,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,在苦难里挣扎。他们没有被打倒,是因为心里始终藏着一点光。那点光,支撑着他们走过黑暗,迎来黎明。这份在苦难中坚守的力量,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