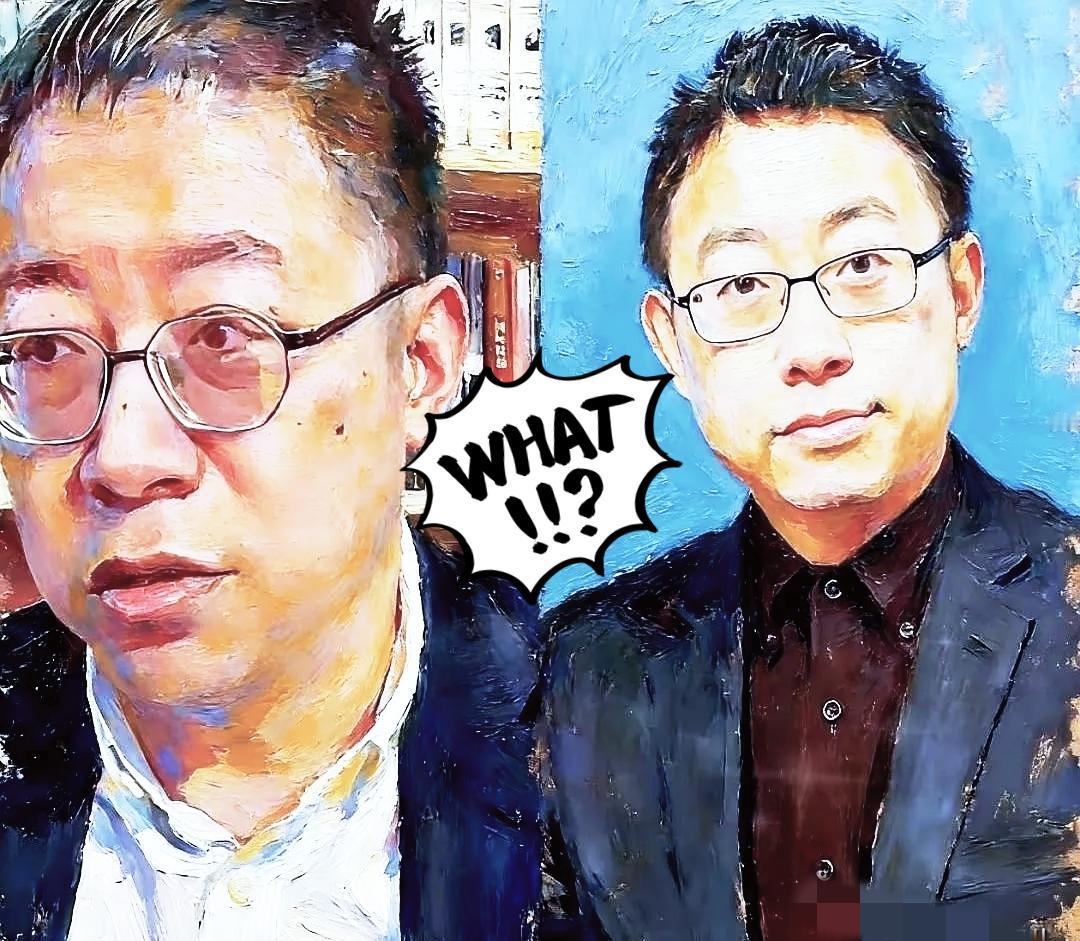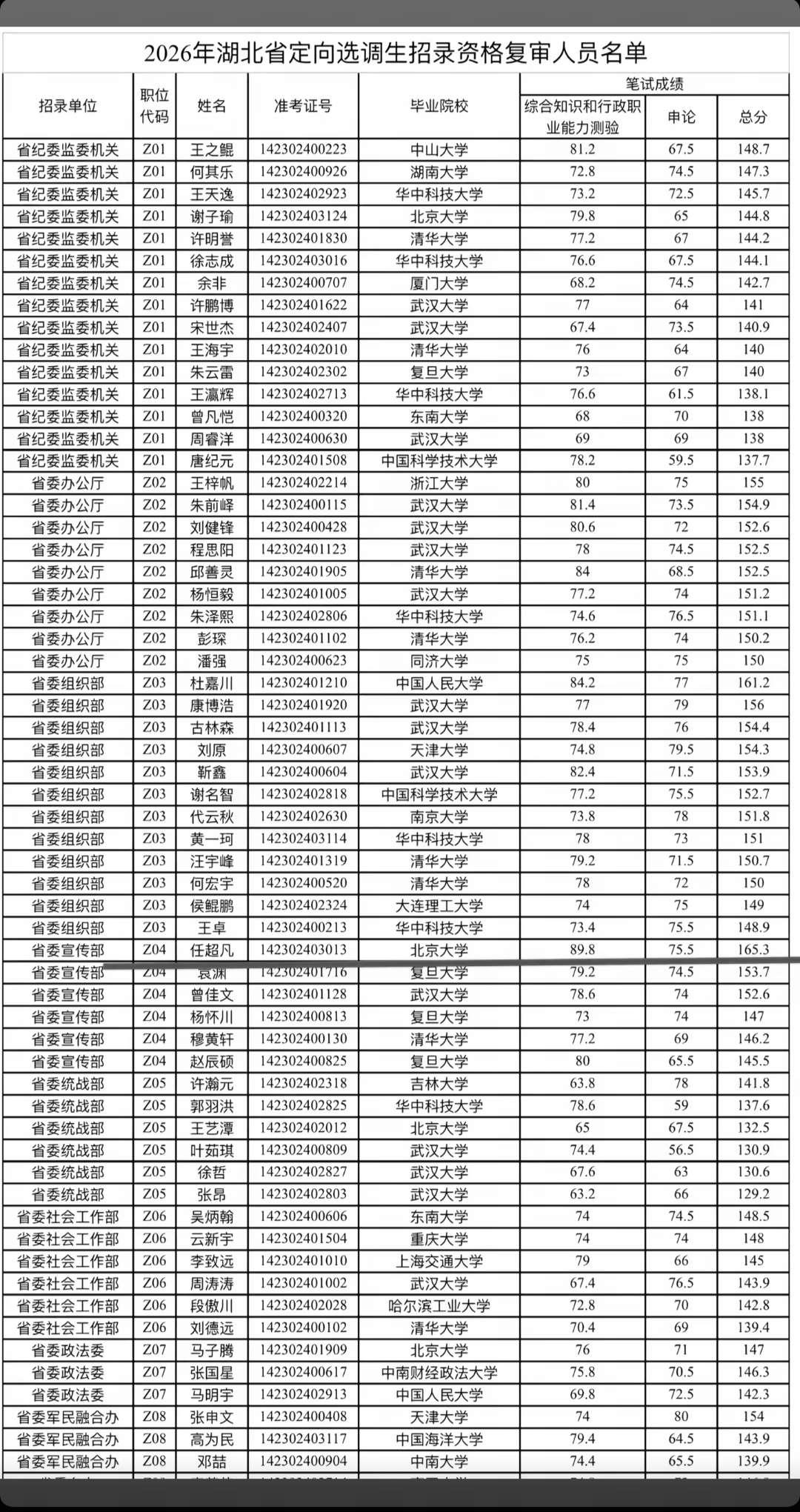“宁愿死也不赔钱!”2019年,一名执教19年的优秀教师,因拒绝向学生道歉赔偿,竟从长江大桥上纵身一跃,撒手人寰。 那天清晨,江面雾气很重。 周安员站在长江大桥的人行道上,风从江面扑上来,带着初冬的凉意。他把围巾又紧了紧,却仍觉得冷。这不是身体的冷,而是一种从心里漫出来的寒。 他今年四十五岁,执教十九年。 在这之前,他从未想过,自己的一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定格。 周安员出生在鄂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父亲在厂里上班,母亲是小学教师。小时候,他最熟悉的画面,就是夜里昏黄的灯光下,母亲伏在桌前批改作业的背影。 “做老师,要对得起良心。”这是母亲常说的话。 也正因为这句话,周安员大学毕业后,放弃了去企业的机会,回到县里中学任教。他教语文,板书工整,说话不疾不徐,学生都叫他“周老师”。 十九年里,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。有调皮的、有聪明的、有叛逆的,也有后来专程回来看他的。 他拿过“优秀教师”,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锦旗。校长常说:“周安员,是咱们学校的门面。” 周安员自己却并不觉得。他只是觉得,站在讲台上,把书教好,把人教正,是本分。 直到那件事发生。 事情起因很小。 那天是晚自习,班里有两个学生在后排打闹,其中一个不小心被推倒,额头磕在桌角,流了血。周安员第一时间带学生去了医务室,又联系了家长。 检查结果并不严重,只是皮外伤,缝了两针。 可第二天,学生家长来了。 家长情绪激动,一进办公室就拍桌子:“孩子是在你班上出的事,你这个老师就得负责!” 周安员一再解释,当时他在讲台上讲课,事情发生得突然,且已第一时间处理。但对方并不接受。 “我们不管过程,只看结果。”家长说,“孩子受伤了,你得道歉,还得赔钱。” 学校出面协调,建议周安员“态度软一点”,毕竟“家长现在不好惹”。医药费本就可以由保险解决,但家长坚持要“精神损失赔偿”。 金额不算天文数字,却像一根刺,扎在周安员心里。 他不是赔不起。他是不认。 “我可以关心孩子,可以去看望,可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。”周安员对校领导说,“但让我承认我做错了、让我赔钱,那不对。” 校领导叹气:“周老师,别太较真。现在讲究息事宁人。” 息事宁人。这四个字,让周安员整夜未眠。 在他看来,这不是一笔钱的问题,而是一个老师是否还站得住的问题。如果所有正常教学中的意外,都要用道歉和赔偿来解决,那教师的边界在哪里? 接下来的日子,压力像一张网。 家长不断投诉,网络上出现了断章取义的说法;有人说他“态度傲慢”,有人说他“漠视学生安全”。学校让他暂停授课,等待进一步处理。 周安员回到空荡荡的家,看着书桌上堆着的教案,忽然觉得自己被一点点剥离。 妻子劝他:“要不就算了,赔点钱,道个歉,日子还得过。” 他沉默很久,说:“如果我错了,我认。如果没错,我不能低头。” 那一刻,他想到母亲的话——要对得起良心。 事情没有朝他期待的方向发展。 调解会上,家长态度强硬,坚持公开道歉和经济赔偿;学校则希望尽快平息风波。所有人的目光,都落在周安员身上。 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已经成了那个“最不重要的人”。 没有人在乎他是否委屈,也没有人真正听他说话。只要事情结束,代价由谁承担,并不重要。 那天回家路上,他给一个老同事打了电话。 “老周,你想开点。”对方说,“这年头,讲理不一定有用。” 周安员挂了电话,在桥头站了很久。 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。 不是愤怒,也不是绝望,而是一种被彻底耗尽的空。 周安员纵身一跃,跳入了江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