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3年,一个断手的机床工人苦苦哀求陈中伟医生为他接手,可这在当时,几乎不可能实现。然而,陈中伟医生却创造了奇迹。 1963年1月的上海,冬日的寒意正浓,但在第六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内,一种灼热的焦灼感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,这不是一台普通的手术,而是一场医学认知与残酷现实的博弈,摆在年轻医生陈中伟面前的,是一只脱离了躯体、依然套着斑驳工作手套的右手。 在这之前的两个小时,这只手属于机床工人王存柏,但那台冰冷的机床冲头无情落下,顷刻间切断了血肉联系,当工友们把他送到医院时,那只断手被一块满是血污的布草草包裹着,甚至指节都还能在布料的褶皱中依稀可辨。 依照当时的医学铁律,面对这样的病例,教科书式的处理方案只有一条:清理创面,缝合残端,等待伤口愈合后安装假肢,在世界医学文献的记录中,此时此刻,还没人能逆转肢体离断的结局。 陈中伟看着那截血淋淋的断肢,理智告诉他应该遵循常规,但感性却让他迟迟下不了清创的命令,王存柏跪在地上,这个在工厂里流血流汗的汉子,此刻为了保住自己赖以生存的右手,在医生面前放下了所有的尊严。 “医生,您救救我的手,家里老婆孩子还要养,没手咋干活啊”那带着颤音的哀求,混杂着冷汗和眼泪,狠狠撞击着在场每一个医护人员的神经,在那个年代,对一个产业工人而言,失去右手,几乎等同于切断了全家的生路。 看着王存柏近乎绝望的眼神,陈中伟心里像是被重重击了一拳,那是劳动人民的手,真的就要这样弃如敝履吗,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与渺茫的技术可能之间,陈中伟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:挑战从未有过的“断肢再植”。 既然不截肢,那就意味着必须要把断裂的骨骼、神经、肌腱,特别是那细如游丝的血管,全部重新接通,这个决定刚一出口,质疑声随之而来。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冒险,更是一场豪赌,万一失败,在这个医疗资源紧张的年代。 后续的感染、坏死以及不得不进行的二次截肢,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医院,后果都不堪设想,但陈中伟没时间犹豫,他迅速组织团队,甚至请来了擅长接血管的专家,然而,手术台上出现的第一个难关就差点让所有人放弃,血管管径严重不匹配。 王存柏断手的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.5毫米,比平日里缝衣服的线粗不了多少,而被寄予厚望的血管专家,也从未在这个微米级别的尺寸上进行过吻合操作,如果用传统的针线缝合,极易造成堵塞或漏血,一旦血运不通,手还得烂掉。 时间的流逝是无声的催命符,离断肢体在常温下的耐受极限并不长,每过一分钟,组织坏死的风险就增加一分,在这个节骨眼上,陈中伟突然想起了曾在一篇文献中看过的“狗腿再植”案例,那里提到了一种非传统的“套缝”技术。 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,立刻让人查阅资料并联络军医大学求证,可现实却再次泼了一盆冷水,电话那头的数据显示,狗腿血管的直径有4毫米,能够使用现成的套管,而王存柏的只有2.5毫米,根本套不上去,两小时已经过去,手术室内的空气凝固到了极点。 难道因为没有合适的管子,就要宣告失败吗,“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替代品”陈中伟在绝望中发问,在这个所有专业医疗器械都失效的时刻,一个护士长的生活智慧意外破局了:“小孩子扎辫子的塑料管行不行”那种塑料管材质软、不仅细还能拉伸。 这一提议瞬间点亮了所有人的眼睛,问题迎刃而解,手术重新换挡加速,在接下来的漫长施术中,陈中伟几乎是屏住呼吸在操作,他戴着放大镜,用细钢针先行固定断骨,再一丝不苟地缝合肌腱。 轮到最关键的血管吻合时,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塑料管作为临时的血管桥梁被植入,这一步容不得半点手抖,哪怕是最微小的差池,都会导致血栓形成,手术从天亮一直持续到深夜,又从深夜做到次日黎明。 当陈中伟终于缝完最后一针,整个人几乎虚脱地瘫坐在椅子上,此时,真正的审判才刚刚开始,大家死死盯着监测仪器和那只刚刚被“缝”回去的手,大约过了半小时,仿佛是某种奇迹的回应,王存柏那根原本苍白冰冷的小拇指,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。 “动了,手动了”欢呼声瞬间在手术室里炸开,陈中伟强撑着疲惫的身躯走上前,指尖搭在病人的手腕上,那里传来了一阵虽弱但清晰的搏动,原本死灰色的断指开始逐渐泛出生命的红润。 然而,医学的探索往往伴随着未知的风险,术后观察期间,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:那只失而复得的手开始异常肿胀,有人怀疑是排异反应,有人认为是术后并发症,阴云再次笼罩。如果不能消肿,受压迫的组织依然会坏死。 解决办法既简单又粗暴,切开释放血水,依照这个思路,陈中伟果断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干预,对患肢进行切开减压,果然随着积血排出,肿胀迅速消退,那只历经劫难的右手终于稳稳地保住了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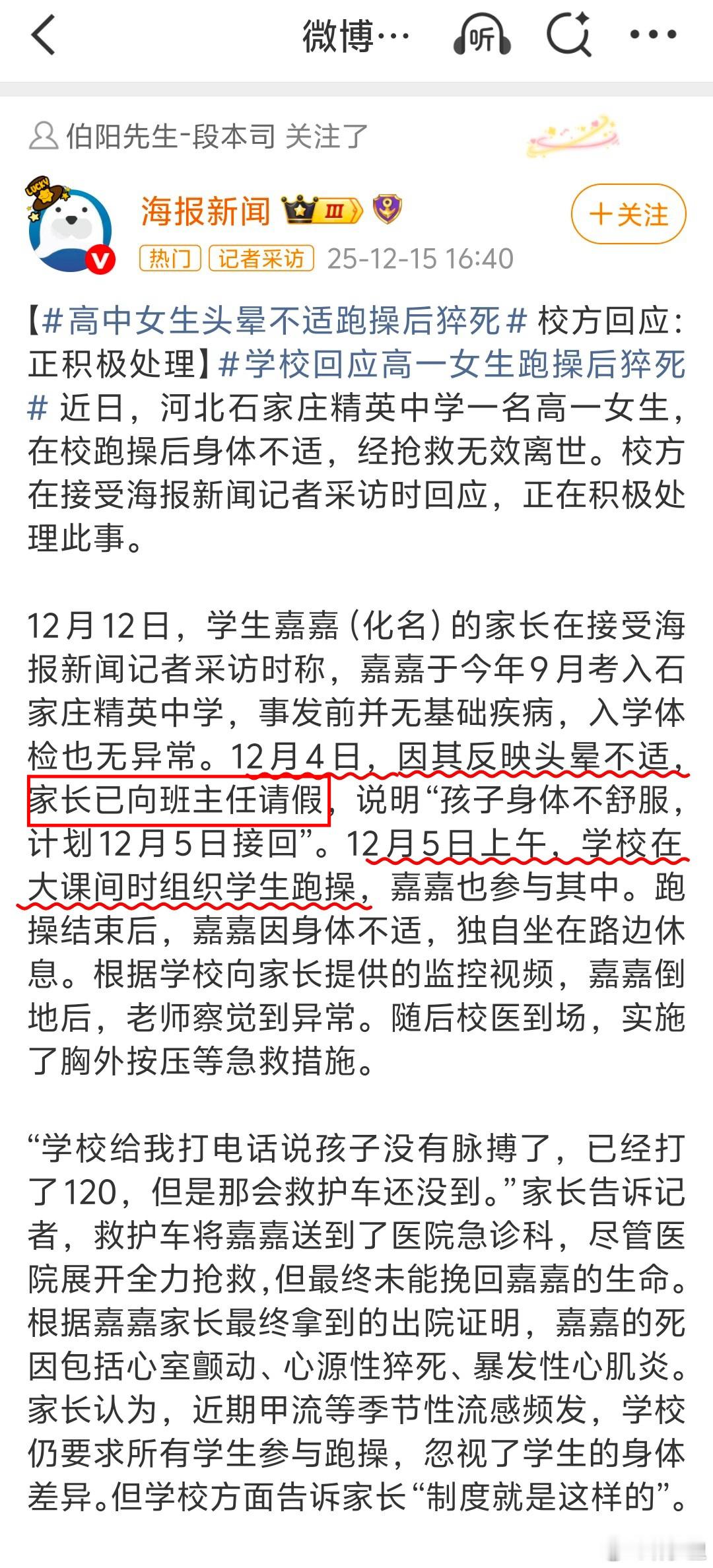


用户40xxx66
厉害👍🏻好医生!这才是医者仁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