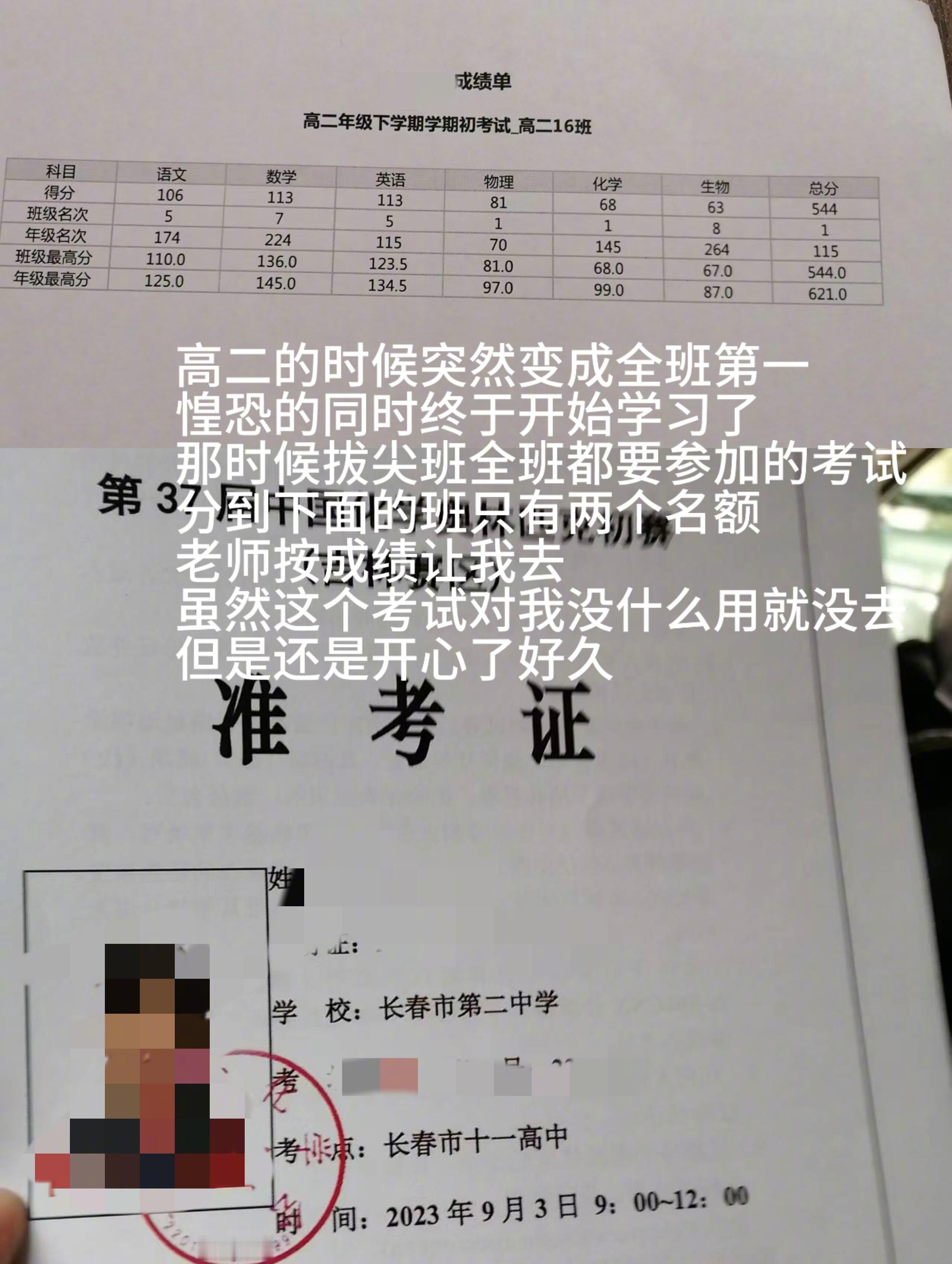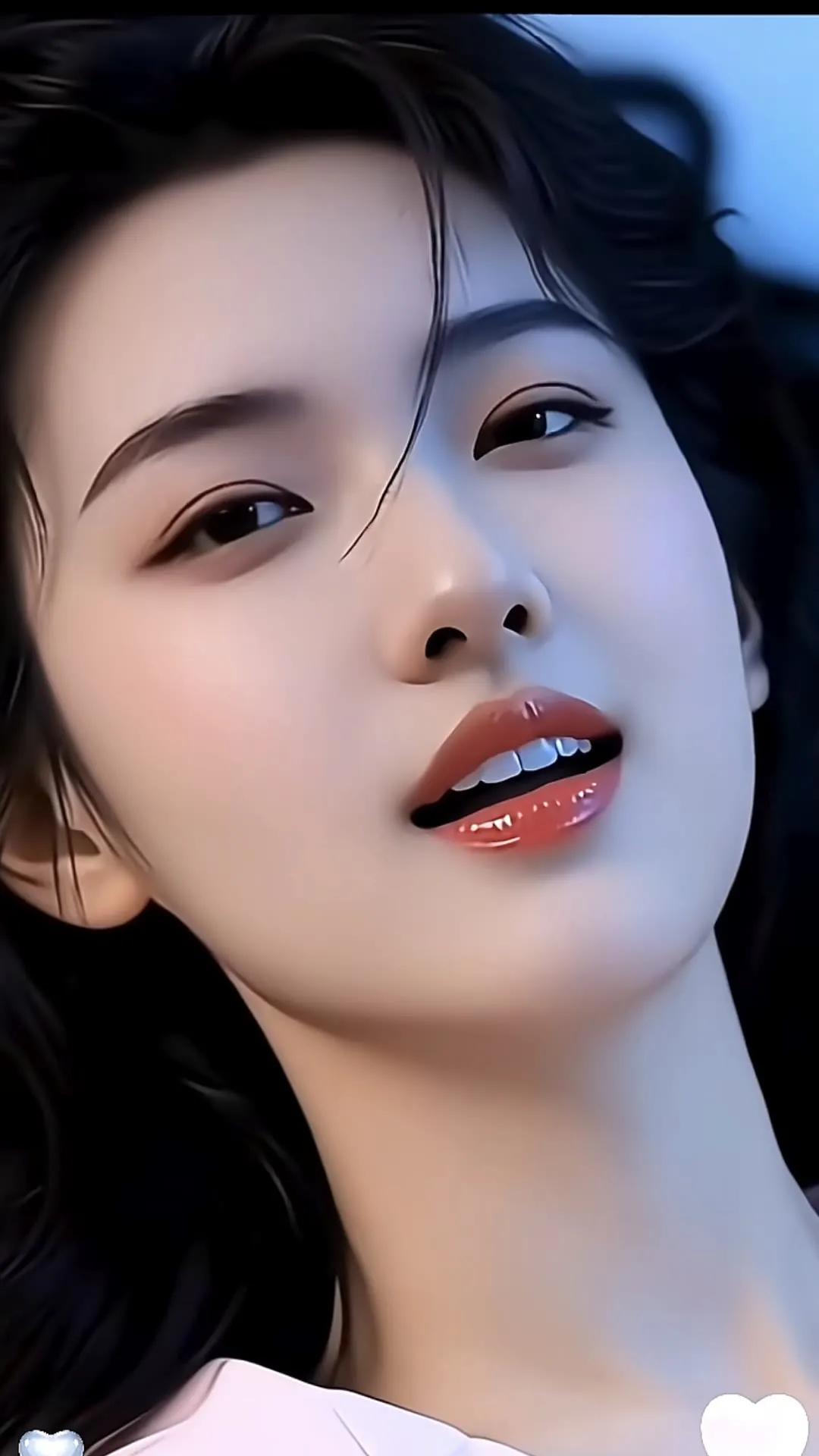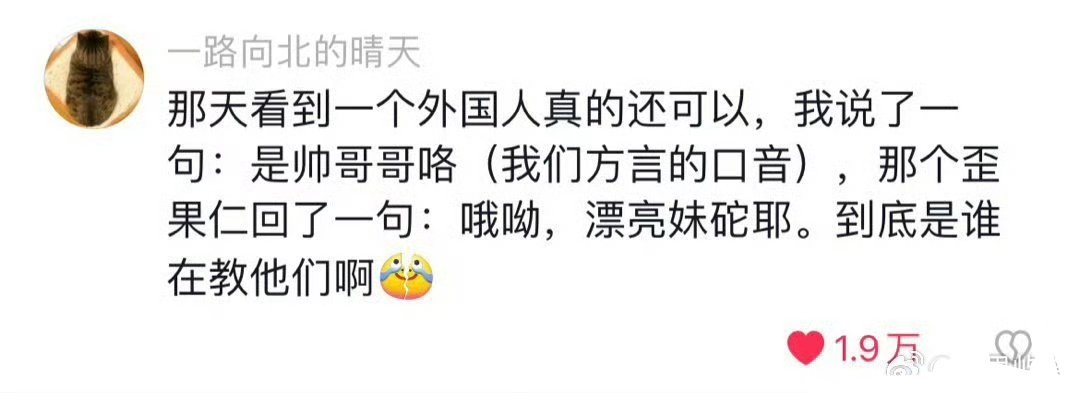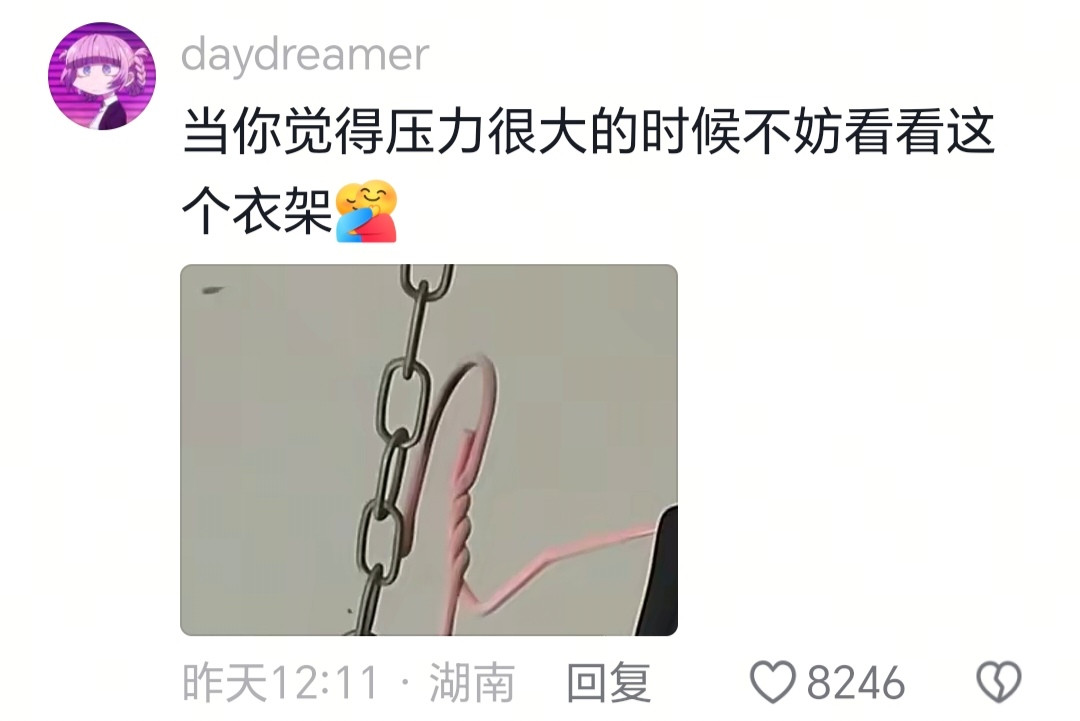一天,太平公主与张昌宗完事后,一边穿衣,一边说:“六郎,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了,从今往后,你就去侍奉陛下吧!”说完,忍不住流下了几滴眼泪。 那泪珠砸在锦缎被褥上,洇出一小片深色痕迹,像极了多年前佛堂里滚落的紫檀念珠。我盯着那水渍,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话:宫里的眼泪,要么是武器,要么是罪证。 那年刚满十六,父皇牵着我的手走进紫宸殿时,武则天正用指尖摩挲西域进贡的翡翠如意。那玉如意通体温润,在她掌心转出细碎的光,她抬眼扫过我石榴红的宫装,突然笑出声:“这丫头的眉眼,倒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。” 我当时不懂,这相似是恩赐还是枷锁。 薛绍教我射箭的那个午后,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握着我的手调整箭姿,箭杆贴着我的小臂,传来温热的触感。“阿瑶,”他说,“箭离了弦就收不回了。” 那时银镯子在我腕间晃荡,反射的光刺得我眯起眼,竟没看清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忧虑。 佛堂的木鱼声突然停了。太监踩着莲花砖跑来报信时,我正抄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,念珠“啪”地断了线,紫檀木珠子滚得满地都是。我蹲下去捡,指尖被木刺扎出血珠,血滴在经文上,晕开一个小小的红点,像极了薛绍送我的那支箭尾的朱砂。 武攸暨捧着凤冠跪在我面前时,金簪上的红宝石映得他脸发青。我摸着腕上的银镯子——那是薛绍留下的唯一念想——突然觉得讽刺。母亲说这是天恩,可这天恩重得像座山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凤冠上的珍珠垂下来,蹭过我的脸颊,凉得像薛绍断气时的手。 张昌宗替我暖手时,掌心的温度烫得我一缩。他的手是冬日炭火,热烈却灼人;薛绍的手是春日溪流,清润却遥远。那天我故意把鎏金粉盒打翻在他锦袍上,看他慌忙擦拭的样子突然笑出声。这宫里的男人,和御花园里的牡丹有什么区别?开得再艳,也不过是主子案头随时能换的摆件。 高戬被押入天牢那晚,我对着星象图枯坐到天明。钦天监说紫微星犯冲,危月燕的位置有血光。我用银簪在图上划了道痕,突然懂了母亲为何总说“最是无情帝王家”。情爱?在皇权面前,连尘埃都算不上。第二天早朝,我亲手递上弹劾张昌宗的奏折,看着他被侍卫拖走,背影竟和十年前薛绍消失在宫墙尽头时重合了。 发髻上的金步摇晃了晃,坠子敲在耳后,冰凉的触感让我一个激灵。母亲当年给我插这支步摇时说:“太平,这宫里的女人,选夫君就是选筹码。” 那时我不懂,如今摸着鬓角新生的白发,突然想不起薛绍究竟是什么模样了。是教我射箭时的温柔,还是最后诀别时的苍白? “六郎,”我又唤了一声张昌宗的名字,眼泪却不再流了。 你说,若当年在佛堂没有捡起那串念珠,我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? 或许吧。可箭早已离弦,路早已选定。这深宫里的每一步,从来由不得自己。 只是偶尔梦回,还能听见薛绍的声音:“阿瑶,箭离了弦就收不回了。” 而我,早已是那支离弦的箭,再也回不了头。
这才是真正的少女心事
【1点赞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