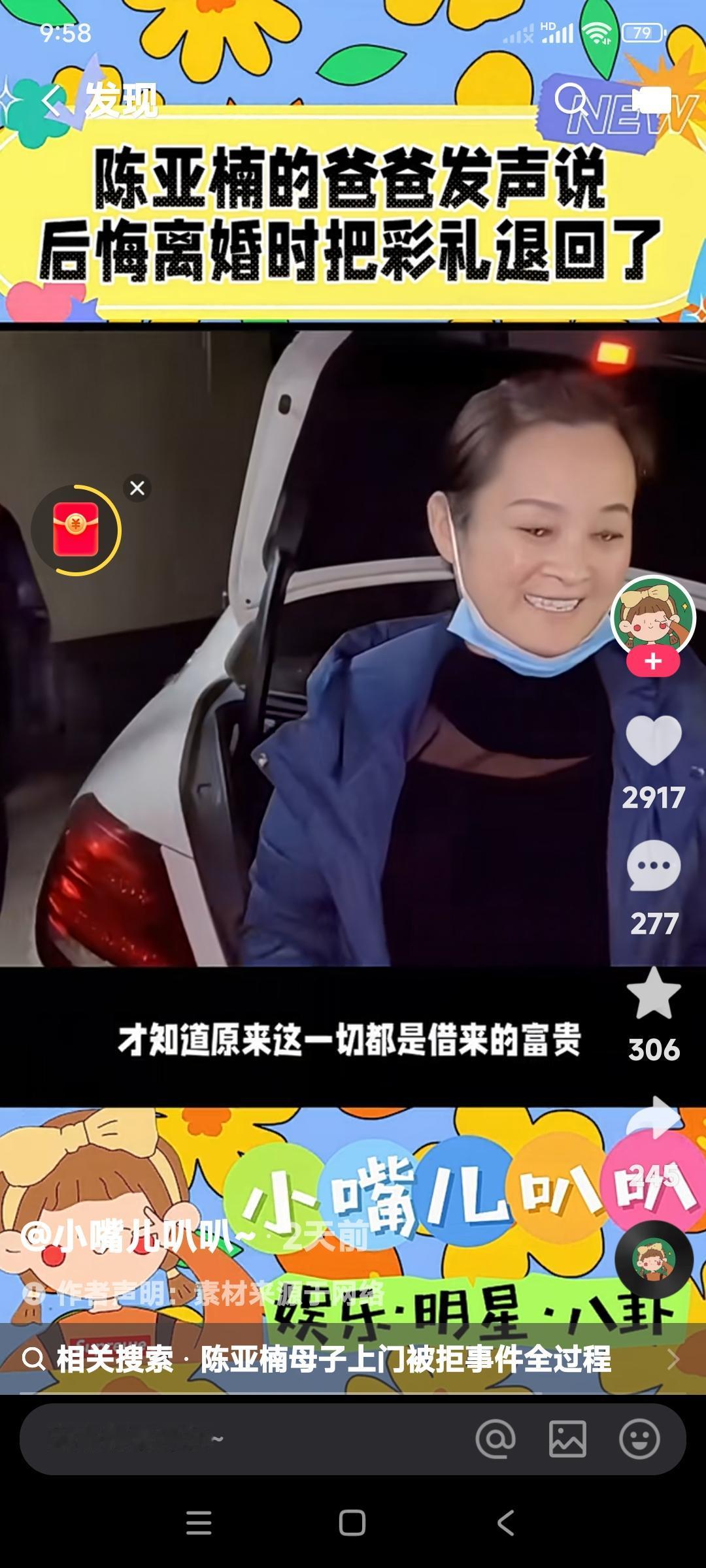1964年,琼瑶离婚后,做了平鑫涛的情妇。平鑫涛的妻子哭着求她,把丈夫还给自己,琼瑶说:“也不是不行,我有一个办法。”平鑫涛的妻子听完那个办法后,当场晕了过去。 那年头的台北,铅字在《皇冠》杂志的版面上跳跃,平鑫涛的名字总与琼瑶的新作连在一起;林婉珍的缝纫机摆在客厅角落,布料堆里还压着没绣完的枕套——她以为的岁月静好,正被巷口传来的流言撕开一道口子。 林婉珍是在丈夫衬衫口袋里发现那把黄铜钥匙的,钥匙串上挂着枚小巧的钢笔状吊坠,那不是她熟悉的物件;后来,又在书堆里翻到夹着风干栀子花的信笺,字迹娟秀,写着“涛,见字如面”。 琼瑶坐在杂志社会客室的沙发上,裙摆扫过地面的声音很轻,说出的话却像冰锥:“他可以周一到周五陪你,周末属于我——这样,你既有丈夫,我也有爱情,不好吗?” 林婉珍没应声,只觉得眼前的吊灯开始旋转,耳边是印刷机持续的“咔嗒”声,再醒来时,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白色床单上,窗外的阳光刺眼得让她睁不开眼。 有人说琼瑶的笔是造梦机,可那些梦的边角,总沾着现实里的泪痕;她在《烟雨蒙蒙》里写“爱情是宿命”,却没写现实中“宿命”的另一头,是三个孩子抱着母亲哭着问“爸爸去哪了”的夜晚。 平鑫涛的名字出现在杂志版权页的时间越来越长,林婉珍的名字却从家庭相册的扉页慢慢淡去;他带着琼瑶的书稿参加文学沙龙,也会在深夜回家时,吃她温在锅里的莲子羹——这种摇摆,像极了他杂志里连载的未完待续的故事。 1976年的离婚协议书上,林婉珍的签名笔画很重,墨水几乎要透到纸背;那天她走出民政局,把十二年的账本和书信锁进旧木箱,转身走进了一家画材店。 琼瑶的小说在70年代的台湾街头被传阅,封面印着“爱情至上”的烫金标语;书店老板说,总有年轻女孩红着眼眶问:“真的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吗?”——她们不知道,书里的“不顾一切”,是另一个女人用尊严换来的。 林婉珍的画室在老洋房的顶楼,阳光透过天窗落在画布上,她握着画笔的手很稳,竹石的轮廓在纸上渐渐清晰;颜料的气味混着松节油的味道,盖过了过去那些酸涩的记忆。 2018年,《往事浮光》出版时,琼瑶正在为平鑫涛的治疗方案与继子女争执;书里没有控诉,只写“缝纫机的线用完了,就换支画笔继续缝补人生”,却让无数读者在深夜红了眼眶。 画展上的《竹石图》前,有年轻人问林婉珍:“您恨过吗?”她指着画里的石头说:“你看这纹路,风雨越打,它越硬;竹叶呢,弯而不折——恨有什么用,不如让自己活成风景。” 如今再读琼瑶的“轰轰烈烈”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;直到看见林婉珍画册上的那句“前半生为家,后半生为己”,才突然明白:真正的爱情或许有很多种,但最好的人生,一定是为自己而活。 巷口的旧书摊还在卖琼瑶的小说,封面已经泛黄;不远处的画廊里,《竹石图》的竹叶在灯光下闪着微光——两种人生,在时光里各自生长,也各自回答着那个未说出口的问题:爱究竟该是掠夺,还是绽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