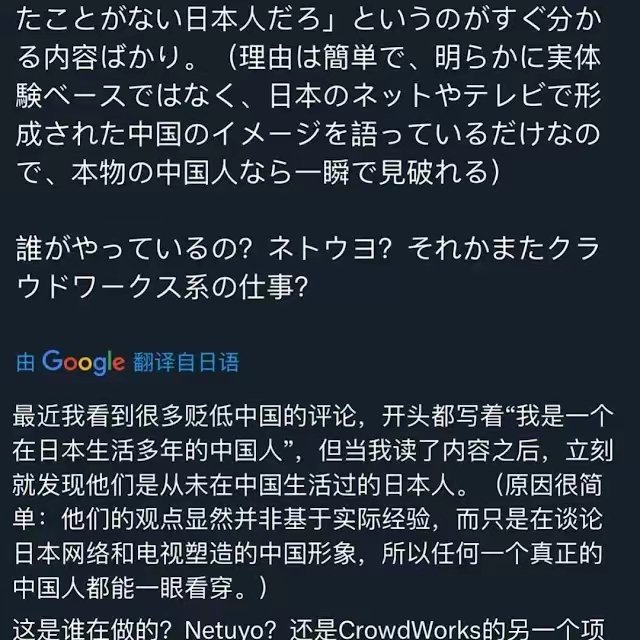我家耕地里有座坟,看着有好几十年了,一直没人来上过坟。我父母在世时心善,从没想过要把这坟平掉。今年开春耕地,我开着旋耕机绕着坟头转,刚想拐过去,机子突然咯噔一下,像是勾住了什么硬东西。我赶紧熄火下去看,坟包边缘的土被犁开一道缝,露出来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。蹲下来扒拉掉浮土,看清是个烟锅子,烟杆断了半截,锅沿上刻着个 “栓” 字,摸着手感还挺沉。 这烟锅看着不起眼,可手里攥着,总觉得沉甸甸的——不光是铜的分量,还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我父母走了三年,他们在世时总念叨,这坟里的人定是可怜人,不然不会孤零零葬在别人家地里。我小的时候,还问过他们这坟的来历,父母只说“早年间的事了”,没多细说,只反复叮嘱“干活时离坟头远点,别惊扰了逝者”。如今挖出这烟锅,我突然想弄明白,这个刻着“栓”字的人,到底是谁。 晚饭过后,我揣着烟锅去了村东头的王大爷家。村里数他年纪最大,今年快九十了,记性却好得很,谁家的老底子他都能说出一二。王大爷接过烟锅,借着灯光眯着眼瞅了半天,突然一拍大腿:“这是栓子的东西!” 我心里一紧,追问栓子是谁。王大爷叹了口气,慢悠悠打开了话匣子。 栓子本名叫李栓柱,是民国末年村里的单身汉,无儿无女,父母早亡,就靠着给人耕地、打零工过活。他手里的烟锅是年轻时跟人学铁匠活,自己打出来的,特意在锅沿刻了“栓”字,走到哪带到哪。王大爷说,栓子为人实诚,干活不惜力,当年我爷爷种地忙不过来,常请他来帮忙,两人处得跟亲兄弟似的。后来我爷爷去世,我父亲接手家里的耕地,栓子也常来搭把手,从不计较工钱,只图一口热饭、一撮旱烟。 “那他怎么会葬在我家地里?”我忍不住插话。王大爷抹了把眼角:“五十多年前的冬天,栓子得了急病,没钱医治,没几天就走了。当时村里没人敢管,一是他没亲人,二是那时候讲究‘无后不立坟’,怕影响村里风水。你父亲心善,偷偷找了我和你大伯,趁着半夜把他埋在了地里最偏的角落,就是怕被人说闲话。” 王大爷顿了顿,又说:“你父母这辈子,从来没跟人提过这事,就是觉得栓子可怜,想让他有个安身之处。这烟锅,定是他下葬时攥在手里的,没想到被犁地给翻出来了。” 听着王大爷的话,我鼻子一酸。想起小时候,父母总教育我“做人要留一线,遇事要存善心”。他们没读过多少书,却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着这句话。栓子的坟在我家地里几十年,父母从未抱怨过,耕种时始终小心翼翼绕着走,甚至每年清明,还会偷偷在坟头培点土、烧几张纸。他们从没想过要图什么,只是单纯地觉得,人活一世,不易;人死之后,该有个安稳的归宿。 可现在呢?村里的耕地越来越少,不少人家为了多多种点庄稼,把田埂刨了、把沟渠填了,更别说一座没人认领的老坟。有人劝过我,趁着没人知道,把坟平了,能多耕半亩地。我也曾动摇过,毕竟种地不易,多一分地就多一分收成。可一想起父母的叮嘱,想起栓子孤苦伶仃的一生,想起这枚刻着“栓”字的烟锅,我就下不了手。 这枚烟锅,锈迹斑斑,早已没了当年的光泽,可它承载的,是老一辈人朴素的善良和人情味。那个年代,物质匮乏,人心却纯粹。我父亲和栓子,没有血缘关系,没有利益纠葛,却能因为一份相识的情分,为他养老送终、守墓几十年。反观现在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。邻里之间,少了走动;遇到事情,先想着利弊;甚至有人为了一点小事,就能争得面红耳赤、反目成仇。 我们总在追求所谓的“成功”“财富”,却渐渐忘了,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一座无人认领的老坟,一枚锈迹斑斑的烟锅,不仅见证了栓子孤苦的一生,更见证了我父母那辈人最纯粹的善意。这种善意,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,而是藏在日常点滴里的体谅、包容和尊重。它不图回报,不求名声,只是发自内心的不忍和善良。 如今,我把烟锅擦干净,找了块红布包好,重新埋回了坟头。耕地时,我依然绕着坟头走,就像父母当年那样。我知道,这座坟,不仅是栓子的归宿,更是父母善良的见证,是我们家最珍贵的“传家宝”。它时刻提醒着我,无论时代怎么变,生活怎么难,做人的底线不能丢,心底的善良不能少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

![也是服了[捂脸哭]用人部门卡试用期最后一天才告知我们不给新员工转正,我们硬着头皮和](http://image.uczzd.cn/5464310708027927438.jpg?id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