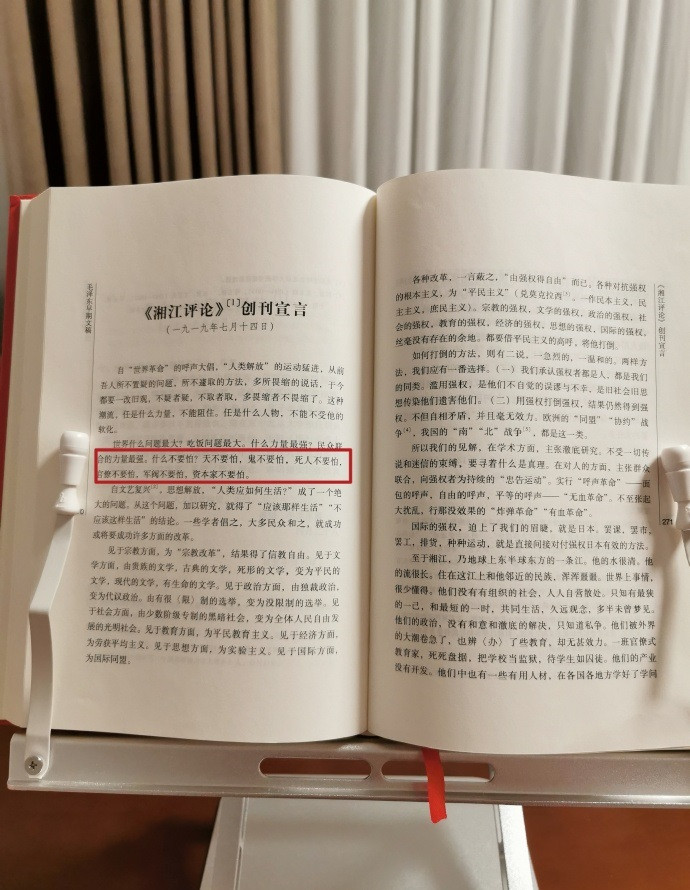1952年,陈赓听说有个军工人才,因贪污几亿元被判死刑,就去找毛主席求情:“此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,能否给他一个机会?” 这句话当时不合时宜。前线天天有牺牲,后方一听贪污两个字就怒火上头。陈赓却还是去了,他心里有个盘算:账能追回,命不能重来,技术也不是街上随手能捡到的。 他并不靠情绪说服人,他拿的是数据和缺口。炮兵没有统一算法,各部队靠经验对,误差一大,代价就是伤亡。他把缺少的那块板子摆在桌上,让人看明白这是堵漏洞。 批示没有立刻下来,流程绕了几圈。有人劝他算了,他把卷宗放回包里,第二天又去。这不是为一个人,是为整条火力链条。他说很硬:该罚的罚,该用的用,别把事混在一起。 最后有个折中办法:先看能力,再谈处理。沈毅被安排到实验室,一件旧大衣挂在门口,进屋就把黑板写满。风速、气温、弹重,他拉着学生搭了个计算框架,先把最基础的误差吃掉。 第一次场测不顺,弹着点偏出几十米。围观的人嘀咕,脸上都是“保错人了”的表情。沈毅拿着记录,沉默把风廓线重新拟合了一遍,调整发射仰角和装药量。第二次,落点稳了下来,误差压到个位数。 外界不容易被一次成功说服。有人问他,你当年挪了那么多钱,你凭什么站在这儿教我们。他没有回避:我做过错事,账要还清,余下的时间拿来把技术做好,这是我能做的事。 他把课堂开到试验场,把讲义写得像说明书,学生拿起就能用。他把每个步骤拆得很细,像在给后来的人铺路。他要求自己和学生都遵守两条底线:不碰钱,不碰虚假数据。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一句心里话:人和制度都不完美,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一个瞬间。贪腐要严惩,这没得商量;但极少数关键技术位,如果能在严格监管下把能力用出来,让更多战士活着回家,我能理解这份取舍。关键在于规矩要硬,权力要关进笼子,成绩要经得起检验。 多年后,有人往学校寄来一封旧信,没有署名,只写了一串数字和三行话:当年第二次试验的风速、温度和装药量,准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沈毅把信折好,放回抽屉。有学生问是谁写的,他说可能是当年的见证人,也可能是提醒我们别忘了那一天。 陈赓后来被问过是否后悔。他没给长篇大论,只留下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:看一个人,别只看他哪次跌倒,要看他后来怎么站起。对我来说,这话不漂亮,但有分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