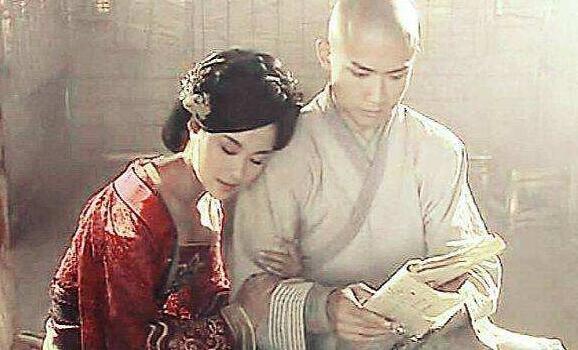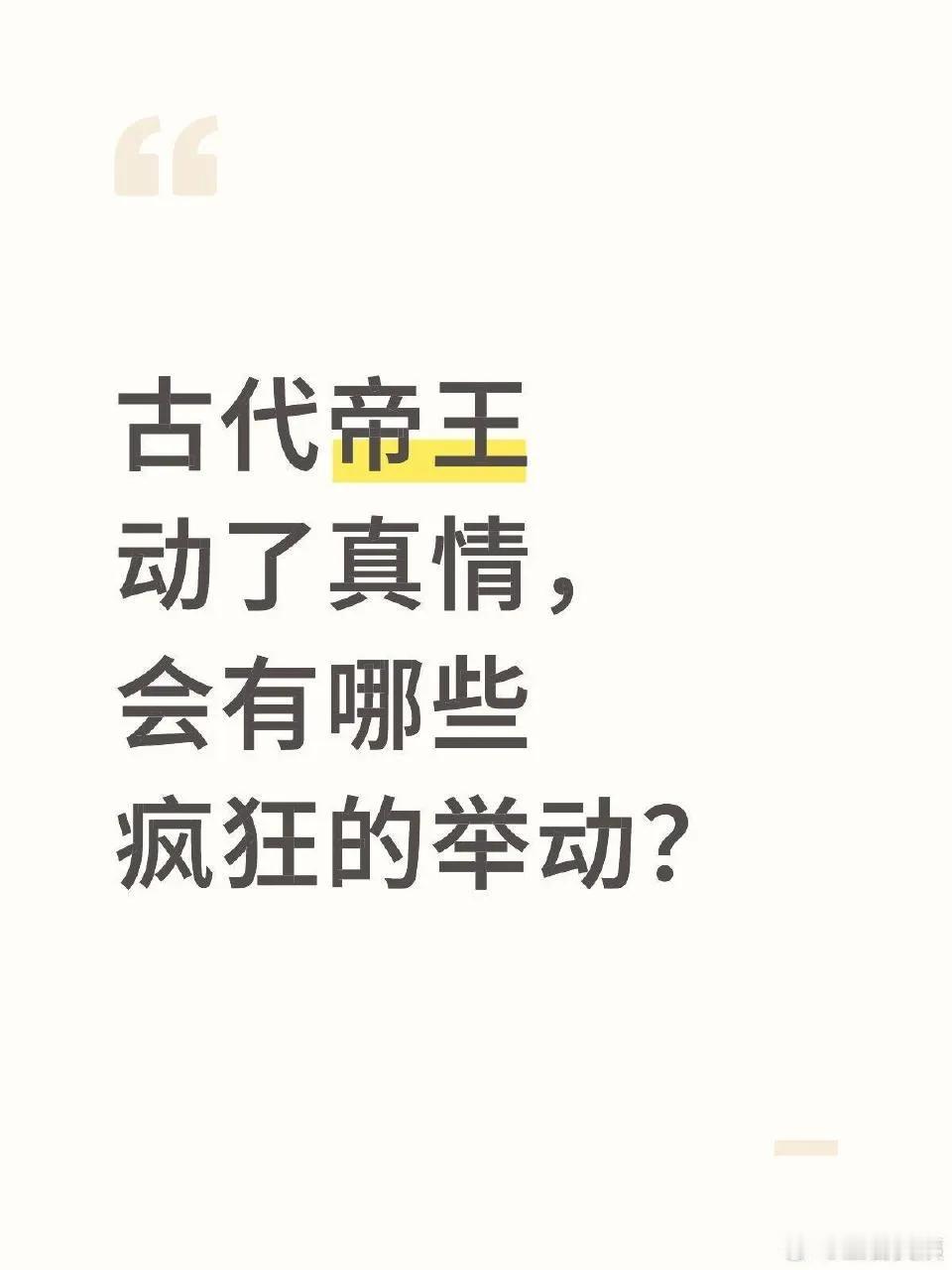显庆二年(657 年),当 62 岁的李勣挂帅西征突厥,他特意带上两个不成器的侄子。军中将领不解,老将军笑道:此去凶险,若有不测,圣上见此庸才,方信我李氏再无将种。队伍刚出长安三日,天就下起了连阴雨,泥泞的路让粮草车陷在泥里动弹不得。李勣的大侄子李忠蹲在路边,看着士兵们挽着裤腿推车,自己却不肯上前,还跟身边的亲兵抱怨:“早知道这么苦,还不如在家待着,起码有热汤喝。”这话刚好被巡营的李勣听见,他没发火,只让李忠去清点车上的干粮。 显庆二年秋,长安城外的风裹着寒意,62岁的李勣披甲站在军前,身后跟着两个缩头缩脑的年轻人——他那两个被京中子弟笑作“米囊饭袋”的侄子。 将领们窃窃私语,老将军戎马一生,怎会带这等货色西征突厥? 李勣听见了,却只捻着花白的胡须笑:“此去万里,总得有自家儿郎在跟前才安心。” 没人知道,他前夜对着祖传的长枪枯坐半宿,枪尖映着烛火,晃出的全是“功高震主”四个字。 队伍刚出长安三日,天就变了脸,瓢泼大雨连下两天,土路成了泥沼,粮草车陷在里头,车轮子搅着泥浆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哀鸣。 大侄子李忠蹲在路边,看着士兵们挽着裤腿、光着膀子推车,泥水溅了满脸,他却往亲兵身后躲了躲,嘟囔着:“早知道这么苦,还不如在家待着,起码灶上的热汤能暖到心窝子。” 这话像根针,扎进了巡营的李勣耳朵里。 他会发火吗?军中谁不知道老将军治军严明,当年斩迟到亲兵时眼都没眨过。 但李勣没动怒,只是走上前,一脚踢了踢李忠脚边的石子:“去,把车上的干粮袋都解开,数数还剩多少麦饼,够不够弟兄们撑到下一个驿站。” 李忠愣了愣,看着叔叔布满老茧的手——那手上有箭伤的疤痕,有握刀磨出的厚茧,此刻却指着那些被雨水泡得发胀的麻袋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家常。 旁边的副将张诚急了,拉着李勣小声劝:“将军,这俩小子连马都骑不稳,让他们管粮草?别到时候把自己弄丢了!” 李勣没回头,只望着远处陷在泥里的粮车:“丢不了,他们要是连数数都学不会,才是真让我省心。” 张诚不解,直到夜里见李勣独自核对粮草账册,在“李忠”的名字旁画了个小小的“钝”字,才隐约明白——这哪是历练,分明是给圣上递话:李家后继无人,不足为惧。 李勣17岁从军,从瓦岗到大唐,手里攥着半壁江山的军功,如今突厥未平,朝堂上的眼睛却比突厥的刀还利。 他不能让李家像当年的韩信那样,成了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的注脚。 所以他故意让侄子在军前露怯,故意任他们抱怨路途辛苦——一个连苦都吃不了的家族,怎会威胁到皇权? 可李勣真就甘心让侄子一直当个“废物”吗? 当李忠笨手笨脚地解开第一个粮袋,麦麸子撒了他一裤腿,他涨红了脸想躲,却被李勣按住肩膀:“数清楚,一粒都不能少——这是弟兄们的命,也是你的。” 李忠从没见过叔叔这样的眼神,那眼神里没有平日的温和,只有沉甸甸的东西,像压在粮草车上的泥,也像压在叔叔肩上的山。 他咬着牙蹲下去,一粒一粒地数,手指被麻袋磨得生疼,却再没说一句“苦”。 当天晚上,李忠的亲兵偷偷给他送热汤,他却把汤倒进了锅里,分给了推车的士兵。 后来的路,李忠不再躲在亲兵身后,他学着帮士兵们扛帐篷杆,学着在雨里清点物资,虽然还是笨手笨脚,却再没人叫他“米囊饭袋”。 李勣看在眼里,夜里写信给家中长子:“吾儿切记,锋芒太露易折,有时候,‘不成器’才是家族的护身符。” 大军行至金山时,雪落了下来,李勣站在山巅望着突厥的方向,身后传来李忠的声音:“叔父,粮草清点完毕,不多不少。” 老将军回头,看见侄子的脸冻得通红,却站得笔直,像一棵在风雪里刚扎下根的小树。 他笑了,这次是真的安心——有些守护,从不需要说破,只需要在泥泞里,慢慢教会他如何站着
显庆二年(657年),当62岁的李勣挂帅西征突厥,他特意带上两个不成器的侄
小依自强不息
2025-11-27 04:20:04
0
阅读: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