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光耀谈到治理贪腐,李光耀说:这个很容易,你一个官员拥有工资之外的巨额财富,这就是贪污来的,你解释不了,就抓你。”一句话,把新加坡反贪的路数捅开:少讲空话,多看账本。 那个面对生死极度坦率的老人走了,享年89岁。他在生前曾直言,与其挂在机器上维持毫无尊严的呼吸,不如干脆利索地结束,这种对“终局”近乎冷酷的理性,贯穿了李光耀的一生。 1923年,李光耀这个名字,起初和“政治强人”毫不沾边,莱佛士学院毕业的他,原本只想做一个生活安稳的律师,但历史没给他平静的机会。 1942年的炮火重塑了他的世界观,日本人把当时的宗主国英国打得落花流水,在李光耀眼中,这堂“暴力课”无比深刻:英国人教会了他如何像绅士一样管理档案和社会架构,但粗暴的日军却让他看见了权力的本质——那是刺刀尖上的威慑。 这种对人性阴暗面的透彻洞察,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时,化作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血流成河的“大扫除”,当时的狮城,贪腐就像散不开的湿热海雾,林有福时代的政府早已烂透,连教育部长的选举经费都要靠外国人买单。 李光耀那一班人穿着纯白衣裤走进市政厅,那身行头不是为了好看,而是向所有人宣告:我们要开始“洗地”了。 他对“脏东西”的清洗,没有任何温情可言,在英国殖民时期也就是个摆设的贪污调查局,到了李光耀手里被直接装上了“核动力”。 不需要逮捕令就能抓人,查账查到连总理的私人户头都不放过,这一招让传统的官场逻辑瞬间崩塌。 其中最令人唏嘘的,莫过于曾经的劳工部部长王永元,此人名下突兀地冒出了六栋别墅和二十多辆豪车,存款甚至是他十年工资总和的三倍有余。 面对质询,他试图把这些巨额财富解释为朋友的馈赠,而调查局根本不听故事,只甩出冰冷的账本:一个还没你零头赚钱的朋友,拿什么送你五十万巨款?没有丝毫回旋余地,哪怕是身居高位的昔日战友,最终也只换来十二年牢狱和倾家荡产的结局。 这种严酷甚至渗透到了毛细孔里,海关官员因为拿了商人一盒没申报的月饼就被撤职,警察顺手收了两包香烟就立刻停职接受调查。 在李光耀的逻辑里,腐败不分大小,因为它是对社会信任最致命的腐蚀,无论是党内元老,还是找他走后门办执照的老同学,在规则面前统统没有特权。 他笃信一点,既然人性的贪婪无法通过进化消除,那就必须建立一个任何人都“贪不起”的恐惧机制,只要你敢伸手,不管金额多小,一旦由于资产来源不明被定罪,连带着养老金和后半生都得赔进去。 但精明的李光耀并不是只懂得挥舞大棒,他对中国的邓小平推崇备至,那种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务实精神深得他心。 他清楚要让精英保持廉洁,光靠恐吓不够,还得给够“胡萝卜”,既然承认绝对的平等是乌托邦,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赋与能力的客观差异,那就建立一套精英制度。 于是,新加坡公务员的薪资与私人企业高管直接挂钩,部长拿着令周边国家咋舌的高薪,这种“高薪养廉”背后是极度精明的算计:让你用合法的体面收入去过上好日子,从而彻底消灭因为生计或诱惑而犯罪的动机。 在这套组合拳下,仅仅二十年,那个曾经只要塞红包就能办事的“贪污之都”,变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富裕社会。 民众从以前的敢怒不敢言,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监督眼线,只要一个举报电话,调查局人员马上就会出现在涉贪官员家门口。 李光耀其实一直没变,无论是对待自己的生死,还是治理国家的毒瘤,他都像一个精准的外科医生:面对现实,摒弃幻想,该切除的时候,绝手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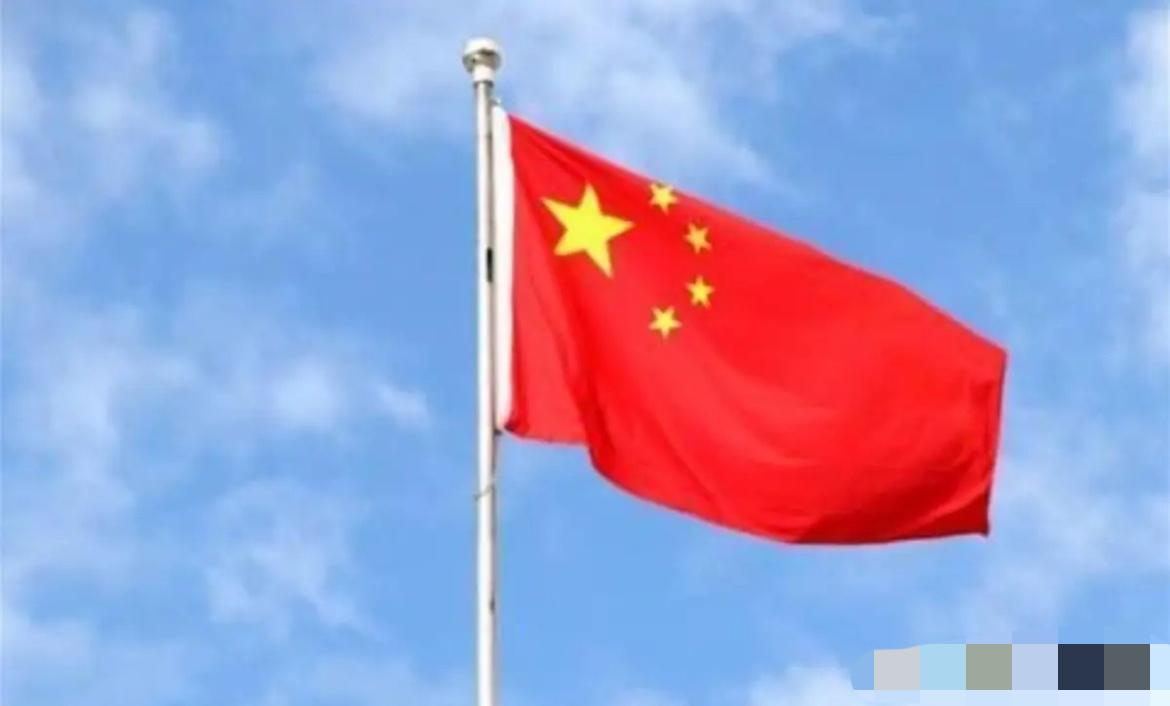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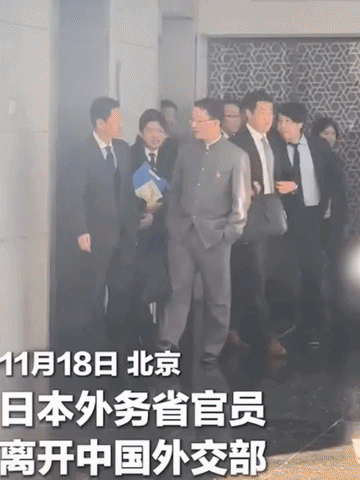



大汉
走了就走了,丢貌似华人,其心早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