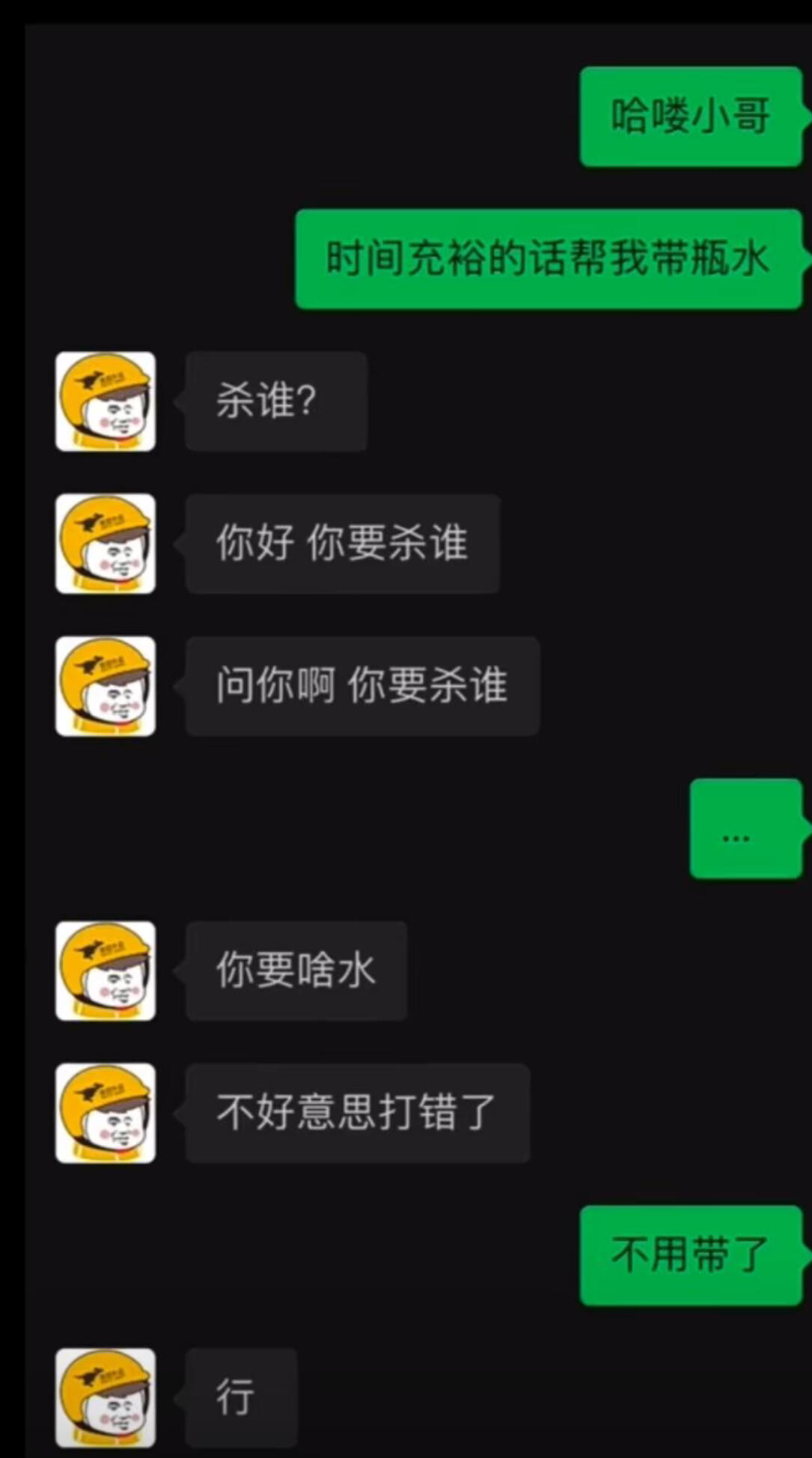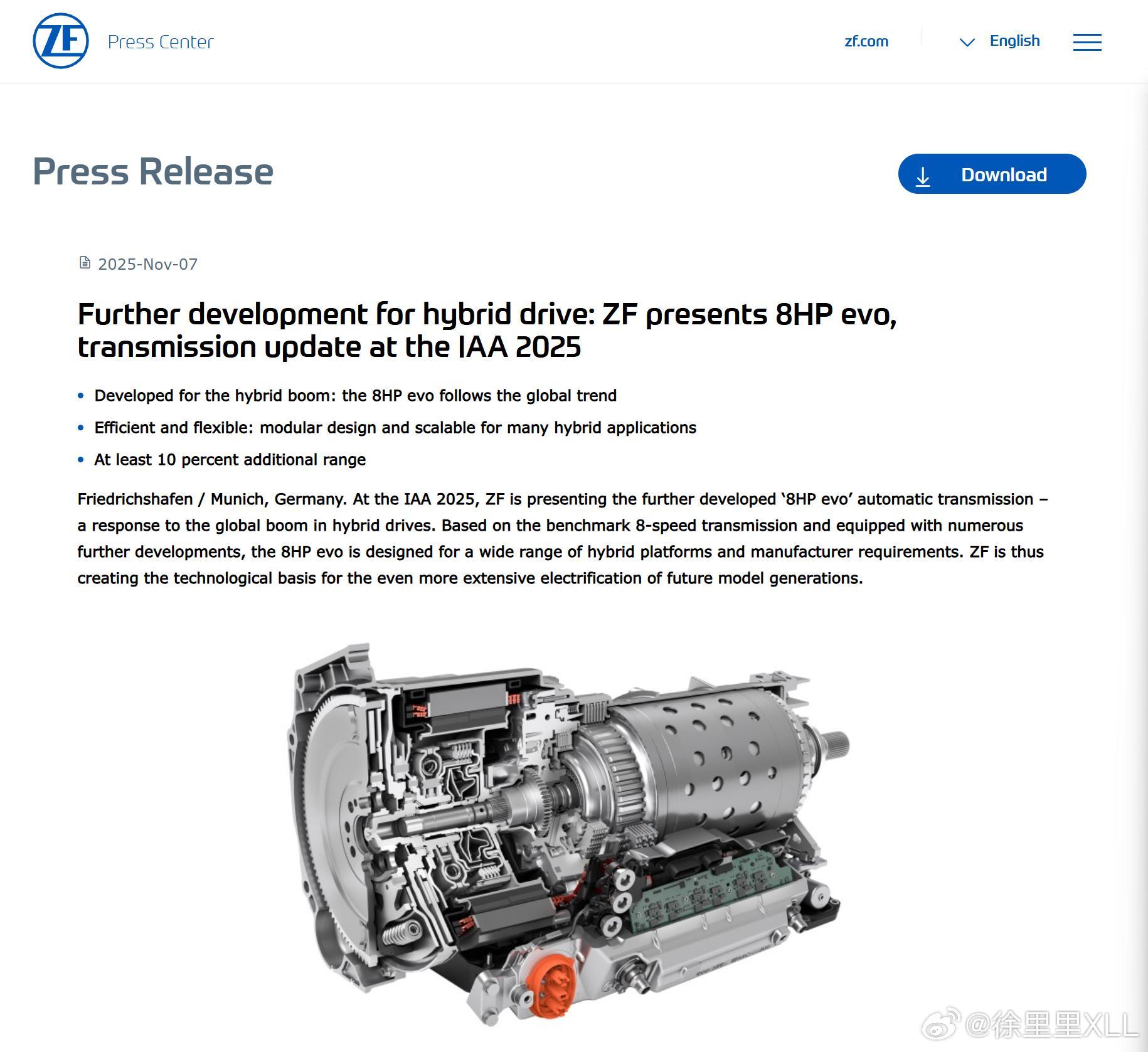山东,夫妻俩花125万,从外地购烟3906条。却在半路被烟草局查获。烟草局对夫妻俩做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,扣除抽样损耗66条。没收33个品种共3840条香烟。男子不服,申请行政复议,市烟草局维持处罚决定。男子大怒,把该区烟草局和市烟草局都起诉到法院。案子先后经过两审,最后法院这样判了! 那本红色的烟草零售许可证,曾是朱亚明和靳丽在山东济宁商业街立足的底气。玻璃柜台里码放整齐的香烟,每个月稳定的流水,本让这个小家庭过着踏实日子——直到那笔125万的“外地订单”,成了压垮一切的稻草。 2020年3月18日的停车场,银色箱货车的车门被拉开时,靳丽攥着手机的手心全是汗。她看着稽查人员清点车厢里的香烟:33个品种,3906条,足够塞满自家烟店的三个货架。那时她还没意识到,这些印着不同品牌标识的烟盒,即将变成法庭上最关键的证据。 “每次运输量都没超过规定”——这是夫妻俩最初面对处罚时的辩解。他们熟悉烟草零售的流程,却刻意忽略了一个细节:从外地批量购烟,不仅需要零售许可证,更得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。就像开车需要驾照,却不能无证运输危险品,法律的边界从来都清晰。 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时,朱亚明觉得“程序有问题”。果然,一审法院审理后发现,烟草局在取证时未能完整提供运输轨迹记录,证据链存在瑕疵,最终撤销了处罚决定。这个结果让夫妻俩松了口气,却没料到这只是法律程序严谨性的体现——而非违法事实的豁免。 烟草局没有放弃。稽查人员重新调取了银行流水,那笔125万的跨省转账记录清晰可见;找到了货车司机王某,他证实“帮忙从乙区转运大批香烟到甲区”;甚至比对了夫妻俩烟店的日常进货量,3906条远超其正常销售需求的三倍。当这些证据被重新提交到法庭,朱亚明的“没超规定”成了站不住脚的托词。 二审法庭上,法官的提问直击核心:“零售许可证允许跨区域采购并运输吗?”朱亚明沉默了。《烟草专卖法》第二十二条早有规定,托运烟草必须持有准运证,且数量有严格限制。他手里的许可证,权限仅限于“在核定地点零售”,而非“绕过本地渠道赚差价”的通行证。 最终的判决下来了:维持烟草局没收3840条香烟的处罚,同时吊销零售许可证。125万货款打了水漂,烟店的玻璃门贴上了“停业整顿”的封条,靳丽站在店外,看着曾经熟悉的招牌,眼圈红了。 这场持续两年的拉锯战,暴露的不只是夫妻俩的侥幸心理,更有法律程序的刚性。初次处罚因证据不足被撤销,恰恰说明执法必须“程序与实体并重”——哪怕事实清楚,缺少关键证据链,行政行为也站不住脚。而当证据补充完整后,法律的裁决便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。 为什么非要冒险?朱亚明后来在法庭陈述时提到,“外地批发商的价格比本地低10%”。125万的货,转手能多赚12万,这个数字让他动了心。却没算清另一笔账:经营多年的烟店价值多少?稳定的客源和许可证的隐性价值又值多少?当这些都因一次违规化为乌有,12万的潜在利润,成了最昂贵的“学费”。 市场上总有人觉得“偶尔违规没事”,就像有人觉得“红灯偶尔闯一次不会被拍”。可法律的红线从来不会因为“偶尔”而褪色。朱亚明夫妇的经历像一面镜子——它照见了利益诱惑面前的人性弱点,更照见了一个简单却容易被忽略的道理:合法经营不是束缚,而是商家最稳固的“保护伞”。 如今,济宁那条商业街上,他们的烟店早已换了新主人。路过的商户偶尔还会提起:“那两口子要是老实从本地进货,现在还安稳做生意呢。”125万的香烟被没收或许只是一时的损失,但失去合规经营的资格,才是真正断了生路。这起案子最终教会所有人的,或许比判决书上的条文更直白:在法律面前,任何侥幸都是在拿自己的生计下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