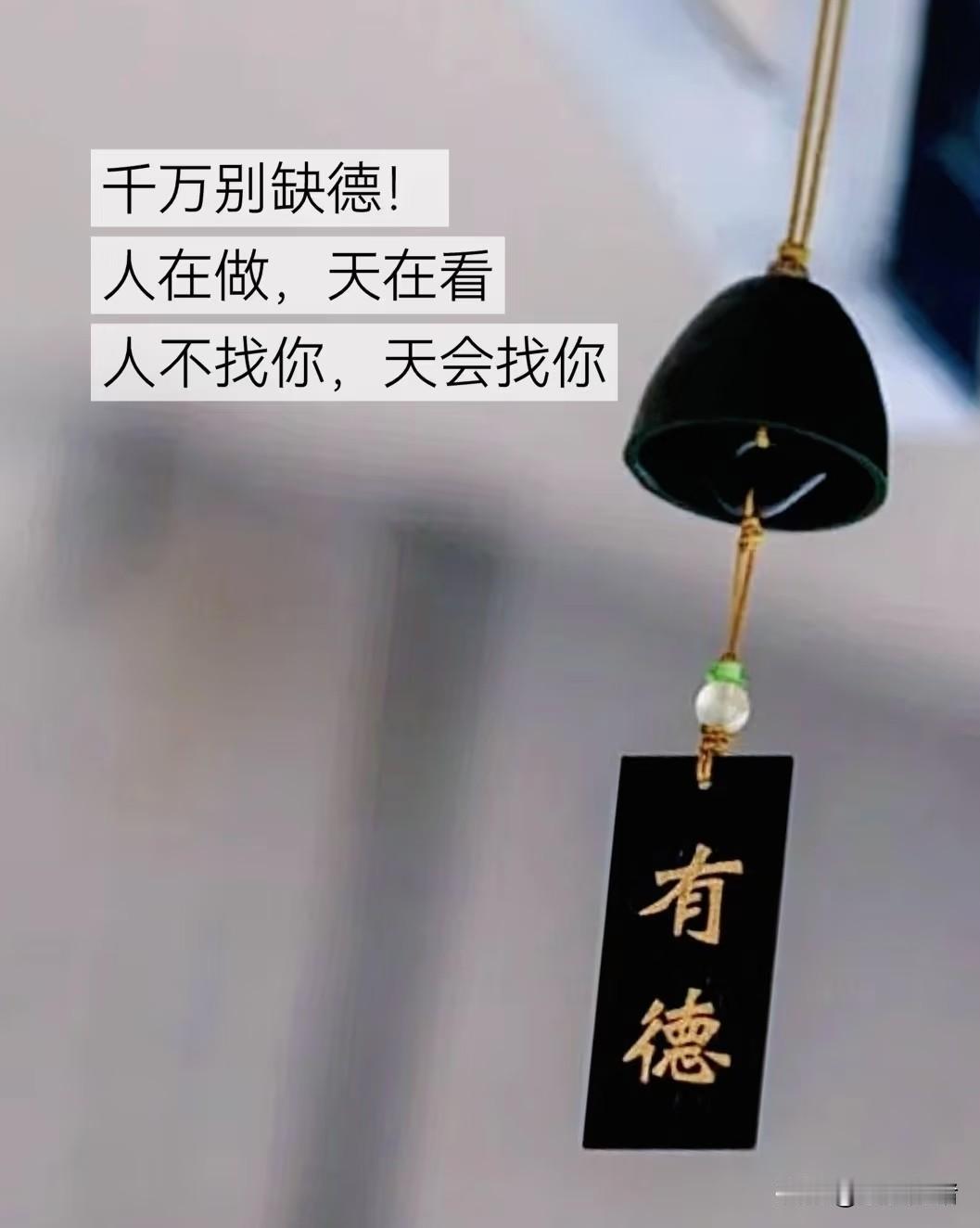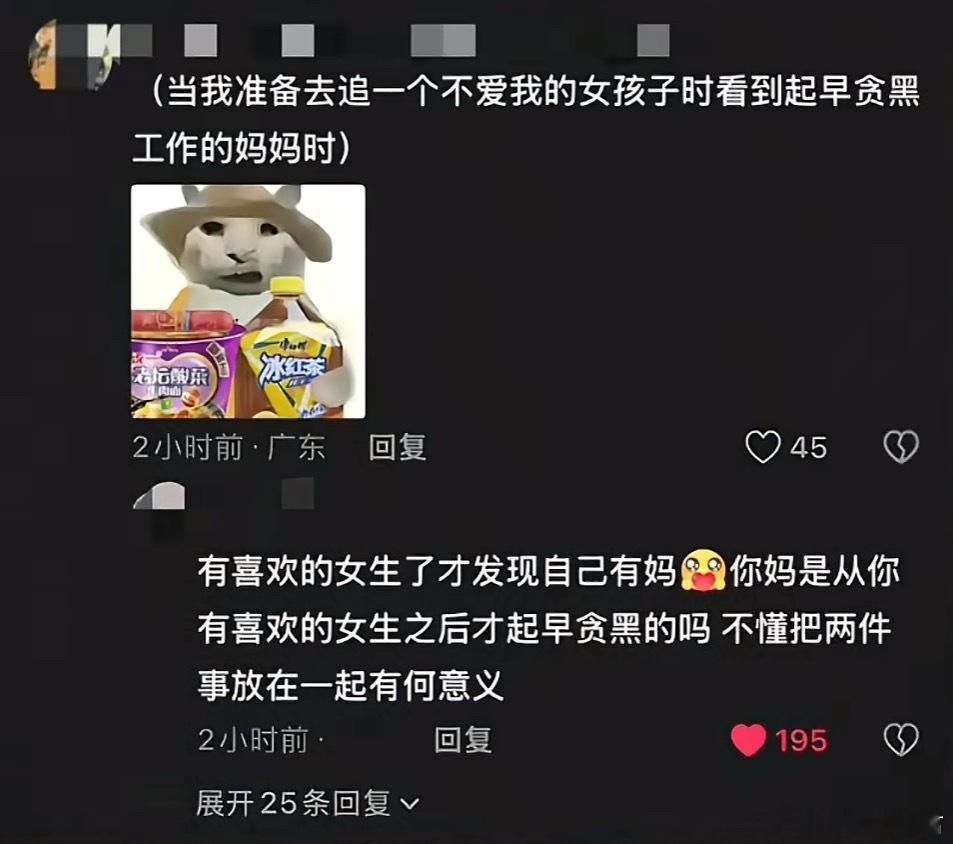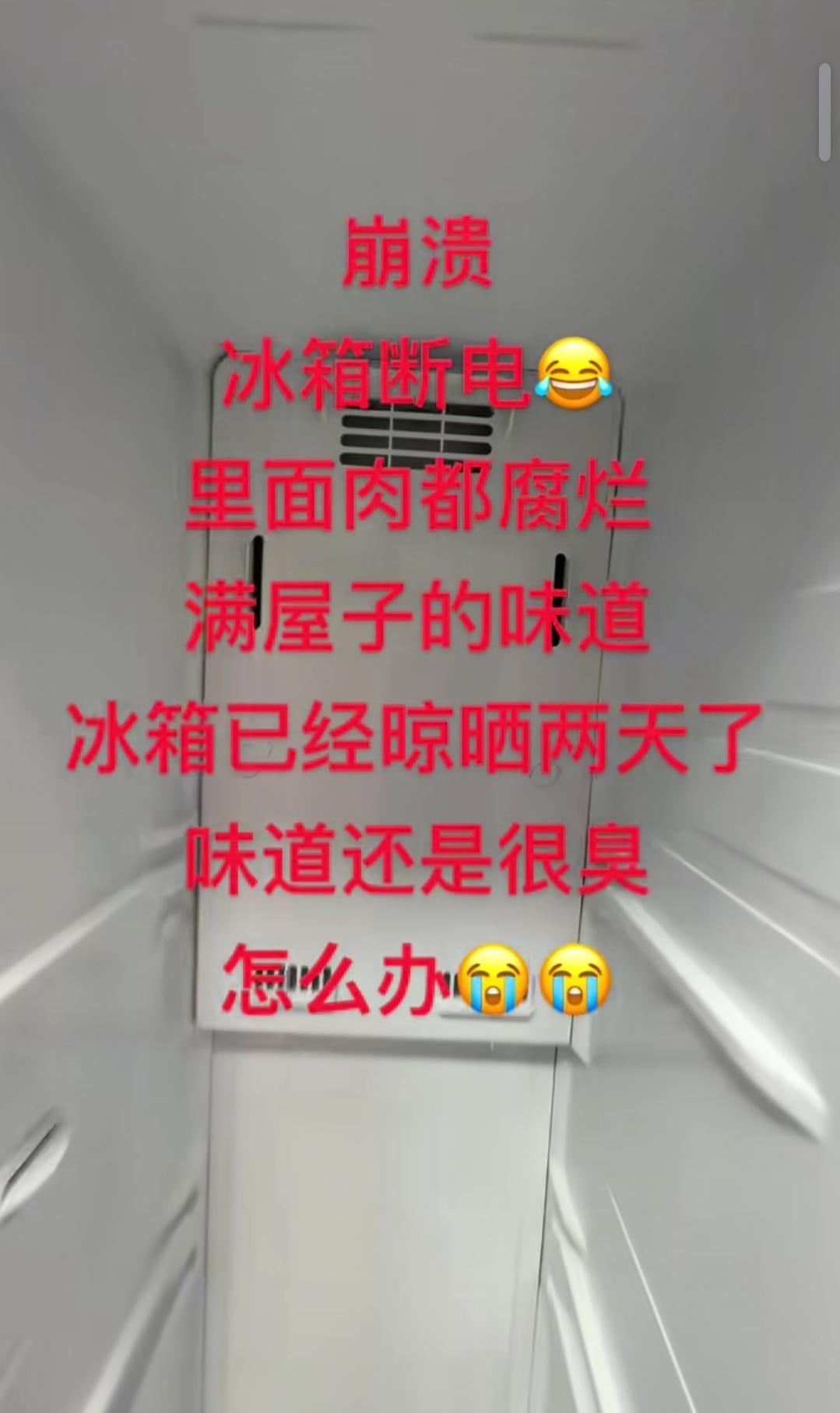看哭了!父母离异,女孩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,这天志愿者来她家里进行帮扶,看到女孩吃一锅不知放了多久的腌菜,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吃肉?女孩说:“因为肉太贵了,我们平时能吃上腌菜就很不错了!” 乡路绕着山转了十八弯,志愿者的帆布鞋沾着泥点,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,院子里晒着半干的青菜,竹匾边缘爬着霉斑,跟屋里飘出的咸酸味缠在一起。 奶奶坐在灶门口添柴,火光映着满脸皱纹,女孩蹲在矮凳上,捧着粗瓷碗扒饭,筷子头戳着锅里的腌菜。 那缸腌菜就放在桌角,陶缸没盖严实,边缘结着白霜,菜叶黄得发暗,看不出原本模样。 “丫头,吃的这是?”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忍不住问,女孩抬眼,睫毛上沾着饭粒,没说话,只是把碗往怀里拢了拢,奶奶叹口气,手在围裙上蹭了蹭:“秋天腌的,能吃到开春,这样省粮食。” 有人注意到灶台上的铁锅里,除了腌菜没别的,“咋不吃点肉?孩子正长身体,”这话问出口,院子里忽然静了,女孩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,声音轻得像风:“肉贵,腌菜挺好。” 志愿者摸出随身带的牛奶递过去,女孩没接,转头看奶奶,奶奶点头,她才双手捧着接了,指尖攥得发白。 屋里墙面上,贴满奖状,“三好学生”的字迹被炊烟熏得发淡,墙角堆着捆好的废品,是祖孙仨攒着换钱的家当。 奶奶说孩子爸妈很早便离婚,老头腿不利索,靠种半亩玉米过活,肉要去镇上买,来回二十里山路,逢集才舍得割一两斤,都给孩子留着。 志愿者翻开带来的物资袋,米面油之外,还有两包真空包装的肉肠,奶奶要推辞,被按住手:“这是爱心社统一配的,每个孩子都有。” 之后有人蹲下来帮女孩撕肉肠,油星子溅在她蓝布衫上,她抿着嘴笑,阳光穿过屋梁的破洞,照在腌菜缸上,白霜慢慢化了点。 志愿者里有人悄悄拿手机拍了腌菜缸和奖状,不是要博同情,是记下来,下次多带点肉和鸡蛋来,就像他们在别的山村做的那样,不光给物资,还教老人怎么给孩子做鸡蛋羹,不贵还补营养。 临走时,女孩站在门口挥手,风吹动她洗得发白的衣角,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肉肠,志愿者回头看,那口腌菜缸仍摆在桌角,但旁边多了袋新米,包装袋上印着的“爱心助学”四个字,在暗屋里亮得很。 这样的场景,在山区不算少见,老人们守着旧习惯省吃俭用,孩子们不懂营养只知懂事。 还好有志愿者翻山越岭送来的不光是吃的,更是让孩子知道,肉不是奢侈品,成长该有的营养和关爱,他们都配得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