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是美国,可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。为什么?江同志说,美国最终和我们达成协议,并不是突发善心。一方面我们的实力摆在那里,他们不让我们加入也不行。另一方面,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,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。 二〇〇一年冬夜,多哈会场里木槌落下,只用了八分钟就走完程序,中国成了新成员。 这条路不是心血来潮起步的。 一九八一年,纺织品配额谈判把现实摆在台面上。纺织品占中国出口三分之一,却不是缔约方,配额排不到名。硬着头皮入场,谈到一口“甜头”,才知道不在桌上就可能在菜单上。 一九八二年,外经贸部给国务院的报告把数字摊开:关贸成员的贸易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五,中国同这些成员的贸易也占到自身进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。 规矩像河里的水,不下水也要被冲。于是才有后面的申请与审议。 一九八七年,工作组成立,十月第一次开会,四万多个问题,针尖对麦芒地问到底“算不算市场经济”。 当时国内还沿用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说法,外方翻遍词典也找不到这个词。 车轮压在缝里,寸步难行。等到一九九二年,南方谈话之后,十四大把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写明白,审议阶段才算过关,谈判焦点移到关税、配额、服务业开放上。 美国从一开始就板着脸当“老大”。架势摆得足,价码抬得高,常用“滚动式要价”,口袋里还揣着制裁的大棒。 市场准入开谈那会儿,动不动就拿逆差说事,威胁十月之前不谈完就动手。 桌下小动作也不少。 一九九九年四月,朱镕基访美,原本要在那一程敲定双边协议,美国国内舆论嫌“让得太大”,贸易代表办公室竟然把未经中方同意的所谓“联合声明”连同十几页附件丢上官网,把对中方的要价全晒出来,像是要在舆论场上逼签。 那天晚上在拉德饭店的晚宴,朱迟到一小时,把“今天很糟糕”端上桌面。 白宫里杯盏碰得响,场外谈判像拉锯。 克林顿后来又打电话挽留,要求“最后修饰一下”,中方回了句“要谈来北京”,风向这才拐弯。 北京回合是硬仗,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,巴尔舍夫斯基落地,住在王府饭店。 按原计划两天收尾,第二天风色突变,美方抛出一揽子新条件,电信增值、寿险持股要到百分之五十一,汽车关税要快步压到二十五个百分点。 房间退了,行李往机场送,话也放得很重,像是要撒手走人。 只是十五日凌晨四点半,小范围工作会又如约开场,对方把几百页文本逐行逐标点校对,这种细密劲儿,分明是想签,只是把七个“最后问题”横在门口,非要中方全盘接住。 清晨九点半,电话打到中南海。朱镕基只问一句:“到底想不想签。”得到肯定判断后,当天下午亲自进场。先要龙永图把那七条写在纸上,前面几个当场拍板同意,让步的分寸摊到光底。 后面几条,直言要对方退一步,“退了就签”。 美方短暂停顿,五分钟后点头。十六时,中美双边协议签下。 那头的斯珀林在外经贸部一间女厕所里拨通电话,向克林顿报喜,像打完一场世界级拳赛。戏剧味足,但每一步都不是巧合,是十五年护理出来的窗口期与彼此算账的交点。 态度上的交锋远不止这一场。 进出口检疫讨论时,美方代表抛出“连做狗粮的检疫都过不了”这种刺耳的话。 龙永图当场拍桌,要求道歉,不道歉就散场。对方愣了,吞回去认错,还解释说在本国狗与人同等。这个插曲没有改变条文,却把底线划得清清楚楚。 否则谈的不是规则,而是尊严被踩的方式。 类似的火星子在那几年并不稀罕,真正有效的是中方那句老话:复关入世不是“不惜一切代价”,国家根本利益不拿去换门票。 一九九五年一月,世贸组织取代关贸,同年七月十一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申请,复关变成入世。这个节点之后,中国另辟侧翼,先与其他成员打通通道。 一九九七年八月,新西兰第一个签下双边协议,同年韩国、匈牙利、捷克陆续落笔。 美国还端着架子,别人已经陆续开门,这种“侧攻”把谈判的重心悄悄挪动了几分。 门进来了,承诺就要兑现。 关税从二〇〇二年起全面下调,到二〇一〇年完成承诺,总水平从百分之十五点八降至百分之九点六,四百多项非关税措施取消。 汽车关税,大排量从一百个百分点、小排量从八十个百分点降到二十五个百分点。服务业的门扇开得更大,外资银行可以给企业和个人办理人民币业务,外国律师事务所设代表处不再限地域、限数量。 二〇〇〇年海关法修订,确立中央垂直领导和综合打私体制,执法和通关与国际标准接起扣子。 入世过渡期,全国层面修改两千二百多项法律法规,地方清理近十九万件地方性文件,规矩往一处靠,市场才有章法。 外贸数据像坐电梯。 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二〇年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万三千四百亿美元蹿到十五万三千亿美元,世界排名从第六走到第二。 进出口总额从五千多亿美元扩大到四点六二万亿美元,占全球贸易的百分之十一点七五,真正成了“全球第一贸易国”。 中国在这个盘子里不只是受益者,也变成了盘子本身的支撑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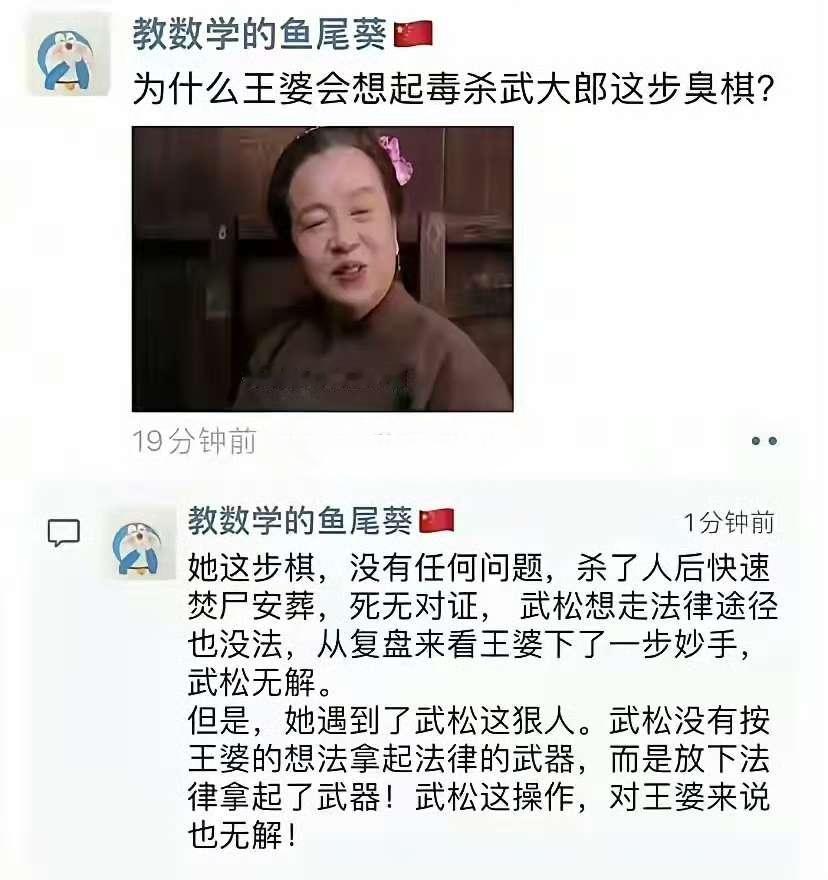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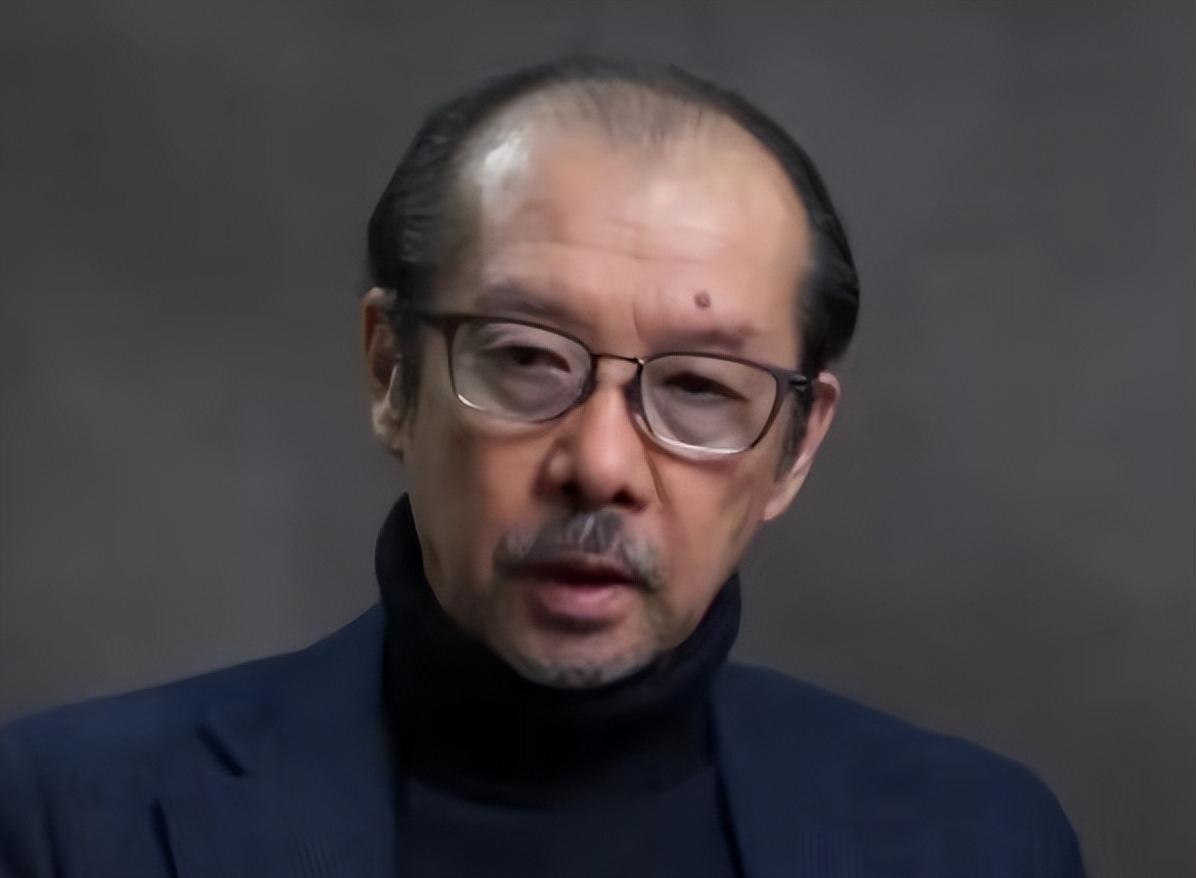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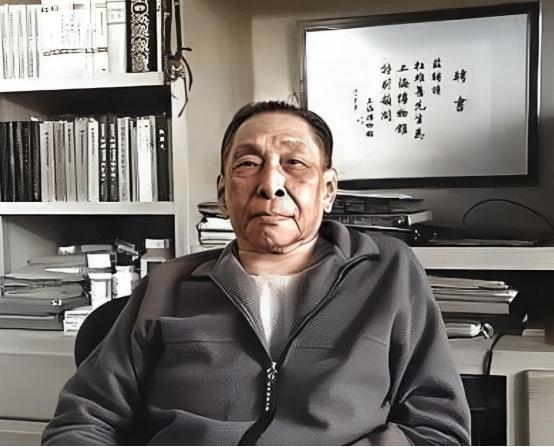

韭菜鸡蛋
感谢拉登
东方先生
美国一直后悔当初准许中国加入世贸,虽然我们有相当实力,但如果老美坚决阻止,也是没办法的,不得不承认,加入世贸后,我们的发展很快,进步很大,实力大增!
天路 回复 12-29 16:15
不入世一样可以卖东西,那样就需要一个个个国家谈,或者中国定个规矩来交易,或许慢一点些但这样就脱离了美国的掌控,美国怕的就是这个
替天行道 回复 01-04 12:32
得了吧中国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让他们资本家赚翻了!iphone99%的利润都是他们拿走了
十三月十七日
克林顿:一开始我以为占了个大便宜……
用户18xxx18
克林顿最后悔的事!
用户18xxx15
当年大陆和台湾同时入世,大陆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,台湾以发达地区身份入世
8421706
老百姓吃饱饭也就是加入世贸之后,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
树苗
九五年才是变化的关键点,我们班和下一届同学穿衣方式就明显不一样了,再下一届衣服更新更时尚,食堂顿顿有肉吃,只是量少点而已,久久年就可以每个月点盘炒菜了,少年的回忆啊
烏尼單刀貓貓須
94~95年最关键,我家不挨饿,有余粮了,从此越来越好
用户20xxx65
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不断解放生产力,发展生产力
用户10xxx51
一场马拉松谈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