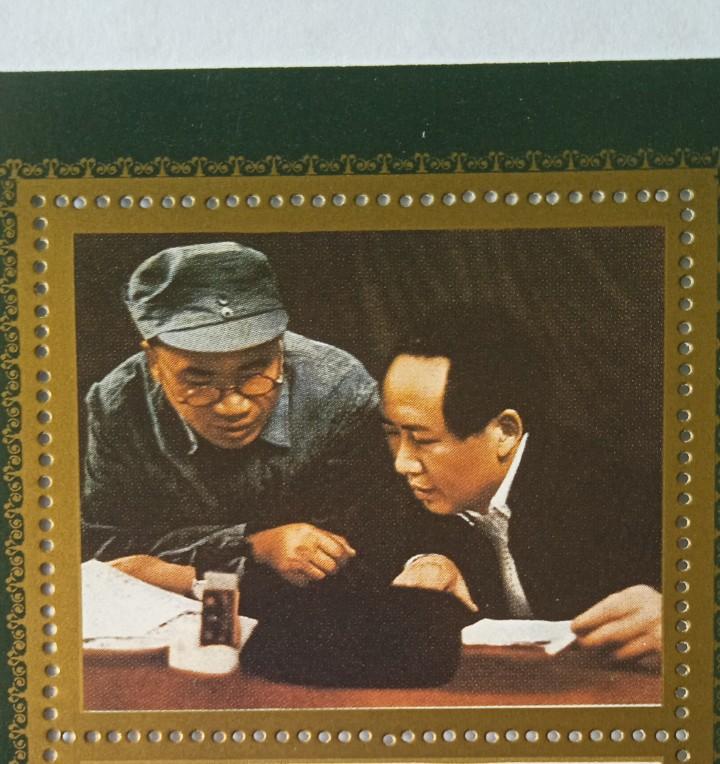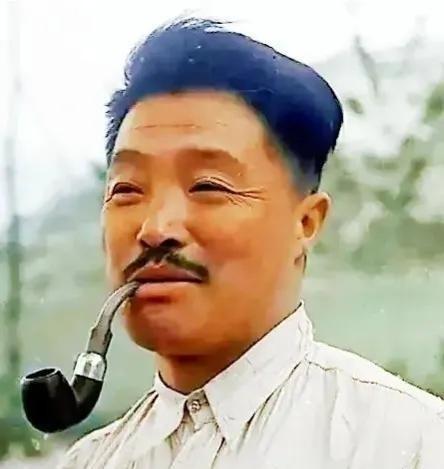其实,老蒋就是遇到毛主席了。如果他不是遇到毛主席,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他不遇到毛主席,别人还真干不过他。他遇到毛主席,那他就完了! 一九四七年,陕北的天刚蒙蒙亮,胡宗南的大队人马正往北压,电台里一封接一封,报上去的数字挺好看。十五个旅,十四万多人,再加上马鸿逵、马步芳、邓宝珊那几路,凑起来三十四个旅,差不多二十五万。 蒋介石看着这些数字,心里挺舒坦,觉得这回总算能在延安这块地方翻一把身。 那时候在南京,他已经把话说死,延安是“匪都”,是“右臂”,拿下来,政略上好看,外交上也好看,等于在国内外面前把中共打了一记闷棍。 在他眼里,棋盘摆得很清楚。先一口气砸向山东和陕北,把近七十万兵力压上去,陕甘宁这块先咬断,党和军队的“右臂”一掐,再逼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往黄河以东跑。 等这些人被赶到华北那边,再找机会集中主力打决战,把解放区一个个捏碎。中共中央那边看得也明白,文件里早就点穿,说国民党打延安,是想先收拾西北,再驱逐党中央出西北,继而调兵进攻华北,“各个击破”就是一整套盘算。 蒋介石心里打的主意挺自信,陕北这边的现实却有点骨感。 守延安的边区部队,算来算去也就二点六万人,轻重武器都比不上胡宗南那边。三月十二日,国民党空军先给延安“开路”,炸弹一排一排落下来。十三日上午,十五个旅分两路压上来,炮火一响,尘土飞起,城里的窑洞都跟着轻轻发抖。 就在外面声音闹腾的时候,三月二日定下来的一个决定已经悄悄在执行,那就是紧急疏散。 延安在共产党人心里不是个简单的地名。 十几年风里来、土里去,很多人的人生,都是从黄土坡下那口窑洞拐了个弯。 是不是硬扛到底,要不要撤,这个选择不只是地图上的小红圈。三月十八日,胡宗南的部队逼到城郊,中共中央在王家坪那排窑洞里开会,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。 毛主席早几天就把话说得很直,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,新四旅的程悦长和袁学凯赶到延安,听到的是一笔“明白账”。 一边,是很多地方来电催他过黄河,说那边更安全,指挥全国战争也方便。另一边,他自己有两条心思。第一条跟感情有关,在延安和陕北十多年,一直是老百姓护着革命,现在枪一响就往远处跑,以后再见面脸上也挂不住。 第二条属于战略算账,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,陕北只有两万,把敌人的主力拖在这里,黄河以东几个解放区就能轻松一点。 他负责全党军事工作,不在陕北,谁来压住“西北王”。 三月十八日晚,炮声渐渐近了,彭德怀几次催他赶紧撤,他只是抬手压一压,照样把饭吃完才起身。 那晚离开延安的时候,城里机关和群众早就已经撤空,只留下掩护部队在外边周旋。 从军事角度看,这个“走”,并不是认输一巴掌。 毛主席在撤离前跟新四旅的干部谈话时,摆出了自己的标准,城可以不要,人不能丢,“存人失地,人地皆存;存地失人,人地皆失”。夺城只是表面风光,拿不下对方的有生力量,早晚要还回来。他还说,胡宗南进延安像握着拳头冲上来,进城之后就得把拳头一指一节地伸开,守城、守路、守后方。 拳头一摊开,就好找机会一块块剁。 蒋介石那边没有这么想。他在日记里写“收复延安对政略、对外交,皆有最大意义也”,胡宗南更是在城里摆拍,宣传“陕北大捷”。 看上去风光,代价却越来越重。 大量部队深插陕西腹地,补给远,战线长,一路都是负担。延安成了要捧在手心的“战利品”,转身都不灵活。 和进延安的“大捷”相比,中共中央接下来的选择就显得有点“反常”。 正常思路,敌人兵力压上来,领导机关怕出危险,会赶紧撤远。可枣林沟那次会上,讨论出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。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带着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,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,去晋西北或者其他合适地方主持工作。 有人主张全部东渡黄河,任弼时就很担心安全,反复劝。 毛主席一句话压上去,说“我不能走,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”,他走了,中央走了,蒋介石肯定会把胡宗南抽到别的战场去,中原和华北就要吃大苦头。 这一下,帅旗就等于插死在陕北了。习仲勋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安塞真武洞的大会上,当众讲明白,敌人造谣说中共中央、西北局、边区政府都跑了,那是做梦。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还在边区指挥,这句话一出,台下心里的那口气就有了着落。 士气这种东西,看不见摸不着,边区老乡听到“毛主席还在这块”,干活打仗的劲头就不一样。 从那以后,就是一年零五天的“转战陕北”。 多年以后,台湾一九五九年编写的《戡乱战史》,也不得不在纸上认输几句,说西北战场上,共军凭借严密的情报封锁和灵活的小后方补给,“避实击虚,钻隙流窜”,国民党主力被牵制在陕北,“一无作为,殊为惋惜”。这种话,从对手嘴里说出来,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分量。 有人说,老蒋是遇上毛主席才输了。 话里有夸张,也有几分实在,棋下得再认真,走错一步关键子,就得一路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