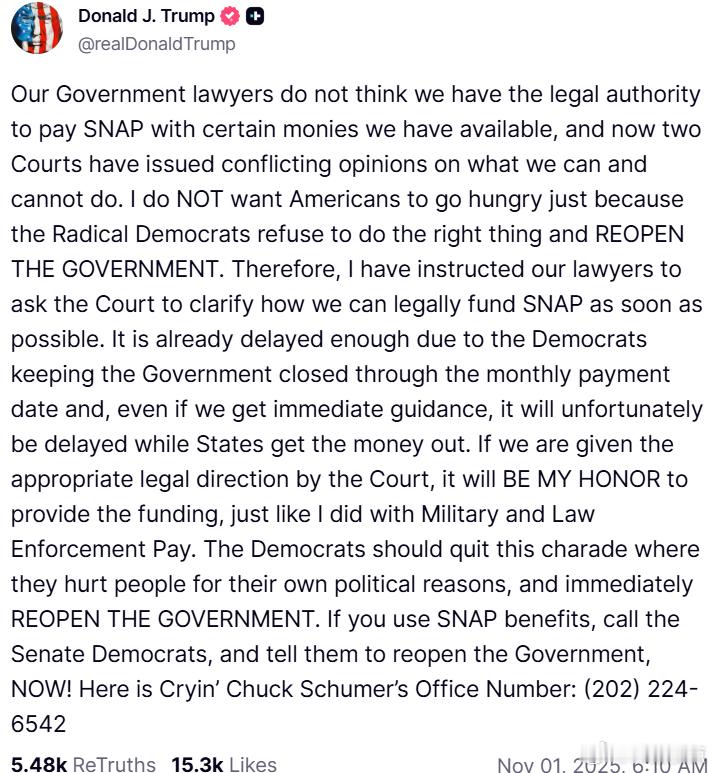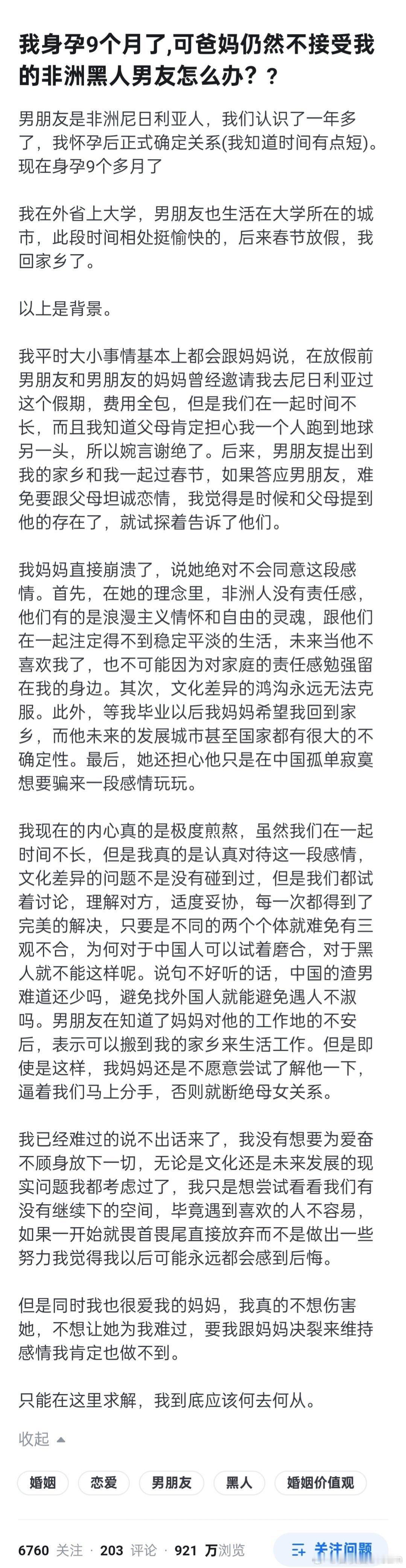新加坡这个国家,再从李光耀开始就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,那就是这么一个500平方公里微不足道的地方,养成了对其他大国以及世界形势,指指点点的毛病。 新加坡这点5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,能从建国初期的困境里活下来还活得不错,确实是李光耀当年踩准了冷战节奏的功劳。 冷战时期的东南亚被美苏两大阵营撕扯,新加坡夹在中间没资源没纵深,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吞噬。李光耀很清楚,单靠自己根本站不住脚,必须靠着对大国博弈的“点评”刷存在感、谋生存。 他一边抱紧美国大腿,允许美军在新加坡设立军事基地,让美国的力量扎根东南亚制衡苏联,一边又让苏联进入新加坡,完事之后还不忘拉着中国,在1976年第一次访华时处处谨慎,全程用英语交流刻意拉开距离,就怕邻国把新加坡当成“中国的特洛伊木马”。 更显眼的是,他总爱在国际场合对地区格局指手画脚,1973年在渥太华抛出“大象与草地论”,把大国争斗比作大象打架,看似是替小国诉苦,实则是借着这种论调让美苏都注意到新加坡的“平衡者”角色—毕竟只有让大国觉得这个小国能传递信息、调节氛围,才会给它留出生存空间。 这种靠着发声绑定大国的套路,让新加坡在冷战里活了下来,也让自己从一个小国成为了这些西方国家的“中间人”,不过同时,他们那“指点江山”也成了生存本能。 冷战结束后,没了阵营对抗的压力,新加坡这习惯非但没改,反而变本加厉,因为它发现这种方式能换来远超国力的影响力。 李光耀晚年更是直白,2009年直接跑到华盛顿的美国—东盟商业理事会晚宴上喊话,说美国必须继续留在亚洲制衡中国,不然就会失去世界领先地位。 这番话当时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,新加坡媒体急着辩解是“被误解”,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就是新加坡刻意通过点评中美关系,巩固自己“地区代言人”地位的手段。 毕竟对新加坡来说,只要大国之间有制衡、有博弈,它这个“传声筒”和“调解员”就有价值,这种靠对大国事务表态获取存在感的路数,早就成了外交基因。 李显龙上任后,把这套玩法学了个十成十,甚至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频繁地“开口”。 这些年他跑遍各种国际论坛,一会儿说台湾问题是亚洲“闪点”,呼吁各国别介入,看似理性实则在中美之间摆姿态,甚至还说,中国不要再走“自给自足”路线;一会儿又对美国的关税霸凌指手画脚,说要是美国破坏贸易体系,各国就该另起炉灶建新体系。 更耐人寻味的是,他曾在访美时拿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开玩笑,被美国媒体质疑后又赶紧圆场,说公开批评中国不明智。 这种左右摇摆却又处处表态的做法,本质上和李光耀当年的路数一脉相承——明明经济上早就靠中国市场拉动,贸易额远超对美贸易,却非要在政治安全上对着大国事务说三道四,既想靠美国的军事存在求安全,又想靠对中国的“点评”刷分量。 说到底,新加坡的这套习惯,根源是小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生存焦虑,但焦虑不能成为对大国事务指手画脚的理由。 李光耀当年靠发声在冷战里站稳脚跟,是特殊时代的无奈之举,可冷战结束后,李显龙还抱着这套不放,动不动就对中美关系、地区热点说长道短,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了。 毕竟再怎么“指点江山”,新加坡也改变不了自己弹丸之地的本质,与其把精力放在对大国事务的评论上,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