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,重庆某殡仪馆在夜晚接收了一具9岁男孩的遗体,当李师傅为其冷冻时,他惊讶地发现男孩的眼皮似乎跳动了一下,于是,他急忙检查男孩的心跳,竟然发现男孩还有呼吸! 这故事的主角,是个才9岁的小男孩,叫刘峻成。2016年4月,小峻成在合川区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,还是个小学三年级的娃娃。本来是个活蹦乱跳的年纪,可悲剧来得毫无征兆。那天,他在宿舍里突然摔倒,手脚发软,动弹不得。家里人赶紧把他送进大医院,结果被诊断为“颅内出血”。 这四个字,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,都像是天塌了一样。小峻成的爸爸刘茂贵当时还在广东打工,听到消息,心急如焚地往回赶。可他赶回来的,却是一个让他肝肠寸断的结果——经过全力抢救,医生们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心电图已经成了一条直线,孩子没救了。 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是人世间最深的痛。在签下了一系列文件后,悲痛欲绝的家人只能按照流程,将小峻成的“遗体”送往了殡仪馆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,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。 在殡仪馆,负责接待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,咱们就叫他李师傅。李师傅在这行干了小二十年,见过的生离死别太多了,心情早已沉静如水。他按部就班地准备着冷冻前的最后工作。可就在他准备把孩子推进冷冻柜的那一刹那,他下意识地多看了一眼。 就是这一眼,让他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 他感觉,孩子的眼皮,好像轻轻地动了一下。非常非常轻微,就像是幻觉。换做个马虎点的人,可能就以为是灯光晃的,或者是自己累眼花了。但李师傅没有。职业的严谨和内心的那份敬畏,让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他探下身子,把手指放到了孩子的脖颈动脉和鼻尖下。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几秒钟后,李师傅猛地抬起头,冲着外面用尽全身力气大喊:“快!快来人!这孩子还有气儿!他还活着!” 这一声喊,划破了殡仪馆夜晚的宁静,也喊出了一线生机。整个殡仪馆的人都惊动了,谁都没想到,这个已经被医院宣判了“死刑”的孩子,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一站,展现出了求生的迹象。救护车再次呼啸而来,载着这个小小的身躯,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 回到医院,医生们也是难以置信。经过检查,小峻成虽然生命体征极其微弱,但确实还有心跳和呼吸!新一轮的抢救立即展开。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捏了一把汗。而这一次,奇迹真的降临了。经过治疗,小峻成不仅活了下来,后来还慢慢恢复了意识,能够开口说话,自己吃饭。 一个已经被放弃的生命,就这么硬生生地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。这事儿当时在重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大伙儿都说,这孩子命大,也多亏了那位叫李师傅的工作人员,他的“多看一眼”,简直就是现代版的“一眼百年”,一眼就救回了一条命。 聊到这,你可能会问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是医院误诊了吗? 其实,这背后涉及到一个在医学界虽然罕见,但确实存在的现象——“拉撒路综合征”(Lazarus Syndrome)。这个名字来源于《圣经》里一个被耶稣复活的死人“拉撒路”。医学上用它来形容病人在心肺复苏失败、被宣布临床死亡后,出现自主循环恢复的罕见情况。简单说,就是“死而复生”。 从1982年首次被医学文献记载以来,全球有记录的案例并不多,但每一次出现,都足以挑战我们对死亡的传统认知。根据一些较新的医学回顾研究,比如发表在《急诊医学杂志》上的一些分析指出,这种现象可能与抢救时使用的药物延迟生效,或是胸腔内压力变化等复杂因素有关。 科学家们有一种猜测,在某些极端的创伤情况下,人体会启动一种深度的自我保护机制。身体的各项机能,比如心跳、呼吸、新陈代谢,会降到一个“仪器都难以检测”的水平,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“假死”状态。这时候,外界的某些刺激,比如身体的移动,甚至是像小峻成这样,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的温度变化,都有可能成为重新“激活”生命系统的那个开关。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,说是一个同样是颅内出血的孩子被送往殡仪馆,结果救护车路过一段颠簸的路面,剧烈的震动竟然意外地将他颅内的血块给“颠”开了位置,减轻了对脑组织的压迫,孩子因此恢复了生命体征。这些故事听起来玄之又玄,但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:生命本身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和复杂。 小峻成的故事,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。 首先,是对所有医护人员和生命最后一站的工作者的警醒。我们现在依赖各种精密的仪器来判断生死,心电图、脑电波……但任何仪器都有它的局限性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多一份细心,多一份责任感,可能就会创造一个奇迹。李师傅的那份“多此一举”,恰恰是人性中最光辉的善良和严谨。 其次,这件事也推动了医学界对于死亡判定标准的不断探讨和完善。尤其是在器官捐献日益普及的今天,如何精准、无误地判定一个人的死亡,既关系到对逝者的尊重,也关系到等待移植者的生命。小峻成这样的案例,就像一个警钟,时刻提醒着我们,在“生命”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,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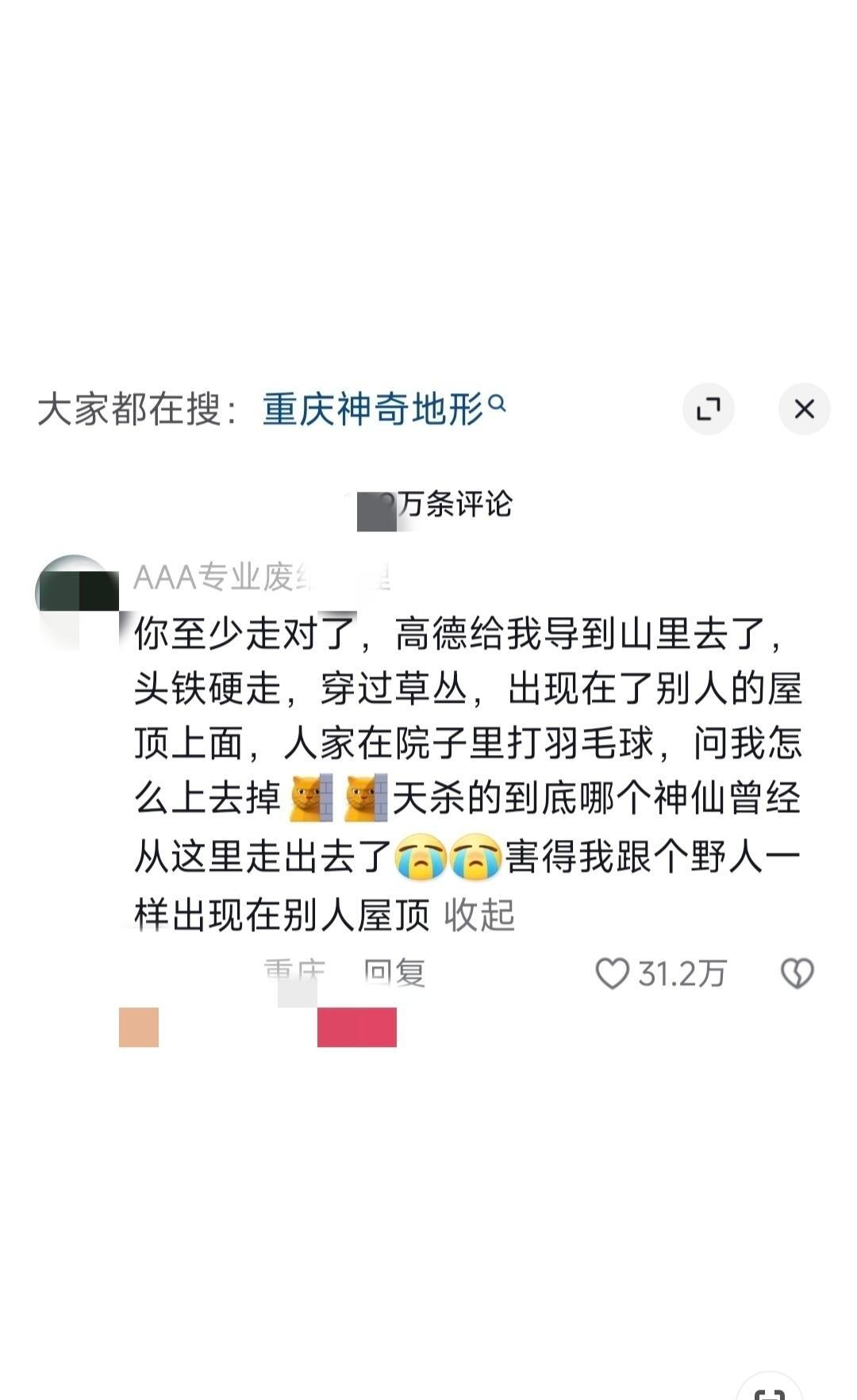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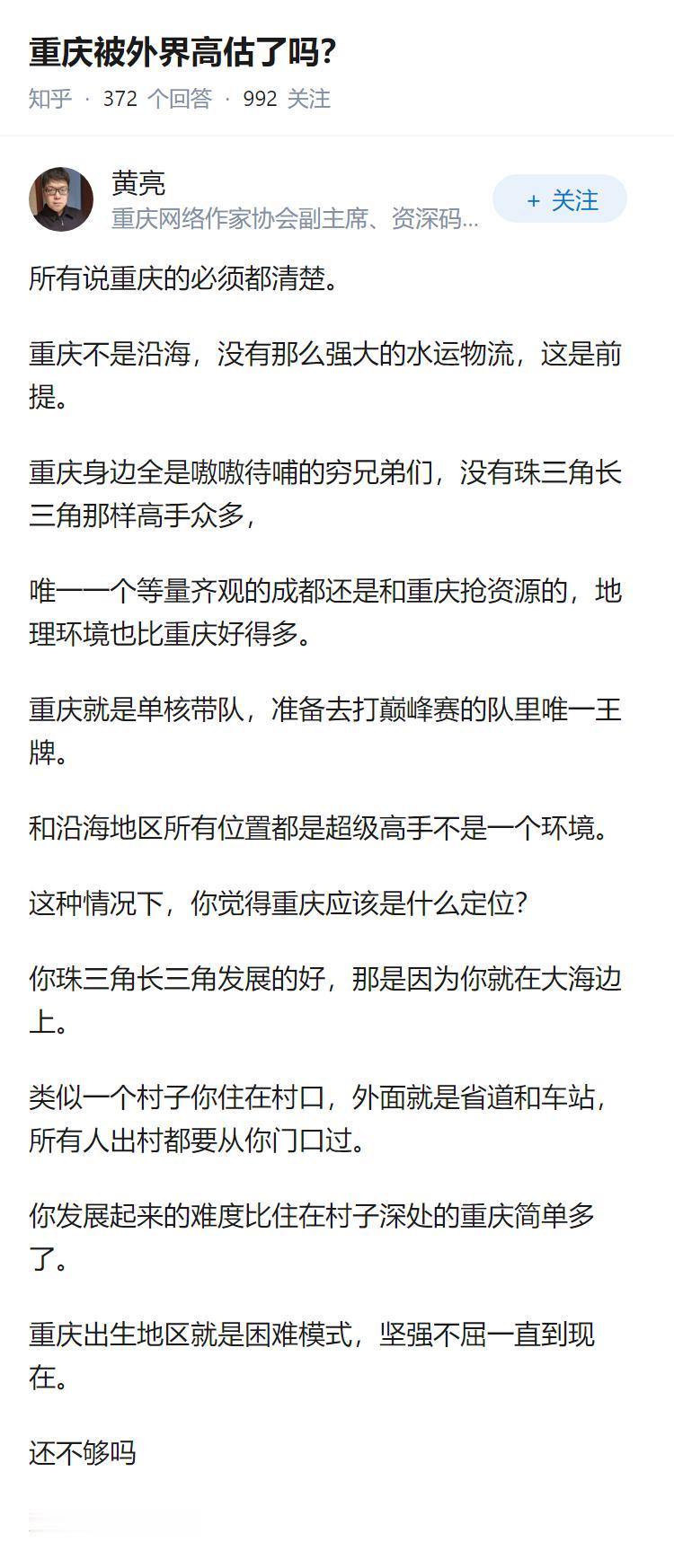





漫步人生路
职业道德拯救了小生命
刚刚
所以古人要停尸七日
用户10xxx63
说明停尸数天还是有道理的。
用户10xxx64
…别忘了救命的恩人…[点赞]
叶红
必须给李师傅点赞
外乡人
你以为以前为啥要停尸几天?小时候听老人讲,有有入殓后,在进行道场法事期间醒了敲棺材,后来还活了好多年的
用户10xxx17
当时医护人员应该判死刑
宝幢开心小帅哥 回复 10-11 20:54
假死!没办法
用户10xxx32 回复 10-15 03:56
从医学上来说当时已经死了,怨不得医生。假死也是死亡,其实事后复活也不是好事,心脏和肺部停止工作,半小时后就算恢复工作,大脑也扛不住损伤,生不如死的活着,对家庭是一个巨大的负担,对自己(正常时的自己)也是一个屈辱
用户18xxx10
必有后福
毛不亦
所以古人是对的要停尸几天吧,现在直接给你火化
j风轻云淡
医院医护人员全部判刑,或警告处分。
宝幢开心小帅哥 回复 10-11 20:54
假死,也看不出来的
学无止境
现在停尸都是直接进冰棺,已经没有万一成活的所有可能了。
仅代表个人观点
敬畏生命,祝师傅长命百岁。
萌猛大逗比
犹如再生父母。。。
用户10xxx93
我6岁时中毒了,经过全力抢救没有任何反应(有生命体征,但是很弱,也没有恢复的迹象)医生已经放弃了,让先放到走廊连椅上,看造化吧,结果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就醒过来了,就是那种直接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,问家人我在哪里,我是怎么了?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那时候农村小孩因农药老鼠药中毒的很多,基本上像我这种程度的基本上都救不活了
墨公 回复 10-15 06:09
那时农药“乐果”中毒,用“阿托品”抢救不成功,但回家途中或回家后活过来不在少数,后来才知是阿托品后效应,此后这种事基本没有了。①乐果不用了,②医生知道了。
用户12xxx61
如果殡仪馆工作人员粗心点 ,不死也被冻死,需要改的地方怎么没有砖家叫兽出来叨叨。
天高海阔
穿越成功,如果这小孩有后福,必然能提升人类对穿越的研究程度
打铁
所以说世事无绝对
江河源
旧时:停尸7日 是有道理的
用户10xxx07
这样的人都有后福,祝愿孩子健康快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