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射死刑:表面的人道,实则的酷刑? 注射死刑的出现,源于人类对 “更体面终结生命” 的探索。 1982年,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查尔斯·布鲁克斯成了第一个“尝试”注射死刑的人。 8分钟后,他死了。过程看起来平静,没人听见尖叫,也没看见血。但这套“程序”,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他好。 这事最早能追溯到1888年。一个叫朱利斯·布莱尔的纽约医生琢磨,绞刑太残忍了,不如打一针来得“体面”。 想法提出来没多久就被压下去了,说白了,那时候没几个人在乎犯人的“感受”。 直到1977年,一位叫查普曼的法医在俄克拉荷马州拍了桌子。 他不是医生,但他给出了“标准流程”:生理盐水打底,接着是巴比妥酸盐让人失去意识,然后肌肉松弛剂让人不能呼吸,最后氯化钾让心脏停跳。 听起来像麻醉手术,但结局是死亡。 第二天,得克萨斯州立法照搬。五年后布鲁克斯上了注射台。从那以后,全美37个州都跟进了。 中国这边,1997年3月28日,昆明四名毒贩被推进了一个陌生的房间——干净整洁,还有个白床单。 32秒、35秒、40秒、58秒,四个人在一分钟内被“悄无声息”地处理掉。这是中国第一次用注射死刑。 那天之后,很多地方开始试点。昆明、南京、成都、北京、长沙……移动注射车也上线了,像救护车一样,把“执行”送到偏远地区。 但说到这你可能以为,这种死法“人道多了”。其实没那么简单。 问题来了,药物真的一直都有效吗? 2014年,美国亚利桑那州,约瑟夫·伍德被执行注射死刑。那天因为药物短缺,改用了一种新组合。 他在注射后挣扎了接近两小时,尸检显示,他全程意识清醒,等于活活被“溺死”。 2016年,俄亥俄州又出事了。丹尼斯·麦圭尔因为镇静剂浓度不够,在台上挣扎了25分钟,像是被罩住头在水里窒息。 这不是个例。吸毒者、慢性病人、胖子……身体差异会影响药效。医生不是法官,法医不是麻醉师,操作失误一出,后果谁也兜不住。 而且最可怕的是,第二针泮库溴铵会让人完全动不了,哪怕你痛到极致,也喊不出来。就像活人被封在棺材里,外面的人还以为你“睡着了”。 有人会说,枪决不是更可怕?其实也不一定。注射死刑没有血,没有补枪,但也没有声音。它看起来平静,其实可能更残忍。 中国的做法是两种并行。法律没明确标准,枪决还是注射,得看当地条件、案件性质,甚至民愤程度。 所以才有争议,说“贪官都用打针的,太便宜他们了”。不无道理。 一台移动注射车200万,一次药物300块,对经济不好的地区压力不小。 像云南、河南、山东、辽宁这种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,才普遍推行注射。其他地方,枪声还没停。 但也不是没人支持。注射死刑避免了血腥场面,家属不至于接受不了;遗体完整,方便火化、捐献、甚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 更重要的是,这符合“国际趋势”。中国最高法院说了,这是刑罚人道化的体现。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也说,这是文明进步的一步,“我们要告别以杀止杀的野蛮时代。” 但现实是,文明和公正,有时候走不到一块儿去。社会上不少人觉得,死刑就该痛,才能解气。有人甚至建议:按罪行严重程度来选执法方式。 这话听着扎心,但不是没道理。比如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老大,跟贪点钱的贪官,难道死法能一样? 这个问题,目前没有答案。因为它没法用法律、技术、甚至道德去衡量。它关乎人性,是惩罚还是复仇,是正义还是报复,全看你怎么看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——注射死刑绝不是你以为的“睡一觉就走了”。 它外表平静,内里复杂。它不是简单的“更人道”,而是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在“如何结束生命”这件事上的艰难选择。 说到底,死刑不是重点,怎么死才是。 而注射死刑,这种看起来最文明的方式,或许恰恰藏着最深的残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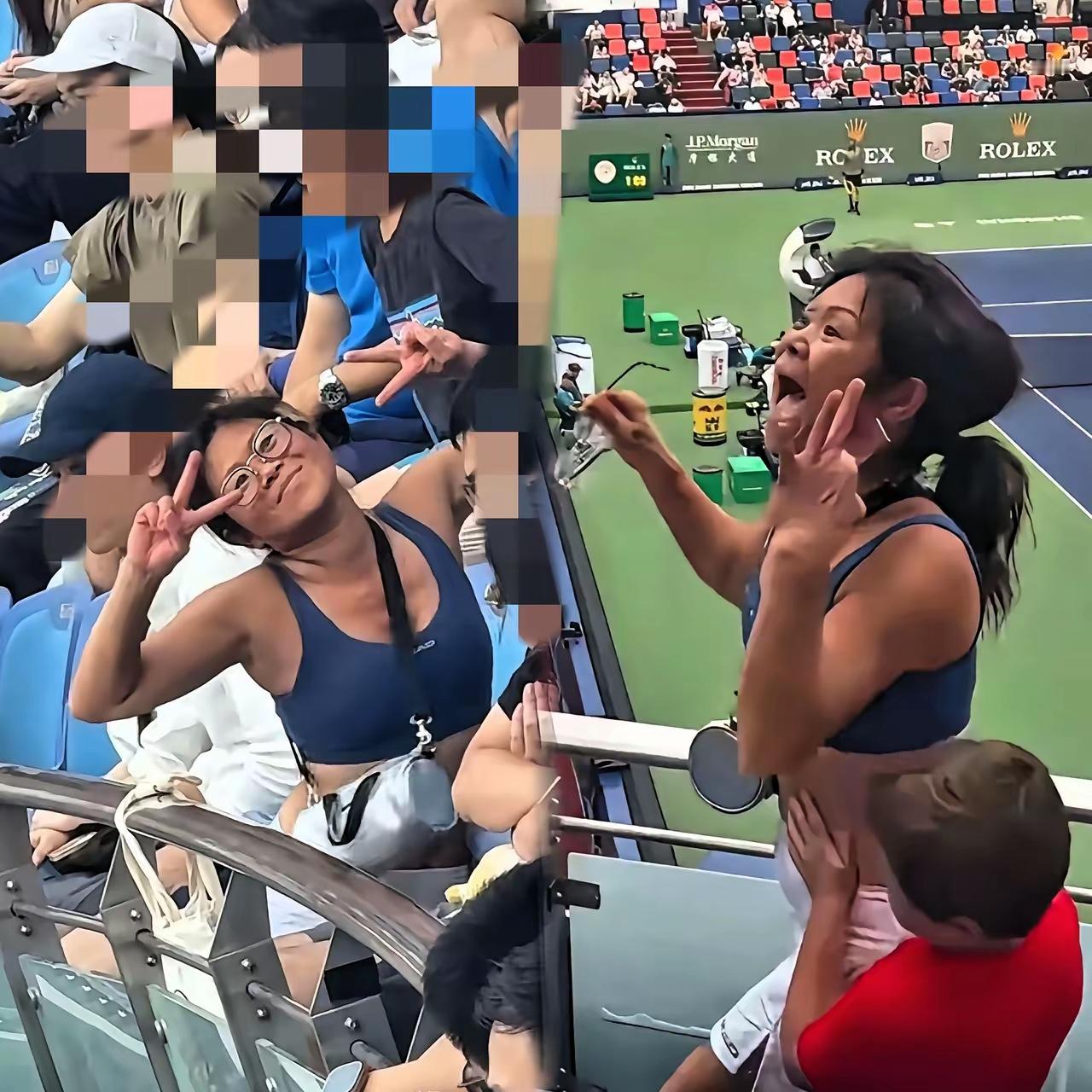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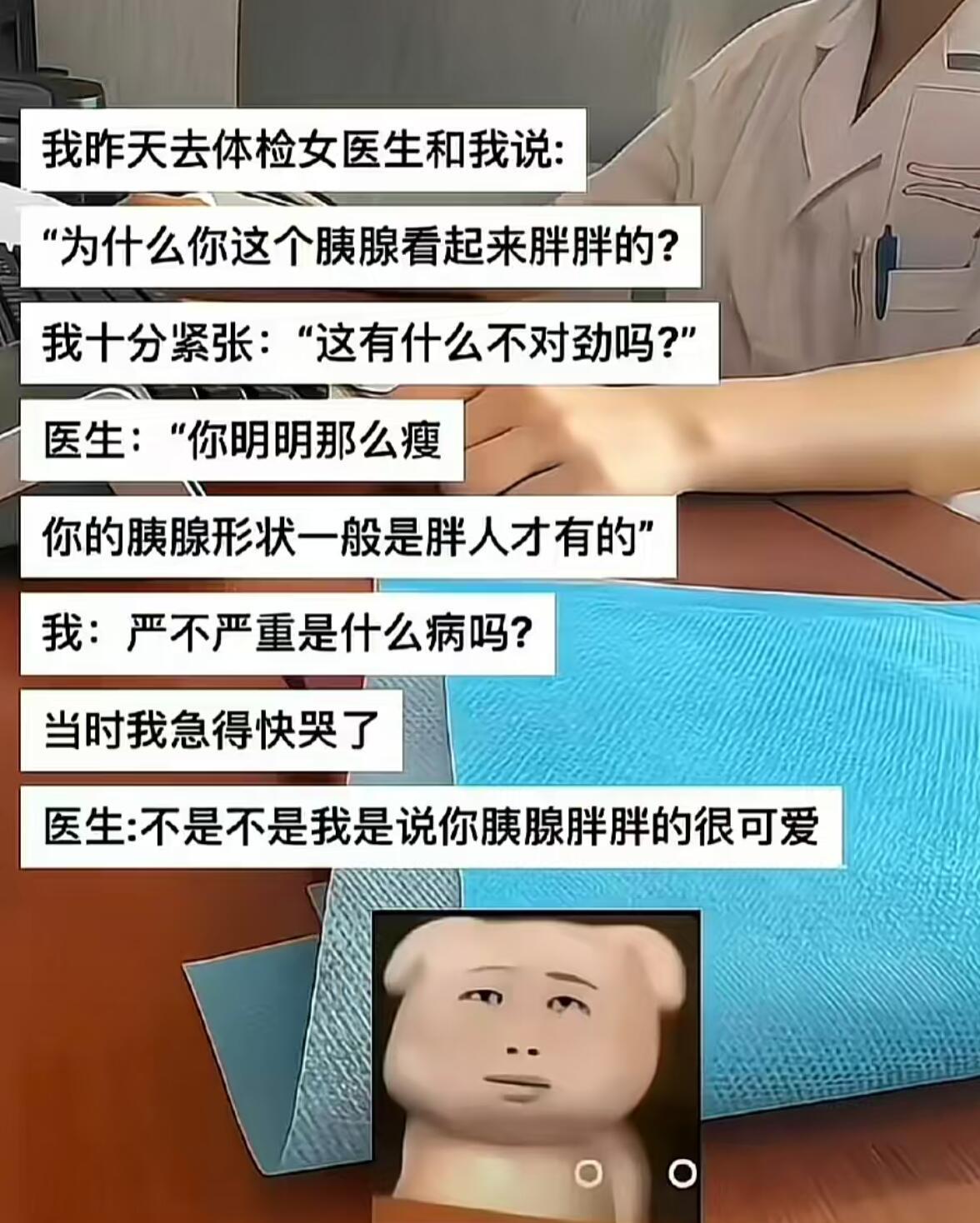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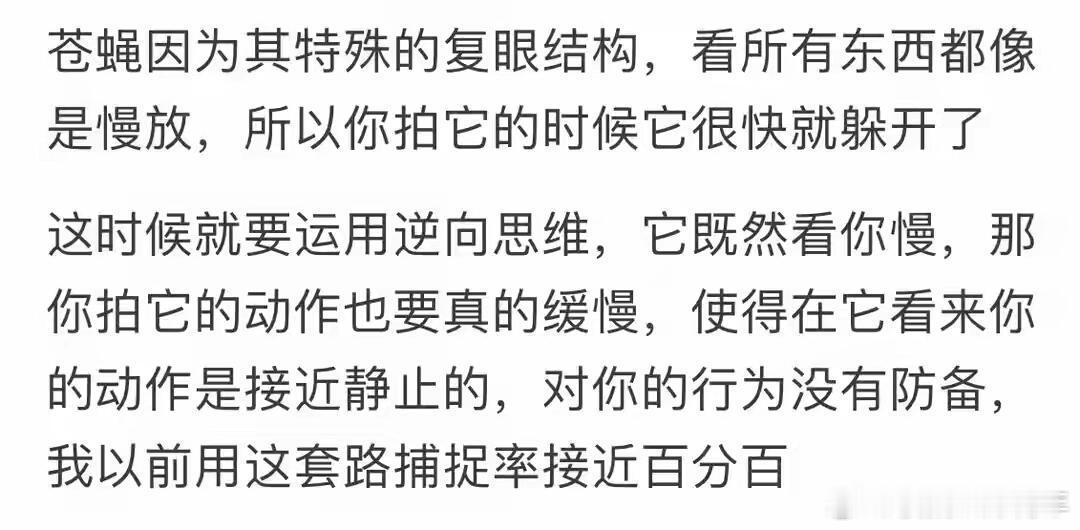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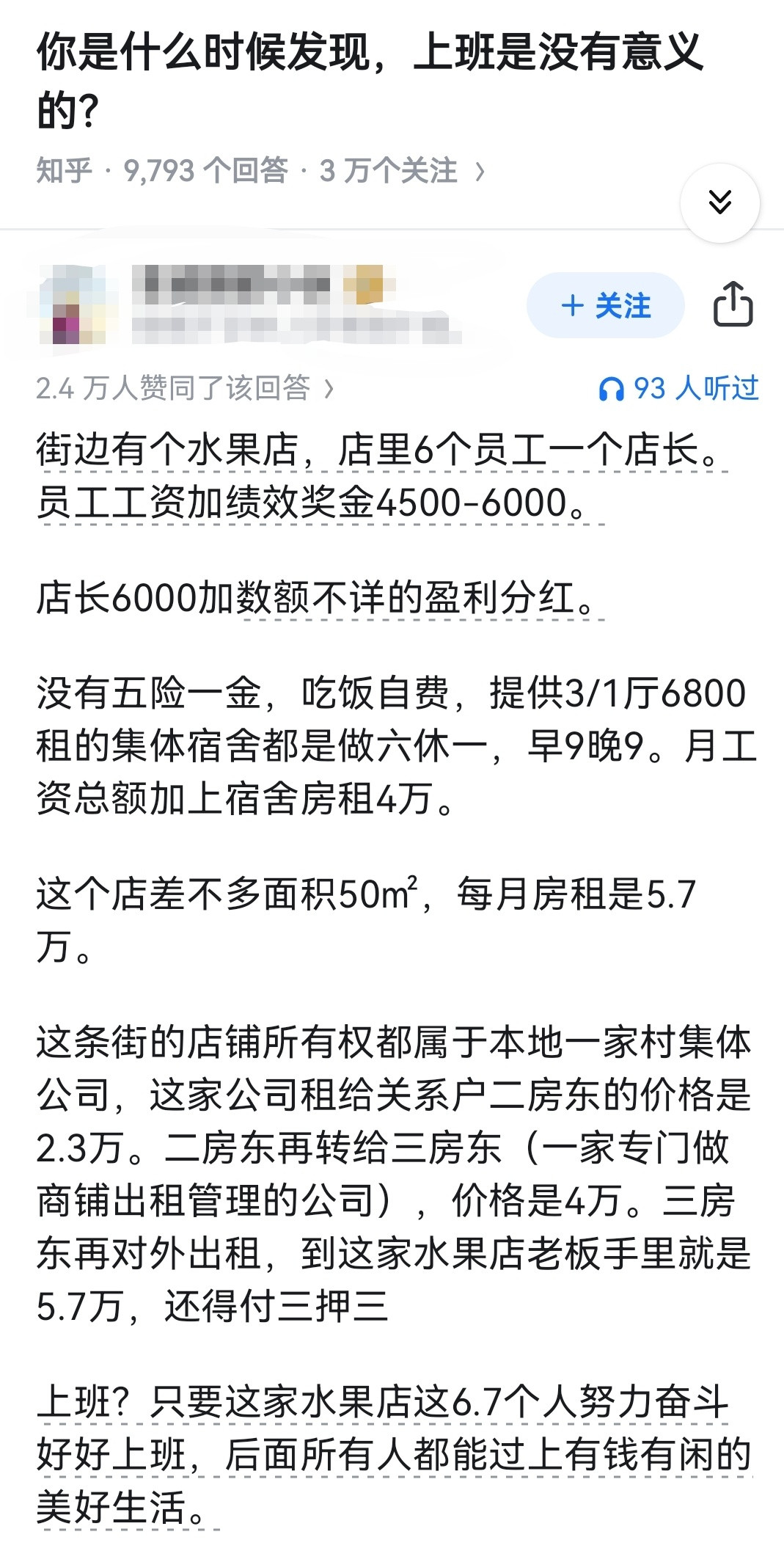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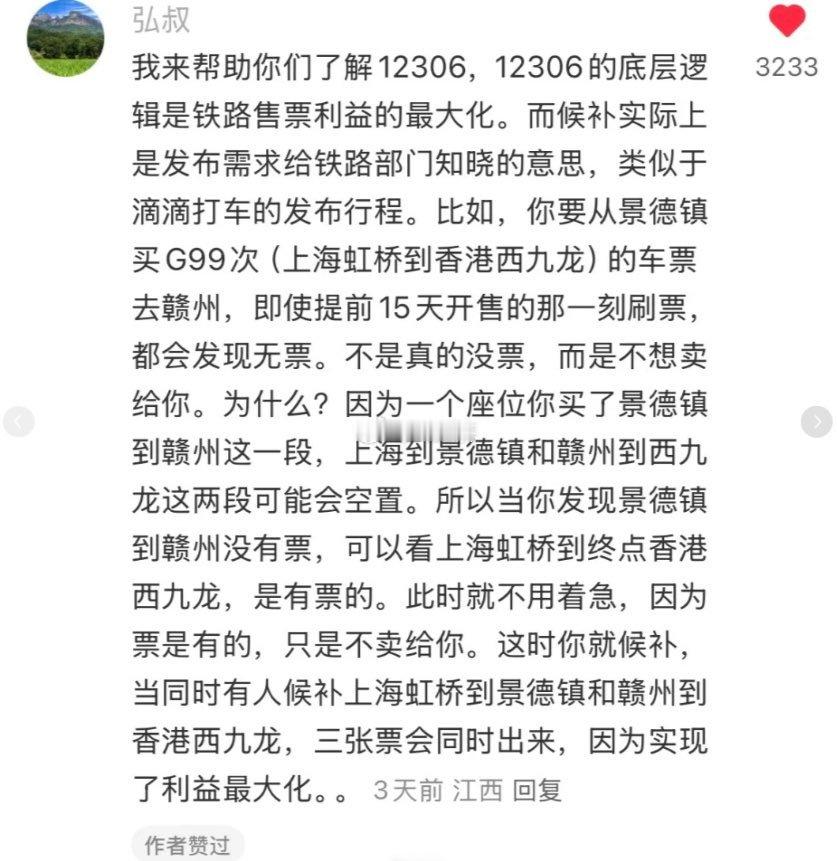

勇劫
写的跟自己被注射过,一样。有些人不能接收恩赐。偶尔出现故障也许就是故意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