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,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,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,连开5枪,枪枪命中,谁知,等敌人走后,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! 他先屏住呼吸,耳朵贴地,听远处还有没有皮鞋踩沙的“咯吱”声。除了雨点,就是潮水,像一口大锅在咕嘟咕嘟煮人。确认没人回头,他才敢大口喘气,血水顺着嘴角往下淌,一喘气就冒粉红泡沫,看着吓人。雨越下越大,浪头扑上来,差点把他卷走,他干脆顺势滚进被潮水冲出的沙沟,让海水托着身子,省点力气,也免得留下一路血印。 夜黑得像扣了盆,他睁眼闭眼一个样。疼得实在受不了,就默念交通站那几本密码,用指甲在沙上划,划着划着就清醒几分:得先找口水喝,再弄件干布裹伤,然后往江西路那边爬——那边有片渔村,村头第三间草屋,门口吊着破船舵,是组织留给他的“死信箱”。念头一多,身上就有劲,他扯下绑腿,把左臂缠成粽子,右手撑地,半爬半拱,像条被剥了皮的鱼,一点点往堤岸挪。 不知爬了多久,雨竟停了,东边泛起蟹壳青。他看见前面有堆黑影,是收渔网的小草棚,门半掩,里头没人。草棚里有火塘,还有一口破铁锅,锅底剩半锅昨夜渔民喝剩的番薯干粥。他顾不得馊味,趴锅边咕咚咕咚灌,温热的粥水下肚,血好像才重新流动。喝完,他把锅灰抠下来,按在伤口上,黑灰混血,黏成疙瘩,好歹不再冒血。火塘里还有火星,他掰根竹片点着,烤自己的衣角,布片一受热,血腥味“嗤啦”往上冲,呛得他直掉泪。眼泪混锅灰,脸上横一道竖一道,像唱戏的。 天刚亮透,村口传来狗叫,他赶紧掐灭火,爬出草棚,钻进芦苇荡。芦苇叶子带锯齿,抽在伤口上,跟鞭子似的,他却不敢停,因为远远看见几个穿胶皮雨衣的家伙,提着枪,沿沙滩一路搜过来——敌人果然回来补刀。他憋住气,把整个身子沉进泥水里,只露鼻孔,耳边嗡嗡,不知道是蚊子还是耳鸣。狗在苇荡边嗅来嗅去,忽然“嗷”一声,被芦苇根绊住脚,那几个人骂骂咧咧转头去别处。等脚步声远了,他才敢探头,吐出一口黑泥,胸口剧烈起伏,肋骨里的子弹像要跳出来。 歇了半刻,他继续往深处爬,找到一条潮汐冲出的沟汊,水咸得发涩,却能把血味冲淡。他折了根空心苇杆,当吸管,一边吸水一边往前挪。日头升高,沙滩烫脚,他身上的湿衣很快又被体温烘干,血痂“咔吧咔吧”裂口,一动就渗血。就这么爬爬停停,中午前,终于看见那条破船舵——草屋到了。 草屋里只一个瞎眼老太,耳朵却灵,听见动静,摸出把柴刀堵在门口。傅有智压低嗓子报暗号:“海蛎子熟了,要加姜吗?”老太手一抖,刀掉地上,反手把他拽进屋,关门上闩。原来这老太是交通员的姑妈,早接到“有同志出事”的风声。她摸黑烧水,拿鱼线蘸盐水,给他把肋旁两颗子弹生生抠出来。鱼线勒进肉里,他咬断一根木棍,愣是没哼一声。老太把子弹头收进布袋,说:“留给娃打耳坠。”又煮了盆海草膏药,呼啦啦糊满他半身,屋里顿时腥得象打翻了一百个螃蟹壳。 他在草屋地窖里窝了七天,白天听老太在地面补网,夜里就借月光写情报——把闽南游击队的布防、敌人新调的机枪连位置,全写进一张薄如蝉翼的竹纸。第七天夜里,老太的孙子划小舢板过来,把他转移到同安山里的炭窑。炭窑黑,只有炭火一点红,他躺在灰烬里,像条被烤熟的鱼,却觉得从未这么踏实。山风带着松脂味灌进来,他摸摸胸口,心跳还在,忍不住笑:阎王殿前走一遭,又被雨水踢回来了。 后来,傅有智一路化名“林大海”,当过盐贩子、船工、私塾先生,把闽南特委残存的联络点一个个重新接起来。有人问他:“老傅,你命咋这么硬?”他咧嘴,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:“子弹也怕穷人,它嫌我血里盐多,腥。”一句话,把人说笑,也把眼泪说掉。抗战胜利那年,他在厦门港看焰火,冲天火光映在脸上,他忽然想起那片海滩,想起自己爬过的湿沙,摸了摸左臂上的贯穿疤,轻声嘟囔:“兄弟,你们没看见,我替你们看见了。” 故事讲到这里,我总在想:今天下暴雨,我们第一反应是喊“收衣服”,而1930年的那场雨,却把一个本该写进烈士名册的人,硬生生从死神指缝里抠回来。历史不是剧本,没有“应该”或“不应该”,只有“居然”和“竟然”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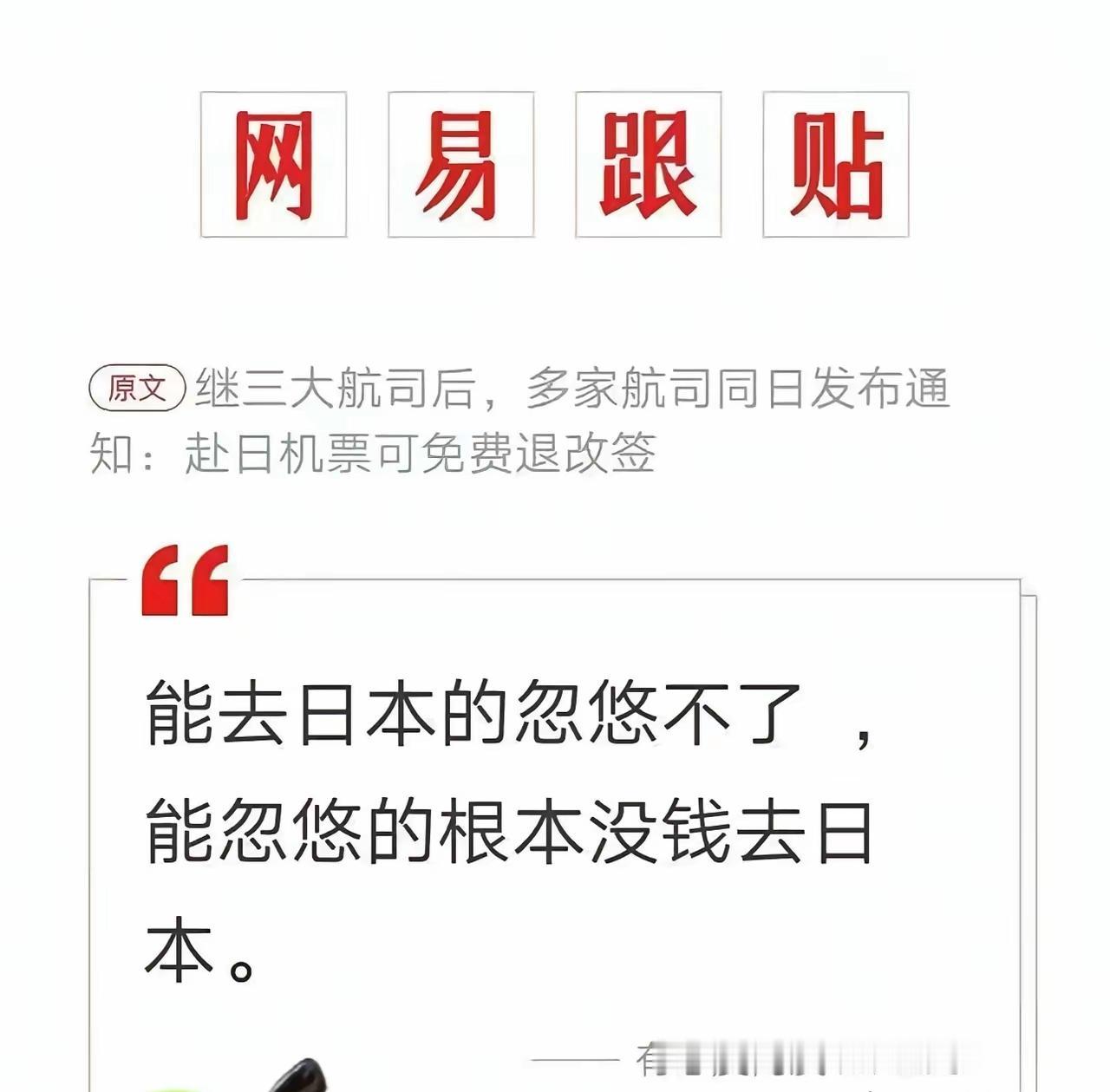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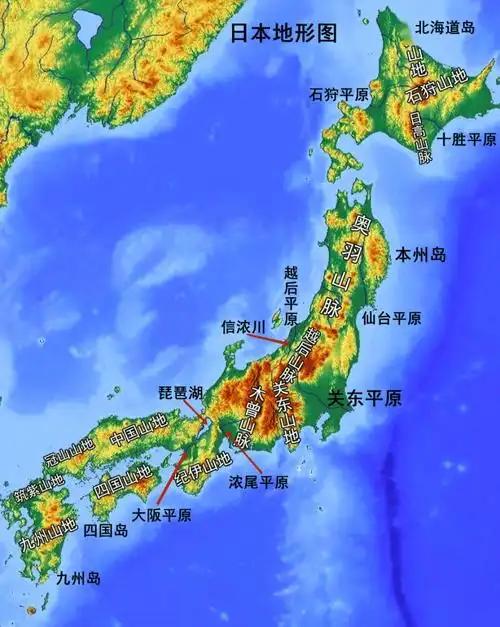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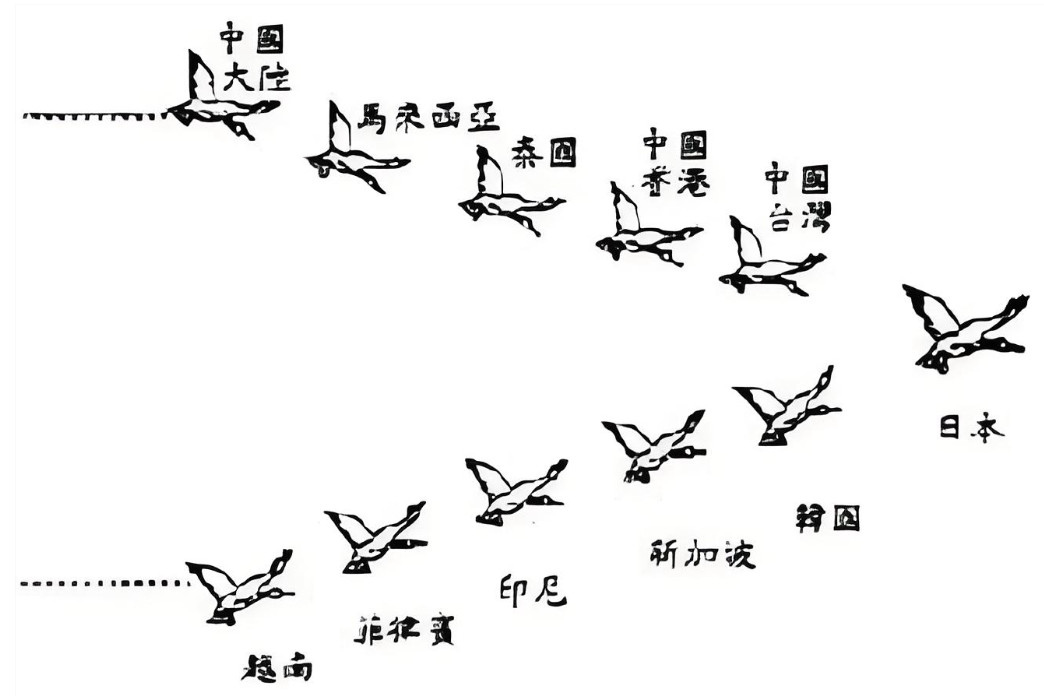


tb324830382
苍天有眼 福佑好人再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