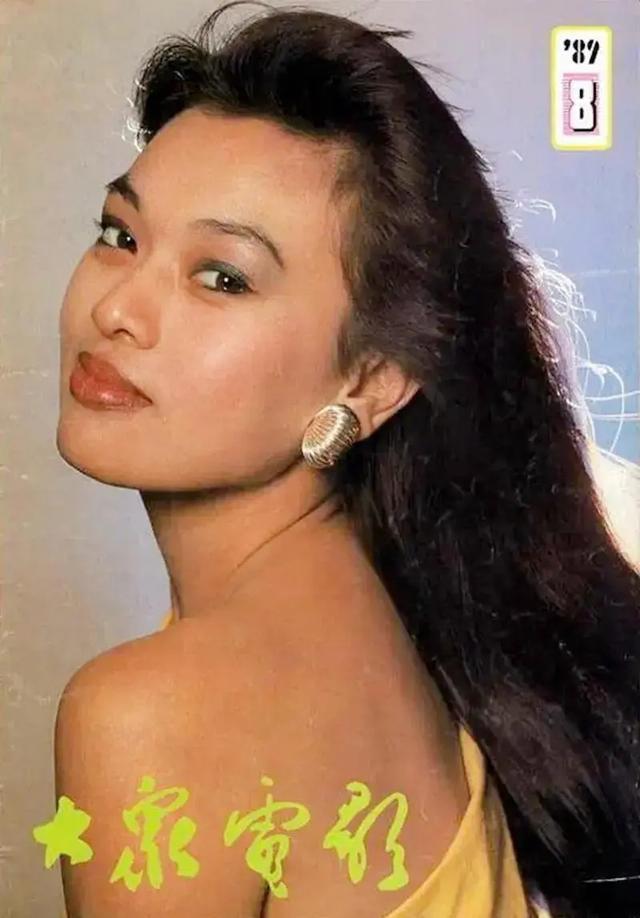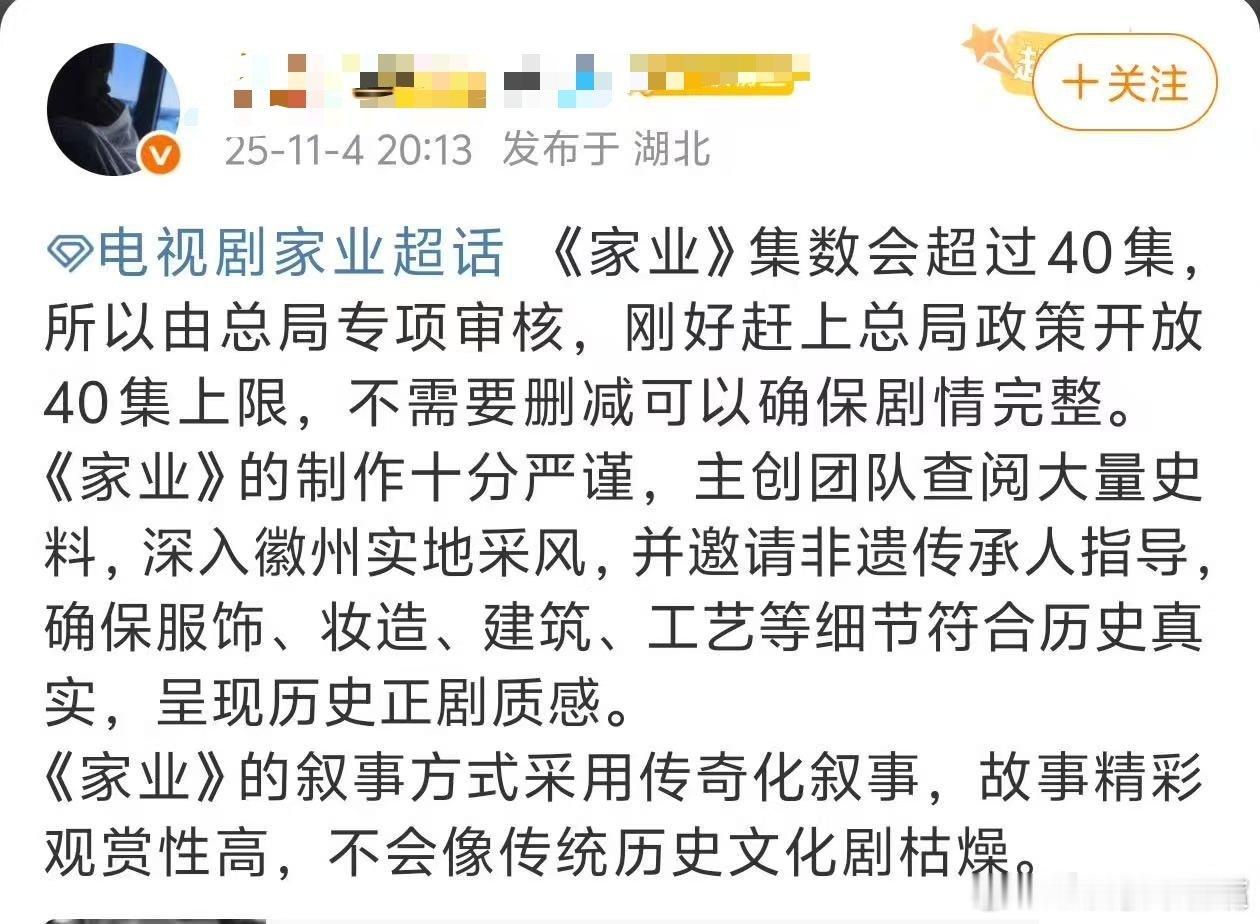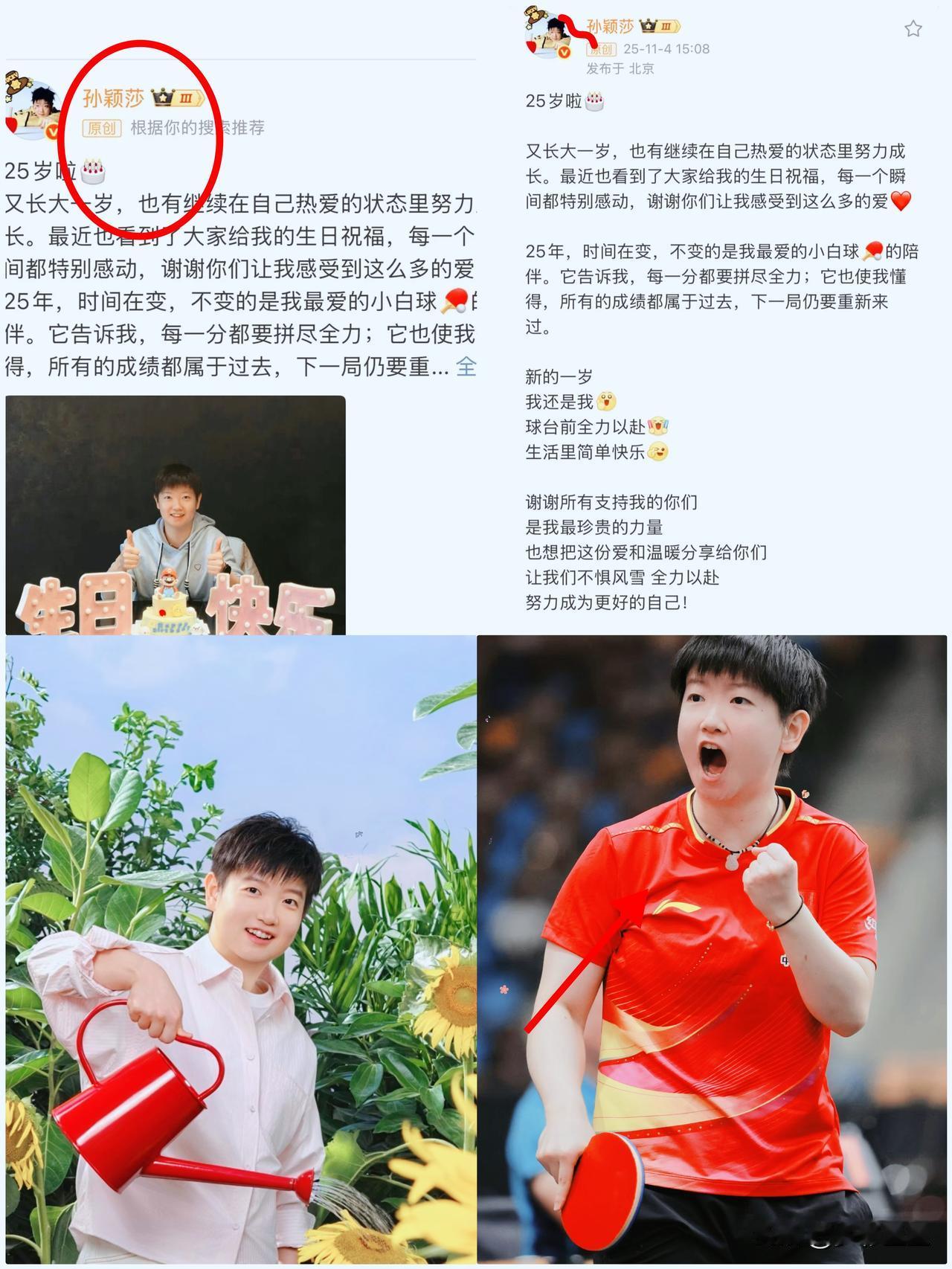演员史可说:“当年,我在瑞士生下大儿子,我的洋婆婆就只来看了我一次,还前呼后拥的牵着几条大狗,告诉我,我没义务帮我的孩子再带孩子,溜达了一圈,完了就走了。 当年,史可在瑞士生下大儿子,正是一个女人最需要帮手、最敏感脆弱的时候…… 医院的房间安静,窗外是阿尔卑斯山常见的晴朗天气,但史可的心里正经历着初为人母的忙乱与不安,就在这时,她的洋婆婆来了。 阵仗确实不一般,人还没到,先听到几条大狗兴奋的吠叫和杂沓的爪步声,婆婆不是独自一人,或许还约了一两位同样精神矍铄的老友,像是进行一项日常的户外活动顺路而来。 她推开病房门,带来一阵室外清冷的空气,笑容爽朗,但姿态是礼貌而保持距离的。 她没有像中国婆婆那样急切地奔向婴儿床,而是先给了史可一个短暂的、礼节性的拥抱,说道:“亲爱的,你看上去不错,孩子很健康,这太好了。” 寒暄过后,婆婆的目光或许在襁褓中的孙子身上停留了片刻,语气温和地称赞:“真是个漂亮的小家伙。” 但随即又用清晰而平静的语气对史可说:“亲爱的,我把我的儿子抚养长大,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。现在,这是你们的孩子,你们的生活。我没有义务,也不会代替你们来抚养他。” 这句话,不是商量,更像是一种温和的宣告。 史可当时听着这话,内心作何感想?有一瞬间的错愕,有种期待落空的冰凉。 在东方文化里,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“冷酷”,但在婆婆的逻辑里,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独立宣言,她完成了“探望”这个仪式,确认了母子平安,并明确划定了未来的界限。 婆婆看了看手表,笑着说:“好了,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休息了,狗儿们还需要足够的运动。” 说罢,便真的像完成了一次友好的社交访问,牵着她的狗,前呼后拥地离开了病房,来去如风,留下病床上的史可,独自消化这巨大的文化冲击。 史可是谁?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,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她可是中央戏剧学院“五朵金花”之一,和巩俐是同班同学,成名很早。 她性格里有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儿,事业上升期时,选择了嫁给一位瑞士籍的音乐家,远离熟悉的国内环境。 当她遇到这种“婆婆不伺候月子”的情况时,她内心的震荡和之后的调适过程,本身就很有故事性。 2000年初的瑞士,史可刚经历完分娩的疲惫与喜悦,身体还没恢复,正手忙脚乱地学着如何应对新生儿,她的丈夫可能请假在家,但毕竟初为人父,很多事情也摸不着头脑。 婆婆的这次来访,其出场方式就奠定了一种“距离感”和“独立性”——狗是她的日常伙伴,她的生活重心的一部分,她并没有因为孙子的降生,就立刻把自己的生活全部抛在脑后。 见面后,没有东方家庭里常见的嘘寒问暖、传授育儿经的环节,婆婆直接、清晰地传达了她的价值观。 这背后,是西方社会非常普遍的一种个体主义观念,强调代际之间的独立,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到其成年为止,之后大家是平等的成年人关系。 他们普遍认为,老年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,而不是再度陷入抚育孙辈的辛劳中,这种观念,和法律上的“没有抚养孙辈的义务”是相互印证的。 反观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,则是一种绵延的“责任伦理”,从“养儿防老”到“隔代亲”,代际之间是深度捆绑的。 婆婆帮忙带孙子,在很多家庭里被视为理所当然,甚至是婆婆体现自身价值、表达对子女关爱的重要方式,它背后是“家”的整体观念。 史可在访谈中也提到,一开始确实不适应,但慢慢也理解了婆婆的立场,并学会了在异国他乡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家庭。 这种独立,虽然初期辛苦,但也促使她和丈夫建立了更深厚的伴侣关系,共同承担育儿责任,而不是依赖上一代,这或许也是一种被迫的“收获”。 史可,她后来有了两个孩子,婚姻走过多年,外人无从知晓她与婆婆后续的具体相处细节,但从她能够平静地讲述这件事来看,她最终实现了某种和解与理解。 婆婆那次“溜达了一圈”的探望,看似不近人情,实则打开了一扇窗,让众人看到家庭关系的另一种可能:爱,不一定表现为无条件的付出和捆绑,也可以是有界限的尊重和鼓励独立。 在中国式大家庭的温情,与西方式个体独立的边界之间,本没有唯一的答案,重要的是,身处其中的每个人,是否找到了让彼此感到舒适和自由的平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