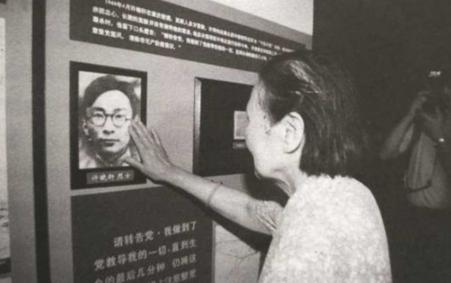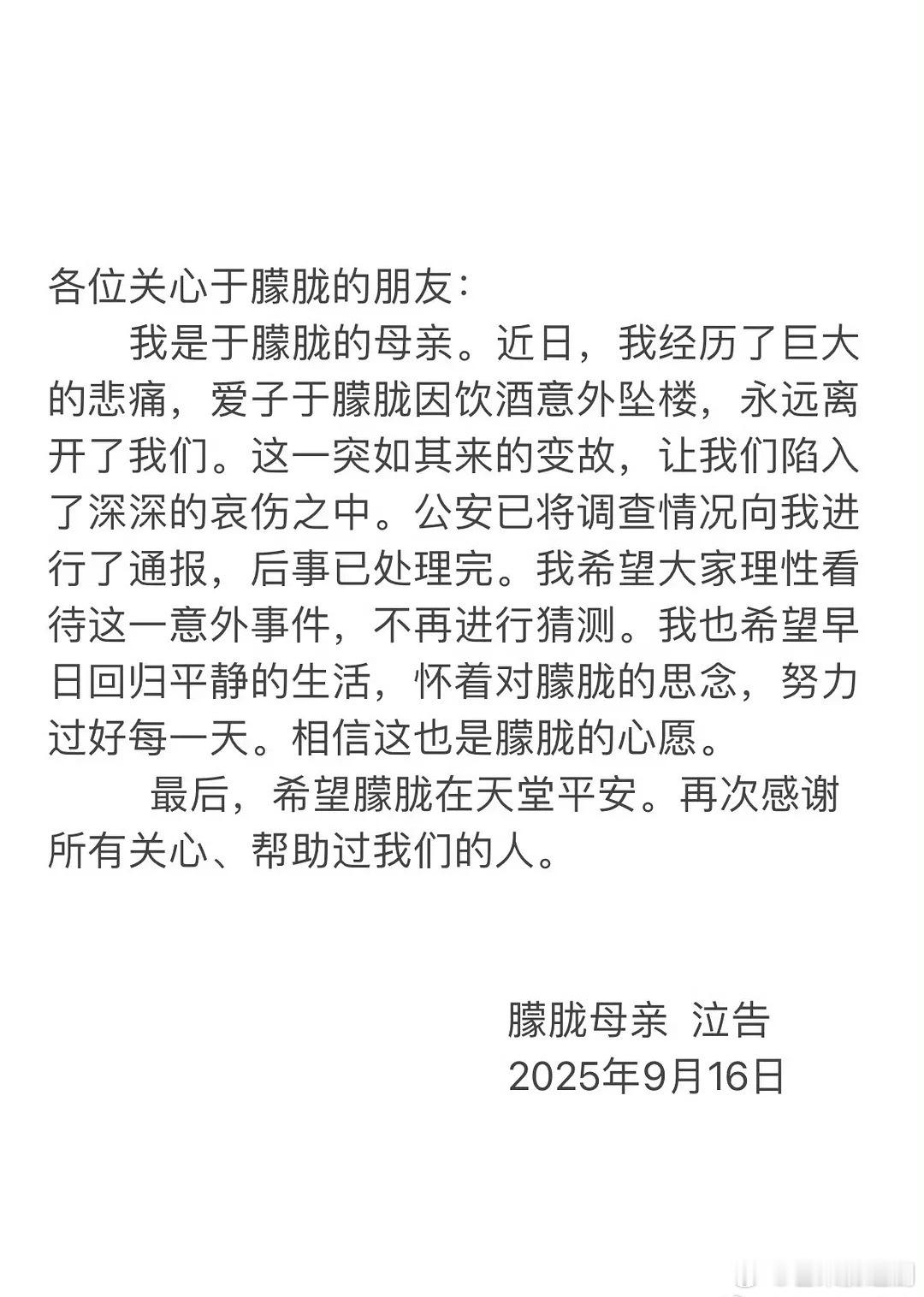1696年,噶尔丹兵败后,身边只剩三类人:一是女儿钟济海,二是两位军官,三是不足百人的卫队。他曾是坐拥十万大军的枭雄,一度不可一世。如今走投无路,最终在一年后,五脏俱焚而亡。 1697年春,噶尔丹裹着破旧皮袍蹲在河边。他手指冻得通红,仍在仔细拔野兔毛。 想当年,他是准噶尔汗王,统帅十万铁骑。如今身边连百人都凑不齐,只有女儿钟济海、老将丹济拉、阿拉布坦,以及七十多个面黄肌瘦的士兵。 十九岁的钟济海递来烤好的兔肉,说:“阿爸,吃些兔肉吧。” 她手上的冻疮很显眼。 钟济海没忘半年前的昭莫多之战。那一战打得惨烈,清军火炮轰鸣,母亲阿奴可敦率军冲锋时,被弹片击中,鲜血溅到她额间。 如今有人劝她逃亡,她不肯。她说:“母亲当年护我时,何曾想过退路?” 于是执意跟着父亲颠沛流离。 噶尔丹看着女儿,喉咙里泛起苦涩。他想起37年前的事。 那时,他还是西藏寺院里的少年活佛。达赖喇嘛赠他 “博硕克图汗” 称号,他根本没料到,自己会踏上这条满是血火的路。 后来他平定准噶尔内乱,率军横扫天山南北,攻占叶尔羌汗国,兵锋一直延伸到里海沿岸。 沙俄使者曾来找他,献上最新式火枪,还许诺支持他重建 “大蒙古帝国”。 与此同时,紫禁城里的康熙帝正注视着西北的烽火。他三度亲征的决心,早已像磐石般坚定。 “大汗,今日又走了三人。” 老将阿拉布坦轻声禀报。 噶尔丹没回头。他清楚,那些逃亡的士兵并非贪生怕死。 半年前在科布多,他亲眼看见部下因饥饿抢马肉吃,可最后一块干粮,还是塞进了他手里。 现在情况更糟,战马全被杀死,士兵们只能靠野兔、草根填肚子。 他还想起乌兰布通之战后,清军在漠北草原布下天罗地网搜捕他。更要命的是,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了伊犁老巢,把他所有退路都断了。 夜幕降临时,丹济拉和阿拉布坦跪在帐篷外。 噶尔丹看着两人斑白的鬓角,想起二十二年前初见的情景。那时,丹济拉是血气方刚的骑兵统领,阿拉布坦是能文能武的谋士。 可如今,他们眼里没了昔日的锋芒,只剩对生存的渴望。 噶尔丹忽然开口:“你们带钟济海走吧,往西去,或许还能找到活路。” “大汗!” 两人叩首,眼泪直流。 噶尔丹拔出佩刀架在颈间,说:“若不走,我现在就死!” 月色下,钟济海冲进来抱住他的手臂,泪珠滴在刀刃上:“阿爸,当年你教我骑马时说过,准噶尔人的刀刃不向自己人!” 噶尔丹看着女儿的眼睛,那双眼酷似亡妻。他终于垂下刀锋。 第二天清晨,噶尔丹召集残部。他指着远处的雪山说:“当年我率军翻越天山时,曾见雪莲在峭壁上绽放。如今虽败,但准噶尔人的血脉不能断。” 士兵们举起残旗,喊着 “博硕克图汗”。可这呼声没了往日的威势 —— 他们的战马瘦骨嶙峋,铠甲破碎,连弓箭都因潮湿无法张满。 四月初三,噶尔丹病得更重了。他不肯进食,只喝雪水。 丹济拉守在帐外,听见帐里传来诵经声。那是噶尔丹在默念《甘珠尔》经文。 据《清实录》记载,噶尔丹曾受戒于达赖喇嘛,此刻正以绝食践行 “入灭尽定” 的密宗修行。 他头痛得像万针穿脑,却始终不说话。只有昏迷时,会反复念叨:“阿奴…… 我来了……” 四月初七,清军骑兵出现在二十里外。 钟济海执刀站在帐前,说:“我父已死,要杀就杀我一人!” 可领兵的费扬古将军下了马,向她行礼:“皇上早有旨意,归顺者从宽处置。” 费扬古让人展开圣旨,上面写着:“准噶尔部众若降,赐地安居,不究前罪。” 第二天,噶尔丹的遗体被火化。骨灰由丹济拉护送到清营。 康熙帝听说后,沉吟许久,下令将骨灰悬在京师城门示众三个月,用以警示天下。 但见到钟济海后,康熙帝改了主意。这个少女在殿前站得笔直,说话间有几分噶尔丹的刚烈。 于是康熙封丹济拉为郡王,阿拉布坦为贝子,还将钟济海许配给蒙古贵族。这样做,是为了恩威并施。 可历史的暗流从未停歇。 据《清内阁蒙古堂档》记载,噶尔丹的骨灰示众后,被策妄阿拉布坦截走。直到康熙四十年,清廷才将骨灰索回。 钟济海嫁入蒙古贵族后,始终保持着准噶尔人的尊严。她的后代中,有人参与了平定噶尔丹同族叛乱的战役,成为清廷 “以准制准” 策略的关键棋子。 噶尔丹的死因,至今仍是史家笔下的谜团。 有人说他 “服毒自尽”,有人称 “绝食而亡”,还有密宗学者考证,他是以 “甘露法药” 完成修行。 但不管真相如何,这个枭雄的结局,印证了一个真理:在历史洪流中,个人野心与时代潮流碰撞时,往往以悲剧收场。 就像康熙帝在昭莫多之战后所说:“非朕好战,实乃天厌其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