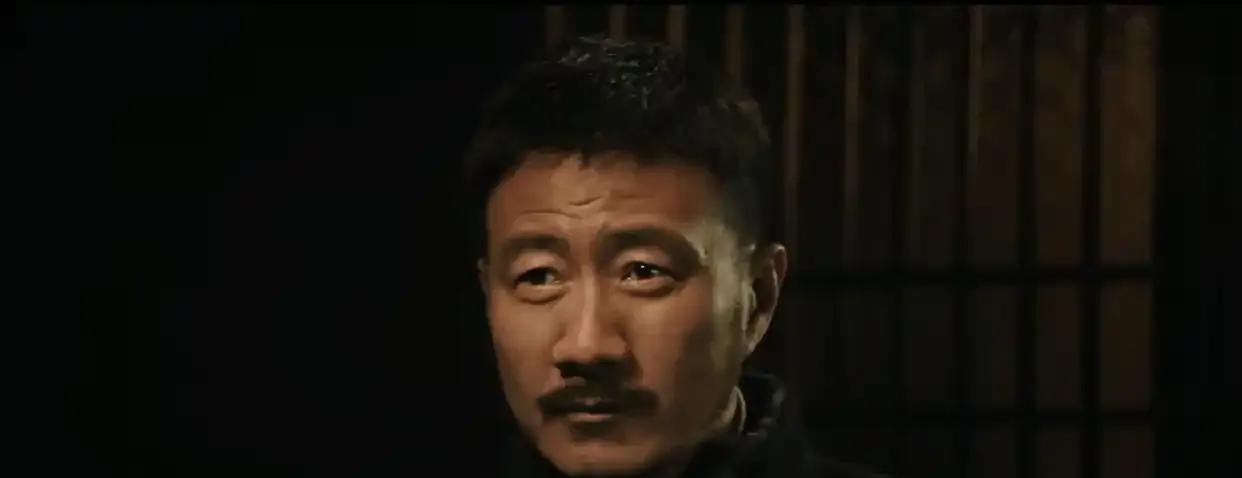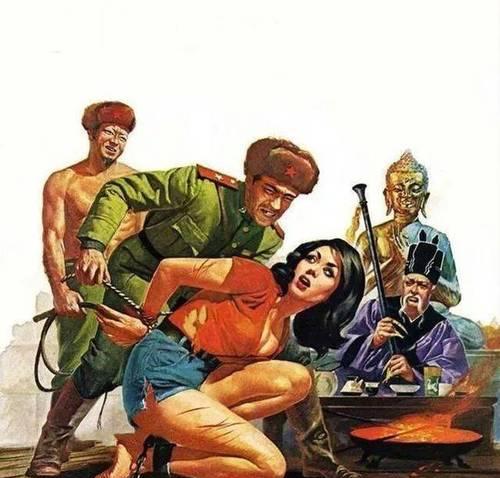问题来了,是什么把情报员硬生生推成了“用骨头换吗啡”的人,向前翻,战争史上不缺类似剧本,一战时德军给前线士兵每月发七克止痛粉,二战英美部队流行安非他命,今天乌克兰前线也能搜到成箱曲马多,疼痛和恐惧一起摆烂,最便宜的解法永远是药物。 再看小贵卖情报的那瞬间,舆论往往先抬出“大义”尺子,但数据告诉我们,痛感在持续十分钟后就足以扭曲决策,大脑前额叶直接掉线,医学杂志《The Lancet》把这种状态称为“理性短路”,当生理极限逼近,任何口号都比不过一针镇痛剂的即时生存价值。 有人说这是背叛,可咱们日常生活也在上演小规模版本,美国去年阿片类药物致死近八万人,比枪械伤亡还高,这是没有炮火的战场,药也是炮弹,持枪抢药房的新闻被推特用户点赞回怼无数,底层逻辑完全一致,疼痛吞噬前一切身份。 此情此景,最值得警醒的也许不是“他竟然卖情报”,而是我们在各种体系里给出多少替代方案,当疼痛管理被军事或资本垄断,所谓忠诚和道德注定先被拔牙似的拔掉根基。 写到这儿我抬头看时间,战争或瘾痛都不会因为手机锁屏就暂停,接下来怎么走,得看是谁掌握止痛药的配方,又有谁能在枪口与疼痛之间硬撑出第二条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