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明末,谁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了? 万历四十七年,萨尔浒之战刚结束,熊廷弼捧
零零说史
2025-09-01 19:03:51
在明末,谁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了?
万历四十七年,萨尔浒之战刚结束,熊廷弼捧着败报走进文华殿时,腿肚子都在转。那会儿万历皇帝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,大臣们还在为“立太子”吵得不可开交。熊廷弼在奏折里写“辽东已无兵可用,奴酋(指努尔哈赤)如狼似虎,不出十年必入关”,满朝文武却觉得他在危言耸听。有个御史甚至弹劾他“夸大其词,邀功请赏”,气得熊廷弼把官帽摔在地上:“你们等着看!”
这人是真急了。他在辽东待过五年,亲眼见过明军的糜烂——士兵们穿着破烂的盔甲,手里的刀锈得拔不出鞘,军官们却忙着把军粮换成银子。有次他去查营,发现一个营的士兵只剩一半,剩下的不是逃跑就是饿死了,营官还在账上虚报人数领饷。他想整顿,却被地方官联手排挤,说他“扰民”。离开辽东那天,他看着山海关的城楼,说了句“这关怕是守不住了”,当时身边的小吏只当他是气话。
比熊廷弼更早察觉的,是个叫吕坤的户部侍郎。万历二十五年,他奉命去河南赈灾,看到的景象让他半夜睡不着。路边的树皮被剥光,灾民们互相换孩子吃,而当地的藩王却在府里修戏台。他回京后写了本《忧危疏》,说“百姓活不下去,国家就站不住”,建议皇帝削减藩王俸禄,拿出内库银子赈灾。结果奏折被万历压在箱底,还被指责“离间君臣”。吕坤心灰意冷,没多久就辞官了,临走前对门生说:“我能做的都做了,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。”
崇祯初年,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望着后金的营帐,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他刚杀了毛文龙,朝堂上骂声一片,皇太极又趁机绕过山海关,直逼北京。他带着关宁铁骑星夜驰援,在北京城下打退了后金,却被崇祯下狱。临刑前,他对狱卒说:“我死不足惜,只是这大明,怕是真的要完了。”他看得明白,皇帝多疑,大臣内斗,边关将领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,没人敢放手做事。
其实民间早有预兆。李自成起义前,陕西一带就流传着“开了城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的歌谣。百姓们不是天生就想反,是苛捐杂税逼得他们活不下去。有个叫顾炎武的读书人,在昆山老家亲眼看到官府为了收税,把不交钱的百姓吊在树上打,他在《日知录》里写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可那会儿他还觉得只要改革就能挽救。直到清军攻破昆山,他的母亲绝食而死,他才明白,有些溃烂已经到了骨头里。
最让人唏嘘的是徐光启。这位明末少有的科学家,早就看出明朝的问题不在外患,而在自身。他引进西洋火器,编练新军,甚至想推广高产作物解决粮食问题。可每次上奏,都被保守派骂“崇洋媚外”。他晚年主持修订历法,看着新铸的天文仪器,对学生说:“这些东西再好,没人用也是白搭。”他去世前一年,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,明军在松锦大战中全军覆没,他躺在病床上,反复念叨“来不及了,来不及了”。
这些人里,熊廷弼的呐喊最刺耳,吕坤的担忧最沉重,袁崇焕的绝望最无奈。他们身份不同,却都在不同时间看到了同一个真相:明朝的病,不是换个皇帝、杀个奸臣就能治好的。从万历年间的民不聊生,到崇祯年间的众叛亲离,就像一栋被虫蛀空的房子,看起来还立着,一阵风就能吹垮。
最早意识到明朝要亡的,或许不是某个具体的人,而是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百姓。当他们连最后一粒米都被搜刮走,当他们看着亲人饿死却求助无门,心里就已经明白,这个朝廷不值得留恋了。熊廷弼、吕坤们的清醒,不过是提前说出了百姓们早已在心里认定的事实。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,明明有那么多人看出了问题,却没人能拉回这架失控的马车。不是他们不够聪明,也不是不够努力,是那个积重难返的制度,容不下任何真正的改革。当一个王朝失去了民心,失去了纠错的能力,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。
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0
阅读:26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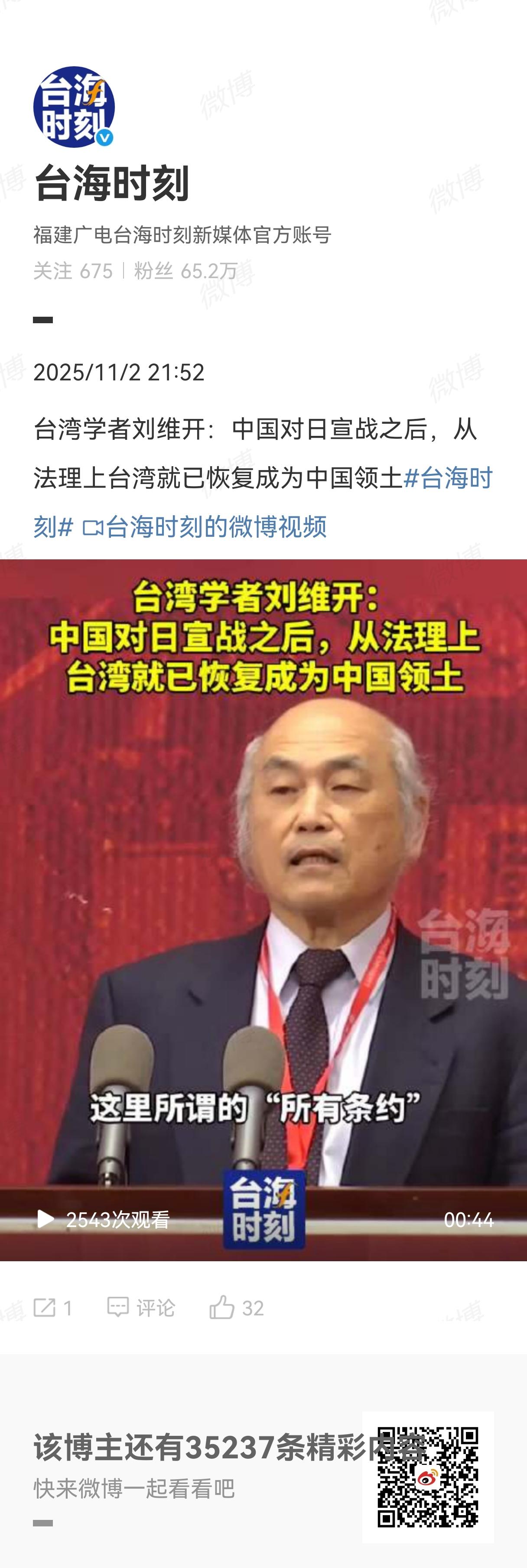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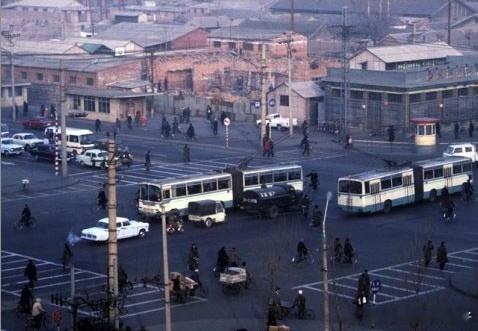



用户10xxx35
半生学习朱由榔,从来不疯也不狂; 白马笑我与霞客,生死都从李晋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