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41年,二十岁的王安石科举考试中排名第一,宋仁宗边看他的文章边点头,突然勃然大怒:“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状元?” 集英殿里,针落可闻。 香炉里的瑞脑香烧得正旺,一丝丝烟气笔直向上,好像被殿内的气氛冻住了。 宋仁宗赵祯坐在御座上,脸色铁青,手里攥着一份考卷。 案前站着几位老臣,为首的是晏殊和欧阳修。他俩是这次的主考官,刚刚还一致认定,这份卷子当为本届第一。 现在,他俩低着头,大气不敢出。 仁宗的手指,死死按在卷子末尾的四个字上。 那四个字是:“孺子其朋。” “朋?”仁宗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,声音不大,却让殿内所有人心头一颤,“他把自己当什么?周公吗?” 没人敢接话。这四个字的分量,在场的人都懂。这是周公教训年幼的周成王时说的话,意思是:你这小子,该把贤臣当朋友老师。 话没错,但分谁说,对谁说。 一个二十岁的白衣考生,对一个在位二十年的皇帝这么说,就是另一番味道了。 宰相吕夷简上前一步,躬着身子:“陛下,此子年轻,引经据典,或是一时孟浪,并非……” “孟浪?”仁宗打断他,将卷子甩在龙案上,发出“啪”的一声闷响,“朕看是狂悖!文章写得是不错,针砭时弊,句句见血。可通篇的口气,就不像个臣子!倒像个先生在教训学生。今天他敢教训朕,明天他得了状元,是不是就要搬张椅子,坐到朕旁边来?” 这话一出,就定了性。 晏殊心里咯噔一下。他知道,卷主那个叫王安石的年轻人,状元是彻底没戏了。 他甚至有些后悔,早知如此,就该把这篇文章压一压,不呈到御前。 可这文章的才气,又实在让他压不下手。 殿外,数百名新科进士正伸长了脖子,等着唱名。 人群中的王安石,神情淡然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布直裰,背挺得笔直。 从江西临川到京城,他走了快一个月,脚上的鞋磨破了边。 他不在乎,他只在乎卷子里写的那些话,皇帝能不能看懂。 他觉得,皇帝一定能看懂。 殿内,仁宗的火气还没消。“把第二份卷子拿来。”他命令道。 内侍赶紧呈上。仁宗只看了一眼卷首的名字——王珪,眉头就皱了起来:“又是‘任子’,拿走。” 按大宋规矩,靠祖上功劳入仕的在职官员,不能点为状元。 内侍又递上第三份,是韩绛的。仁宗扫了一眼:“还是‘任子’!这届考生是怎么回事?”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 欧阳修捧着第四份卷子,硬着头皮上前:“陛下,这份卷子的主人杨寘,身家清白。且乡试、会试,皆为头名。” “哦?”仁宗来了兴趣,接过卷子。文章写得中规中矩,没什么锐气,但也没什么错处。他现在不想看什么锐气了。 “连中三元,好兆头。”仁宗疲惫地挥了挥手,“就他了。传旨,今科状元,杨寘。” 他想起那份让他动怒的卷子,补了一句:“那个王安石,降为第四甲。” 旨意传出,殿外人群一阵骚动。 有人欢喜,有人叹息。王安石听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,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默默地向着皇宫的方向,行了个礼。 有同乡替他抱不平,凑过来低声说:“介甫兄,以你的才学,状元本是探囊取物,怎会……” 王安石摇摇头,只说了四个字:“朝廷自有法度。” 说完,他转身挤出人群,没去参加庆祝的琼林宴,也没去拜见恩师,一个人走回了广济桥南那家烟熏火燎的“云集馆”。 他住的是下铺,与人合榻。 他从随身的竹箱里,拿出一本破旧的《周礼》残卷,就着昏暗的油灯,又读了起来。墙壁上,画满了圈圈点点的图,不知是何用意。 馆主端来一碗热水道:“王官人,中了进士,怎还这般用功?” 王安石头也不抬:“没读懂的地方,还有很多。” 几天后,授官的文书下来了。他被派往扬州,任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,一个从八品的小官。 离京那天,没人来送。他依旧背着那个竹箱,穿着那身旧青布直裰,走出了汴京城门。 走出城门时,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大的城楼。 他想起殿试那天,在文章末尾写下“孺子其朋”四个字时,自己手腕没抖,心跳没快。他只是觉得,这句话,该写。 他后来在扬州首创“贷谷于民”的法子,成了日后“青苗法”的影子。他在地方一待就是十年,从扬州到鄞县,再到常州。 十年后,他再回汴京,已是两鬓微霜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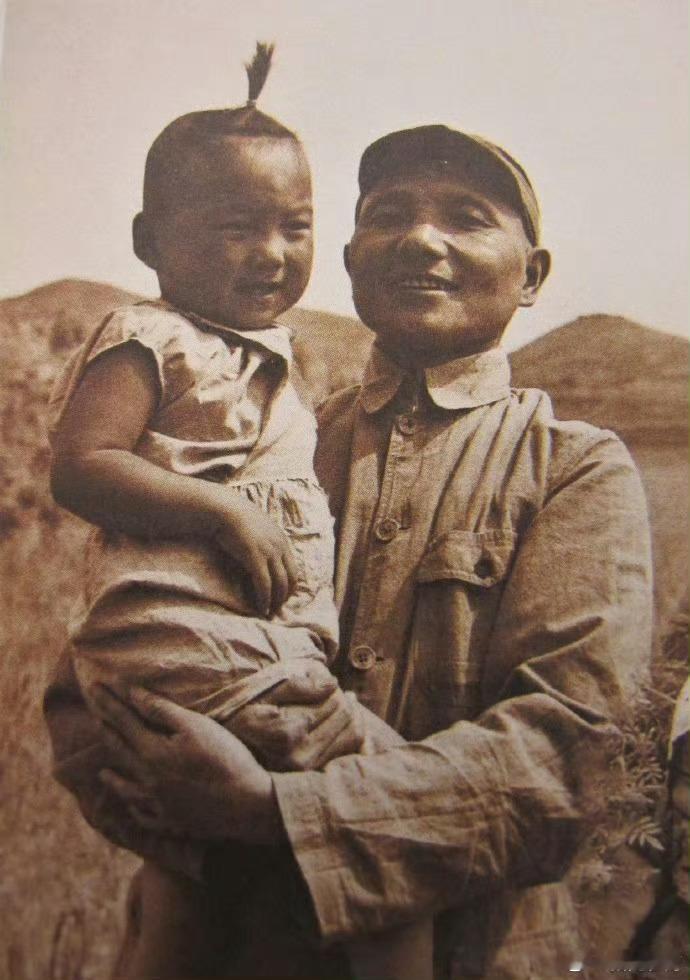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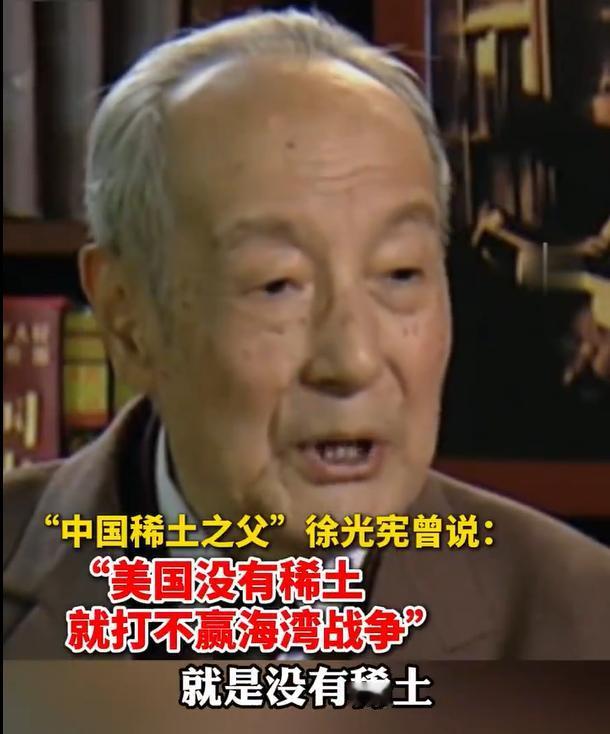
![于正要演将军了[笑着哭]](http://image.uczzd.cn/10775405504116759187.jpg?id=0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