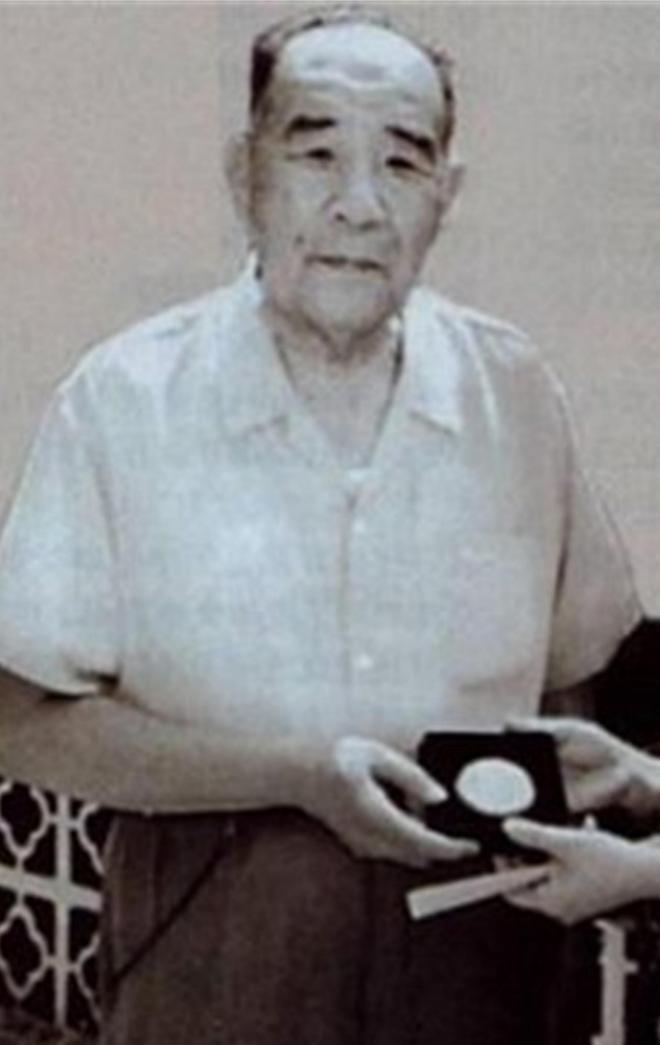“如果预测不准,我承担一切后果,宁愿丢掉我的乌纱帽,这47万人我也一定要保下。”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,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河北省青龙县时,用“奇迹”一词形容这里的情况。 距离震中仅115公里的县城,在7.8级强震中竟只有一人因心脏病发作离世,而同期唐山却有24万同胞永远闭上了眼睛。 创造这个奇迹的,正是当时的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,一个在没有红头文件、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,仅凭一则地震预测就敢力排众议的基层干部。 故事要从1974年说起,当时国务院下发文件指出华北地区地震形势紧张,青龙县所在的冀东一带被列为重点关注区域。 冉广岐上任后没把这当口号喊,而是实实在在地搞起了准备工作。他在全县16个公社都建了地震观测站,连村里都设了观测点,发动群众盯着井水变化、动物异常这些“土办法”。 县里的干部们白天抓生产,晚上就抱着地震知识手册啃,连冉广岐自己都成了半个“土专家”,遇上天气异常总会跑到观测点问东问西。 这种看似“小题大做”的铺垫,在两年后成了救命的关键。 1976年7月中旬,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开了个群测群防交流会,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带着任务去了。 会议期间的两个晚上,专家悄悄通报了一个紧急情况:7月下旬到8月初,唐山、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。 这个消息像块石头压得王春青睡不着觉,散会后他马不停蹄往回赶,7月21日一到县里就直奔县委办公室。 冉广岐听完汇报,手指在地图上敲了半天,青龙到唐山就一百多公里,真要是大地震,县城里这些土坯房根本扛不住。 可拍板防震不是拍脑袋那么简单。当时的规定是县级无权发布临震预报,必须等上级批复。 冉广岐召集县委班子开会时,有人提出“等等再说”,怕万一弄错了担责任,还有人担心动员群众会影响农业学大寨的进度。 冉广岐猛吸了口烟:“上级批文没来,可地震不等人!真出了事,咱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。” 他当场拍板成立防震指挥部,自己当主任,要求三天内必须让全县百姓都知道危险,还要搭好能住人的防震棚。 接下来的几天,青龙县像上了发条。公社干部骑着自行车跑村串户,大喇叭里反复播着防震知识;学校把课桌搬到操场,工厂在空地上搭起棚子;连供销社都改了规矩,把油盐酱醋搬到路边摆摊,方便群众买东西。 冉广岐每天带着人四处检查,看到谁家还住危房就直接上门劝说,遇到搭棚子缺材料的,就让公社统一调配。 有村干部嘀咕“会不会是狼来了”,冉广岐撂下话: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,真要是没事,我去给大家赔罪。” 7月28日凌晨,大地突然剧烈摇晃,睡在防震棚里的人们被惊醒时,只见远处的房屋像积木一样倒塌。 震后清点情况,青龙县1.8万间房屋损坏,7300多间塌了顶,但全县47万人里,只有一位老太太因为看到房子塌了受惊吓引发心脏病去世。 当时的场景让亲历者至今难忘:别的地方一片哭喊,青龙县的干部群众却在指挥部统一调度下,有条不紊地救治伤员、分发物资,连解放军进村时都惊讶于这里的秩序。 后来人们才知道,当时全国不少地方都收到了类似的预警。就像江苏江都县,根据地震预测搭了27万间防震棚,组织90多万人撤离。 但为什么只有青龙的故事被反复提起?关键就在于冉广岐把“可能发生地震”这个模糊信息,变成了“必须撤离”的具体行动。 他没等上级文件,而是用“日不闭户,夜不内宿”这种接地气的说法让群众明白危险;他没搞一刀切,而是让每个村根据实际情况搭棚子、备干粮。 这种把政策原则转化为民生实践的能力,在今天看来依然难得。 震后的青龙县很快恢复了生产,冉广岐却没把这事挂在嘴边,继续埋头搞建设。 直到多年后,联合国专家来考察,这个藏在燕山深处的县城才被世界知道。 有人问冉广岐当时怕不怕丢官,他只是笑笑:“官帽子再大,也大不过老百姓的命。” 这句话里藏着的,正是基层干部最珍贵的担当,在风险面前不推责,在考验面前敢决断,把纸上的政策真正变成护佑百姓的屏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