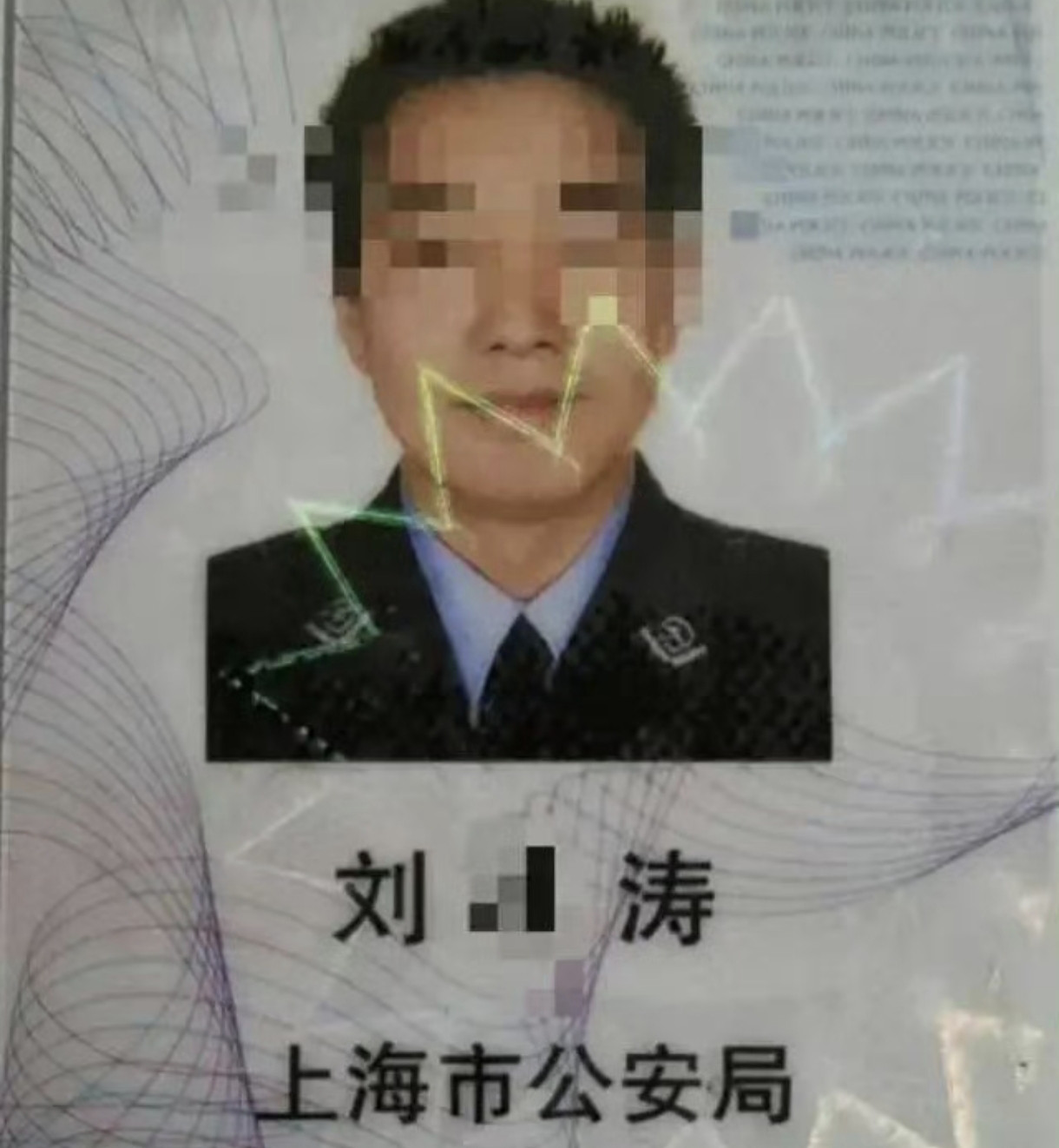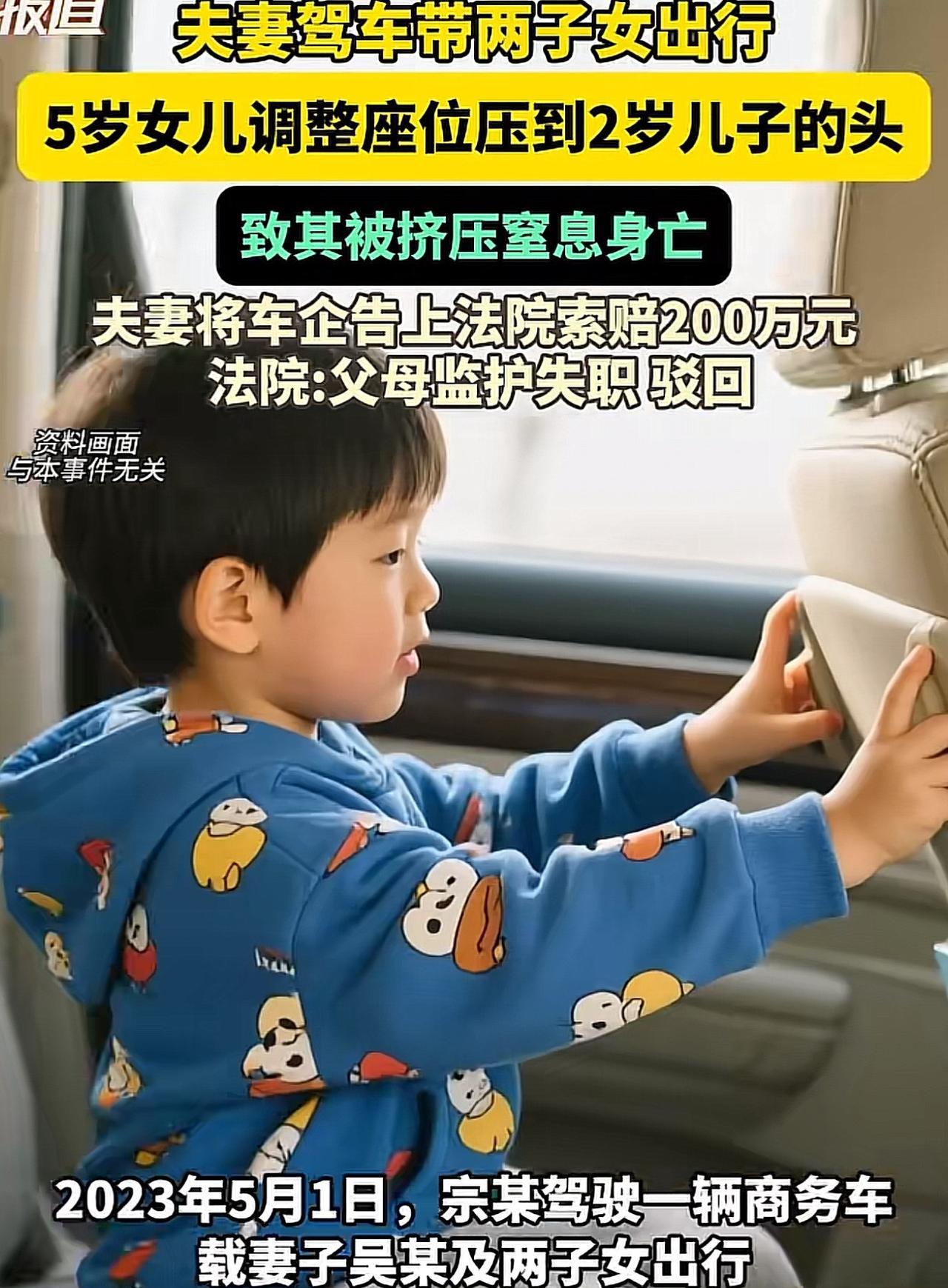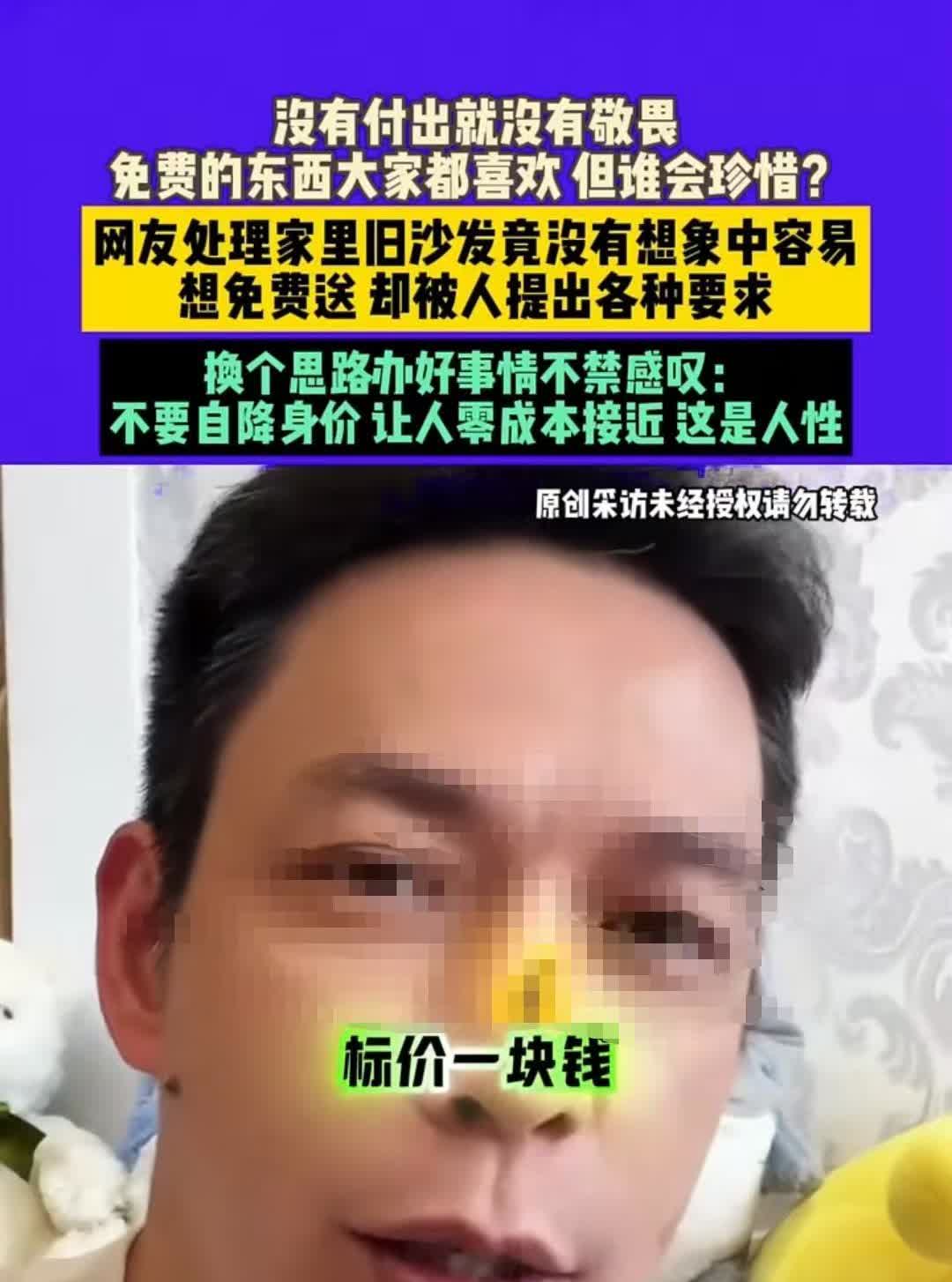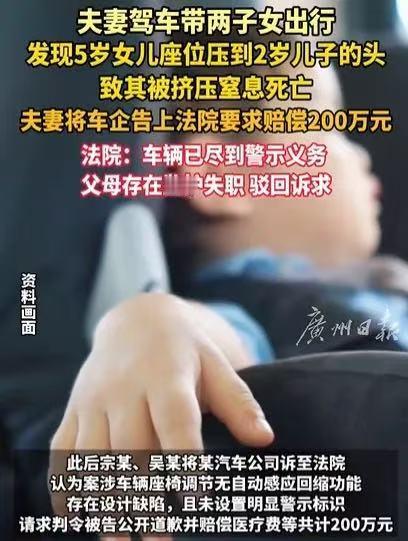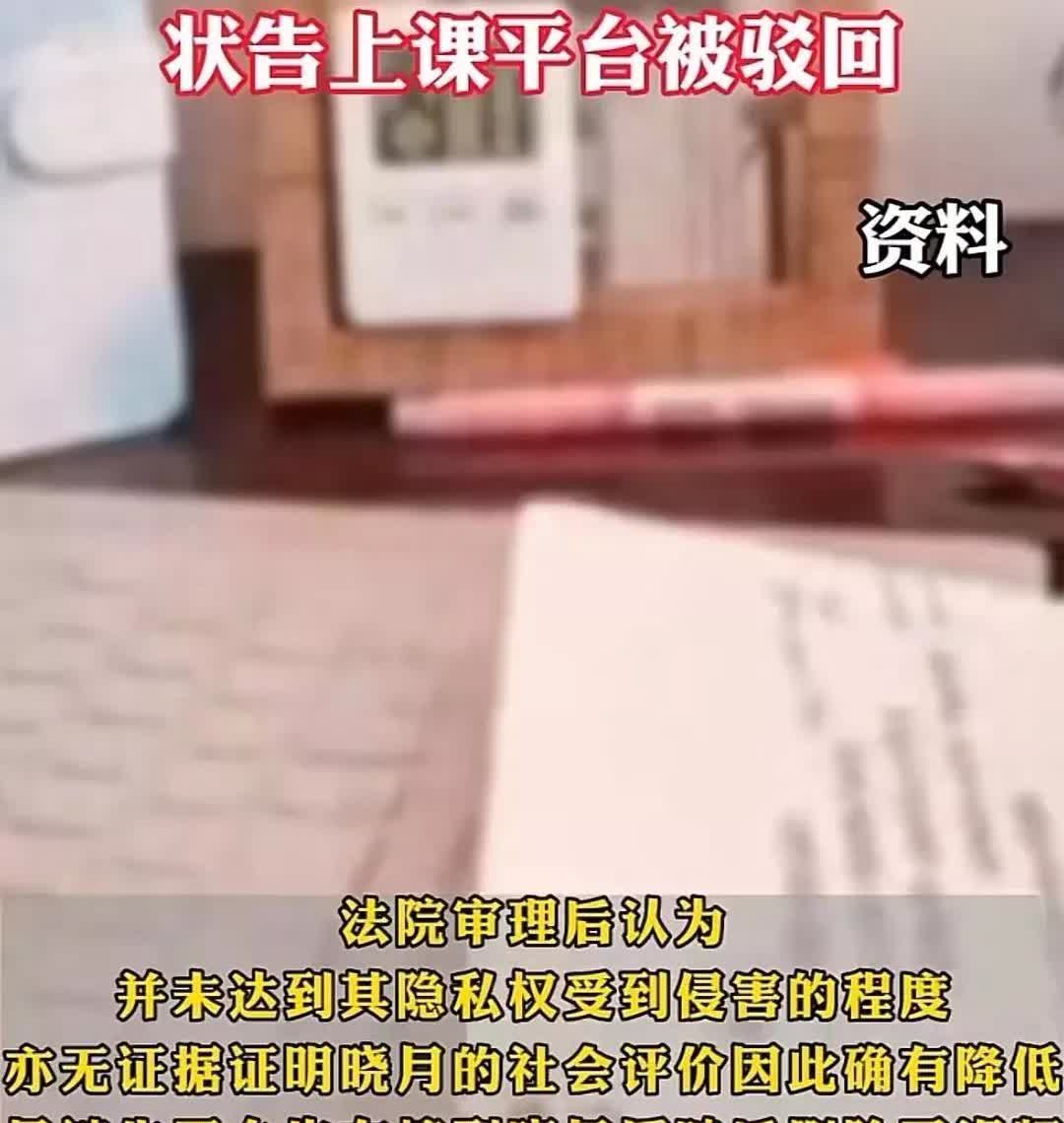1958年的冬天,上海长宁区一栋老式红砖楼里,年轻的李爱珍裹着厚棉袄,哈着白气,蹲在实验室里调试一台老旧的真空镀膜机。 窗外广播正高喊着“大跃进”的口号,室内却冷得手指都快冻僵。实验室没有供暖,水泥实验台上摆着几台破旧仪器,连液氮冷却装置都是她和同事用废铁皮自制的。 她咬着牙,一次次调整参数,手指被冻得通红,却不敢停下——因为她知道,这台机器里正在孕育中国第一个砷化镓样品。 那天深夜,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,她终于看到仪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——成功了!那一刻,她激动得几乎落泪。 这块小小的半导体材料,像一束光,照亮了中国科技自力更生的希望。然而,谁也没想到,这只是她漫长征途的起点。那时的她,怎会料到,未来她会面对更大的困境,甚至连“忠诚”都被质疑? 1980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,李爱珍站在匹兹堡机场,紧握着一张单程机票和一箱珍贵的技术资料。 送行的同事泪眼婆娑,挥手告别。她心里五味杂陈——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,她将前往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,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分子束外延(MBE)技术。 但临行前,政审会上刺耳的声音却像刀子一样扎心:“她有华侨背景,去了美国还能回来吗?会不会叛逃?” 面对质疑,她的导师王守武拍案而起:“科学无国界,但科学家有祖国!如果李爱珍不回来,我辞去所长职务!”这句话,给了她莫大的勇气。她暗下决心:学成之后,一定要回来,把技术带回祖国。 在美国,她每天工作16小时,实验室成了她的家。导师杜威恩·霍夫曼曾回忆:“她总是带着中国茶叶和大家分享,但从不提自己的辛苦。” 两年后,她带着满满的技术笔记和一颗滚烫的赤子心,毅然回国。然而,迎接她的,不是鲜花和掌声,而是更大的挑战。 1982年,李爱珍回到上海微系统研究所,迎接她的是一间破旧的实验室——没有先进设备,没有充足经费,连一台像样的分析仪都要通过香港转运,才能绕过技术封锁。她没有抱怨,卷起袖子就干。 她带着团队,用最原始的工具,自制液氮罐,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。墙上挂着“自力更生”的标语,成了他们唯一的信念。 1983年,中国首个分子束外延(MBE)实验室终于建成。那天,她俯身调试显微镜,齐耳短发下是一双专注的眼睛。 学生们回忆,李爱珍常说:“院士只是名片,实验数据不会骗人。”她用21项专利,打破了美日对半导体技术的垄断,让中国中红外激光器的精度提升到纳米级,甚至应用到北斗导航卫星的热控系统。 然而,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1999年、2001年、2003年,她三次申请中科院院士,却一次次落选。 2003年第四次落选时,同期某白酒品牌首席科学家却当选院士,学界一片哗然。面对质疑和不解,她只淡淡一笑:“评不上说明我水平不够,我只管继续做事。”但谁能懂,她内心的失落和坚持? 2007年,美国国家工程院的当选通知传来,李爱珍的名字响彻国际。她被誉为“推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在光电子领域应用的先驱”。面对采访,她却说:“我在美国有房有车,但我的实验室在中国。这里的学生需要我,中国半导体需要人铺路。” 晚年的她,依旧住在上海一间简陋的寓所里。书桌上堆满学生论文,她常通宵达旦为学生修改,甚至自掏腰包为贫困学生订牛奶。学生们尊称她“李先生”,不仅因为她的学术成就,更因为她的无私与坚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