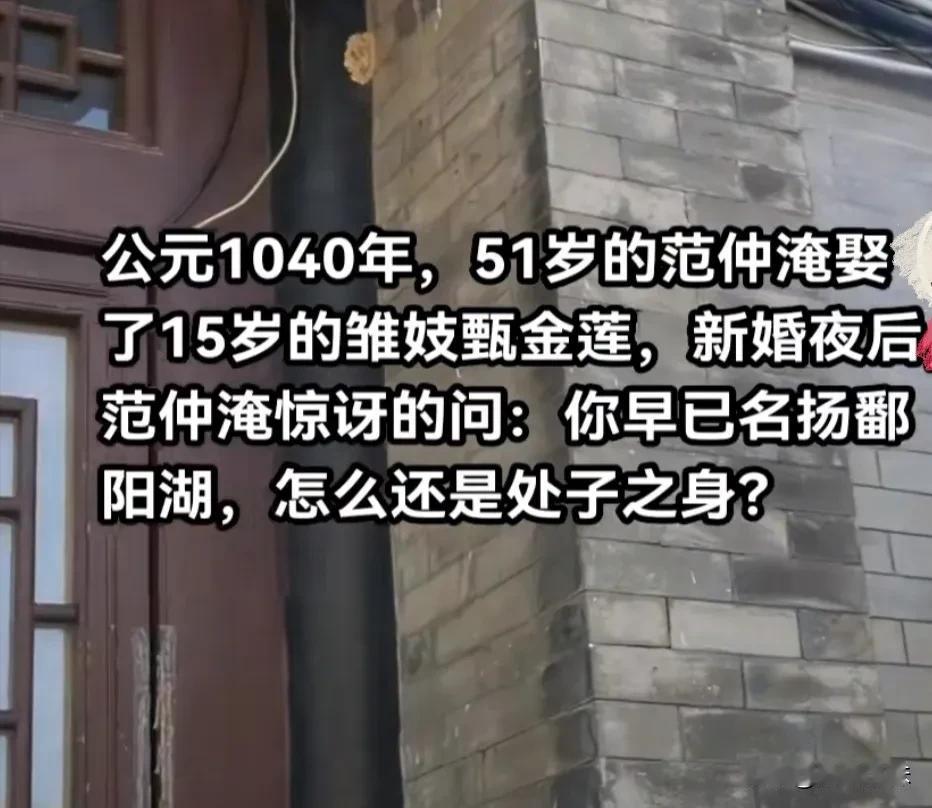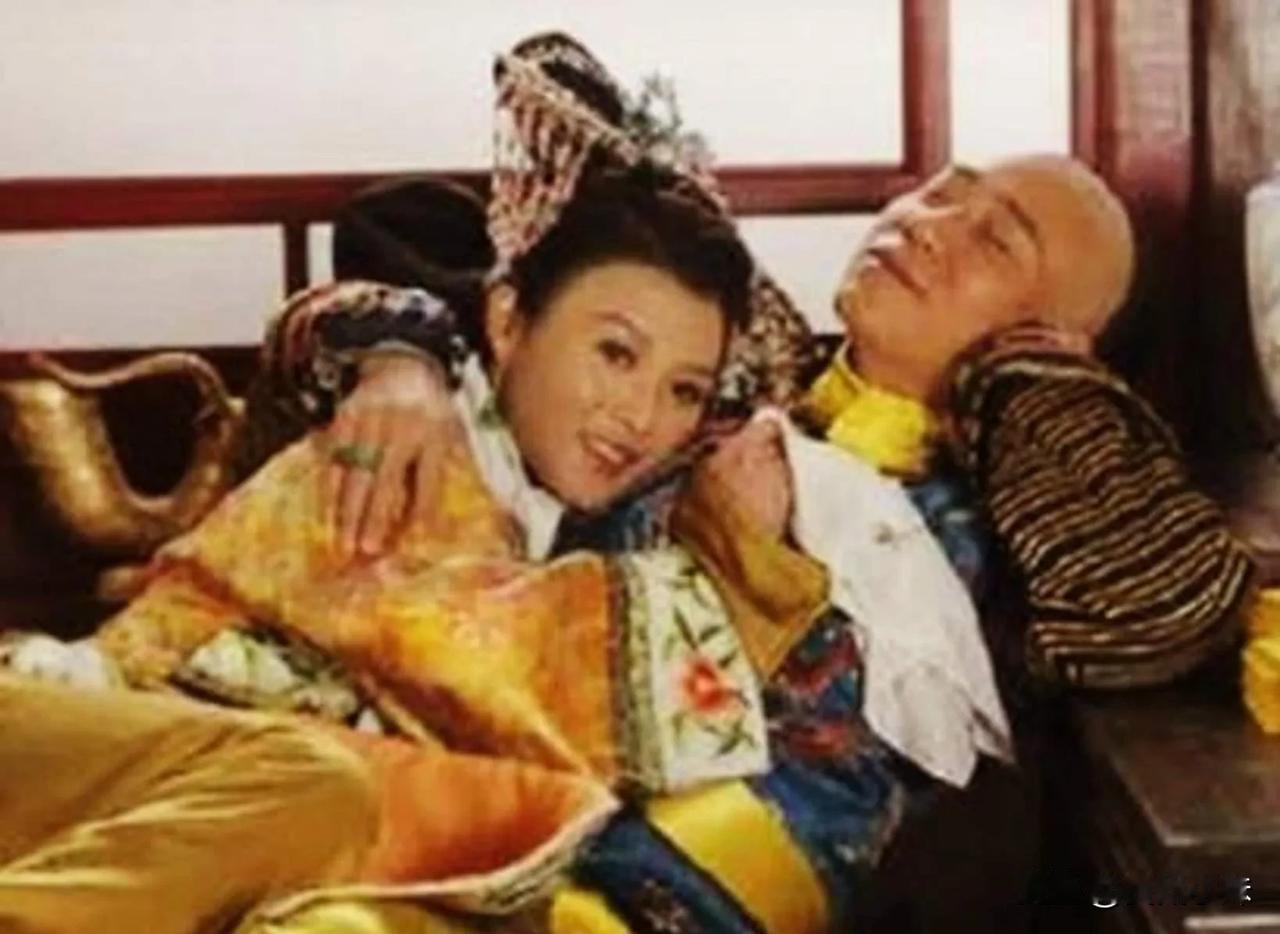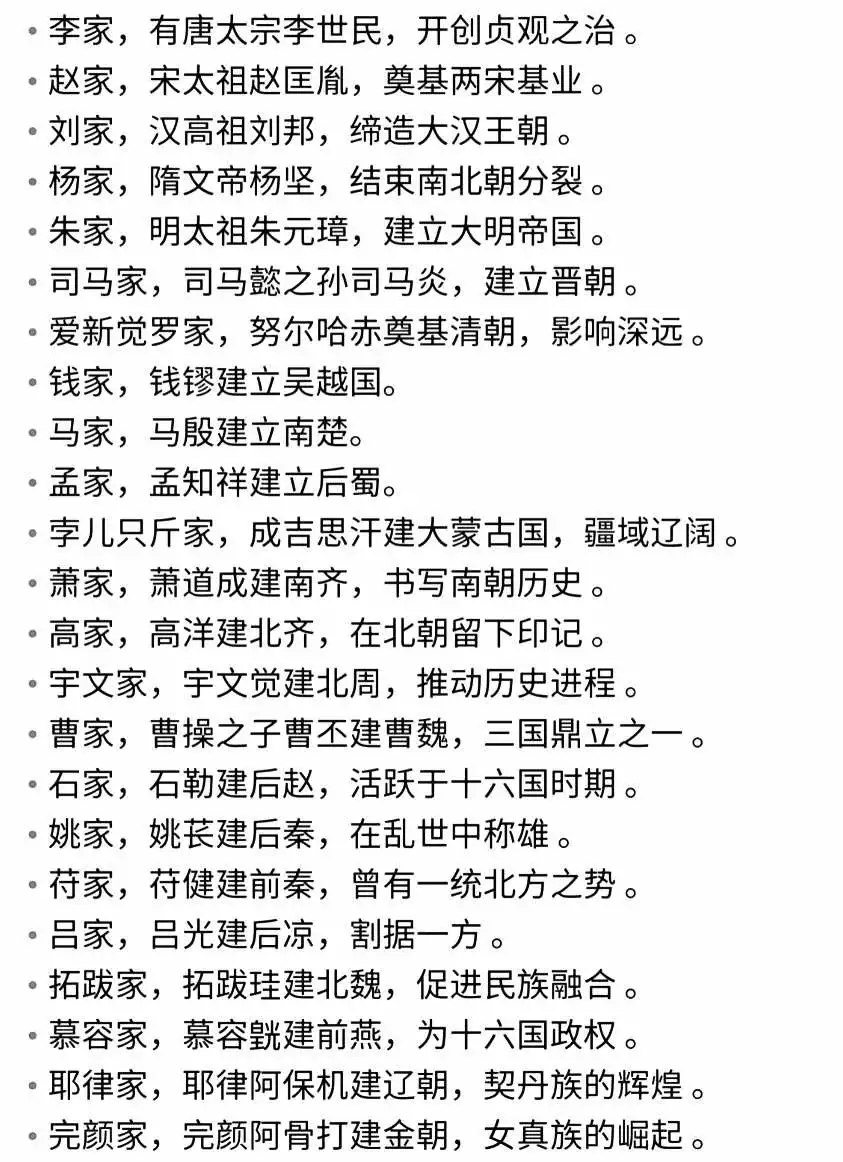1040年,51岁范仲淹娶15岁青楼女子甄金莲。洞房夜,范仲淹惊讶发现新娘竟是处子之身,不禁问道:“如夫人名扬鄱阳湖一年多,怎么还是完璧之身?” 红烛跳动着,映得甄金莲脸颊泛着泪光。她攥着衣角,指节都泛了白,半晌才低声开口:“大人容禀,小女本是饶州秀才之女,去年家父遭人诬陷贪墨官粮,满门流放,我被恶奴卖入青楼。” 声音发颤,却透着股倔强,“老鸨逼我接客那日,我揣了把剪刀抵着心口,说谁敢碰我,就见官去——他们怕惹官司,才只让我弹唱卖艺。” 范仲淹。这年他51岁,早已不是年少时那个在醴泉寺断齑划粥的穷书生。朝堂上,他因直谏被贬过四次,却始终梗着脖子不肯低头;西北边关,他正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主持防务,西夏人见了他的“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”的旗号,都得绕着走。这人一生清介,吃饭连肉都舍不得多吃,却在鄱阳湖见到甄金莲那天,当众拍板要娶她。 同僚们私下里嚼舌根,说范大人怕是老糊涂了。青楼女子,还是个名声在外的,传出去不怕毁了清誉?范仲淹只淡淡一句:“看人要看骨头,不是看去处。” 洞房里的红烛烧了半寸,范仲淹听完甄金莲的话,沉默了。他想起自己年少时,继父家道中落,他背着行囊去应天府求学,寒冬腊月里冻得脚生冻疮,不也靠着一股“不认输”的劲熬过来?眼前这姑娘,揣着剪刀抵着心口的模样,怕是比他当年还难。 “你父亲的案子,有凭证吗?”他忽然问。 甄金莲愣了愣,从枕下摸出个皱巴巴的纸团。是父亲被抓前偷偷塞给她的,上面写着诬陷者的名字和几笔可疑的账目。范仲淹借着烛光细看,眉头越皱越紧——那账目上的字迹,他竟有些眼熟,像极了去年被弹劾的饶州通判。 第二天一早,范仲淹没去军营,反而叫人备了马,直奔饶州方向。他知道自己这举动冒险,边关军务正紧,私自离境可能被参。可他忘不了甄金莲昨晚说“家父一生清白”时,眼里强忍着的泪。 查案查了整整半月。范仲淹扮成商人,在饶州乡下摸查,终于找到当年经手粮库的老吏。老吏起初不敢说,被他堵在柴房里,听他说“我范仲淹一生不做亏心事,今天就是拼着乌纱帽,也要还冤者一个公道”,才哆哆嗦嗦拿出证据——那通判为了填补自己的亏空,故意栽赃给了刚正不阿的甄秀才。 真相大白那天,范仲淹回到家,甄金莲正在廊下晒书。见他回来,她手里的书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嘴唇哆嗦着,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范仲淹捡起书,轻声道:“你父亲的案子,翻了。” 甄金莲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,不是委屈,是松快。她这才知道,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三十六岁的男人,娶她不是一时兴起,是真的把她的委屈放在了心上。 婚后的日子,过得平静。范仲淹在边关忙,甄金莲就在家里打理,把他那些被幕僚嘲笑“寒酸”的旧衣浆洗得干干净净,把他写的奏折草稿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有时范仲淹熬夜看兵书,她就坐在旁边磨墨,不说多余的话,只在他咳嗽时递上一杯温热的蜜水。 有人又嚼舌根,说甄金莲终究是青楼出来的,登不得大雅之堂。范仲淹听了,在一次宴会上指着甄金莲道:“她父亲是忠臣,她本人是烈女,比那些只会空谈道德的伪君子干净百倍。” 后来西夏议和,范仲淹回朝任参知政事,推行庆历新政。忙得脚不沾地时,总有人看见他案头放着一方绣着莲花的砚台——那是甄金莲亲手绣的。 1052年,范仲淹病逝于徐州。临终前,他拉着甄金莲的手,断断续续说:“你父亲的坟,记得……每年去扫扫。”甄金莲含泪点头,她知道,这是他记挂了一辈子的事。 范仲淹死后,甄金莲没再嫁。她把范仲淹的文稿整理成册,其中就有那篇后来名扬天下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有人说她傻,守着个老头子的遗物过一生。可她在整理文稿时,看到范仲淹早年写的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总会想起洞房夜那支跳动的红烛,想起他为父亲翻案时奔波的背影。 这世间的感情,从来不止风花雪月。有时是一句承诺,是一场坚守,是两个受过苦的人,借着彼此的温度,把日子过成了光。就像范仲淹,他护了甄金莲的清白,甄金莲也守了他一生的风骨。 信息来源:参考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《宋人轶事汇编》相关记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