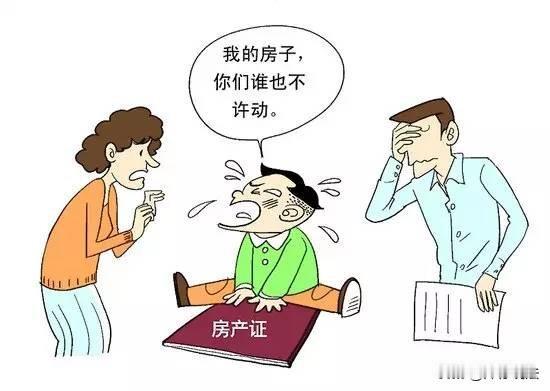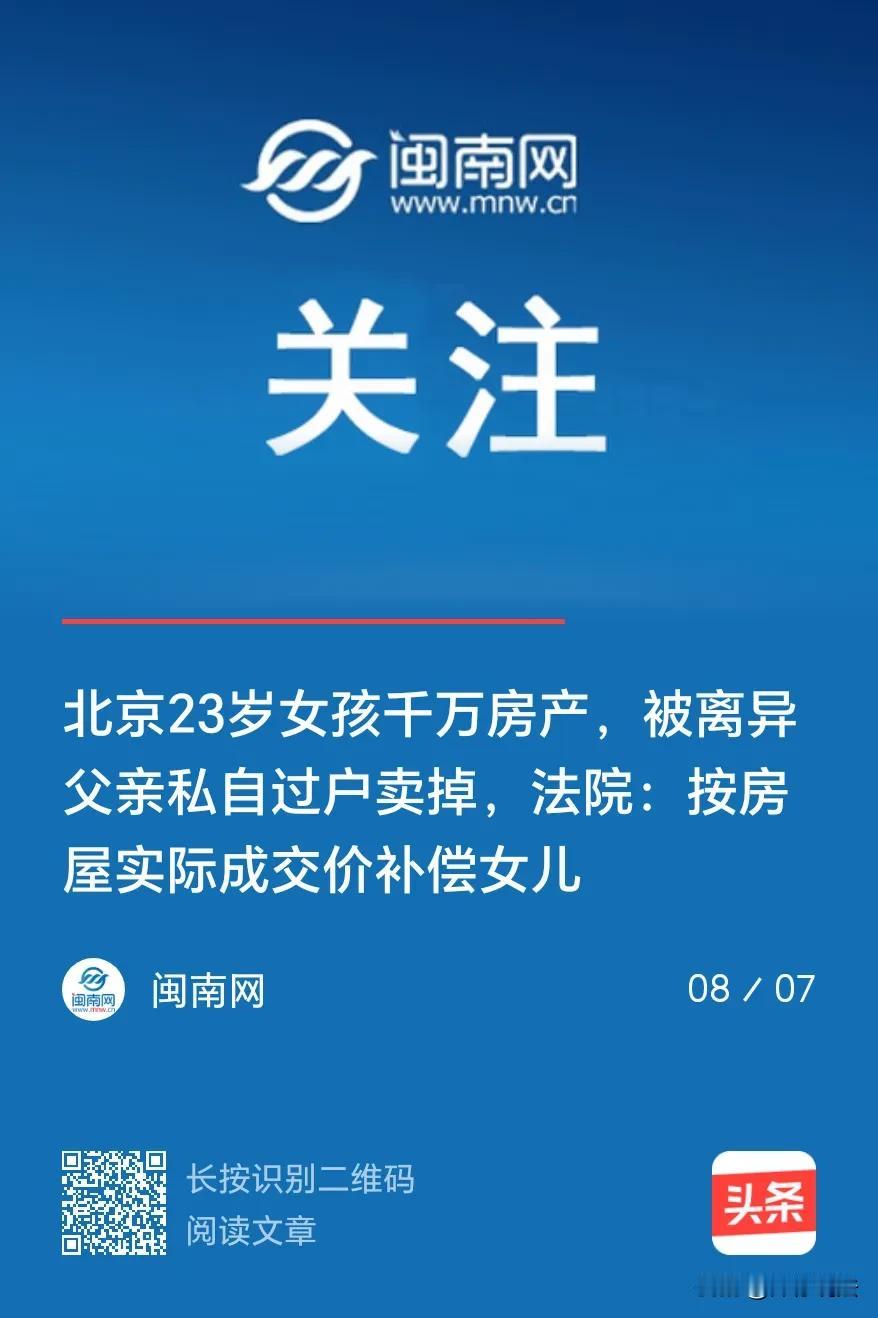北京,一女孩在5岁时,父母就把一套房子登记在她名下。父母离异后,父亲成了她的监护人。然而,在女孩14岁时,父亲偷偷以女儿“代理人”身份,和自己签了份“赠与合同”,把女儿价值千万的房子“送”给了自己!紧接着,他火速过户、转手卖给他人,套现1160万。多年后,女孩成年归来发现“家”没了,愤而将父亲告上法庭,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,并赔偿1160万元。庭审中,父亲辩称钱花在了女儿留学和付前妻补偿上。但法院判决出乎意料。 据闽南网8月7日报道,二十三岁的小王(化名)从海外留学归来,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想回到童年记忆里的那套温馨的房子看看。 然而,当她拿着钥匙来到海淀区那套熟悉的房门前,开门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,对方疑惑地告知:“这房子我几年前就买下了。” 小王如遭雷击,那套父母在她五岁时就登记在她名下的房子,她记忆中永远的家,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消失了。一场围绕千万房产归属的亲情与法律之战,就此拉开序幕。 时光回溯至2002年,小王诞生在王先生(化名)与张女士(化名)组建的家庭中。 2007年,出于对女儿未来的深切关爱,王先生和张女士共同出资在海淀区购买了一套房产,并明确将产权登记在年仅5岁的女儿小王名下。 这一行为在法律上意义重大,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条规定,房屋登记在小王名下,该房屋即成为小王的个人合法财产,其父母作为出资人,并不因此享有该房屋的物权。 然而,家庭的和睦并未持久,王先生与张女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,双方在法院主持下离婚。 法院判决女儿小王由父亲王先生抚养,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,因涉案房屋登记在小王个人名下,该房屋明确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范畴,法院未对其进行分割处理。 这一处理虽符合法律规定,却也为后续风波埋下了伏笔,因为父亲王先生作为监护人,实际掌控着女儿名下的巨额财产。 2016年,时年14岁的小王尚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,王先生作为其法定监护人,本应恪守职责,维护女儿的最大利益。然而,王先生却利用其监护人身份,上演了一出荒诞的“独角戏”。 王先生先是以女儿小王“代理人”的身份,与自己作为受赠人签订了一份《赠与合同》,声称小王自愿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自己。 接着凭借这份“左手赠右手”的合同及其他相关手续,王先生成功地将房屋产权从女儿小王名下过户到了自己名下。 完成过户后,王先生立即以1160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案外人,完成了对女儿财产的彻底转移。 成年后的小王惊悉真相,悲愤交加,毅然将父亲王先生告上法院。 面对女儿的指控,王先生提出了两点主要抗辩: 第一,辩称售房所得款项主要用于支付女儿小王昂贵的海外留学费用,是“为了女儿的利益”。 第二,声称因离婚后需向前妻张女士支付一笔款项,迫于经济压力才“无奈”出售女儿房产以筹措资金。 那么,法院会怎么判决呢? 一审法院首先确认涉案房屋自2007年购买时起即登记在小王名下,依据《民法典》物权编规定,该房屋所有权依法属于小王个人,从未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。 王先生作为法定监护人,在处分被监护人小王名下价值千万的房产时,未征求当时已年满14岁、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女儿本人的意见,完全无视被监护人的意愿。 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,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。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,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 王先生的行为直接违反了监护职责,侵害了女儿的合法权益。 对于王先生所谓“为女儿利益”的抗辩。 法院进一步指出,王先生未能提供任何有效、充分的证据证明售房款实际用于了女儿留学,其陈述仅为单方口头辩解。 而王先生将女儿名下的巨额房产无偿赠与自己再出售套现,与直接使用该房产收益或在其成年后协商处置相比,显然不是“最有利于被监护人”的处置方式,损害了女儿利益。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和法律分析,法院认定: 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,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 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,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,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 王先生同时作为代理人和受赠人,构成自我交易的恶意串通,王先生以小王名义与自己签订的《赠与合同》自始、当然、确定无效。 但是,由于房屋已被出售给善意第三人,小王要求返还房屋本体的请求客观上无法实现。 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,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……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,应当折价补偿…… 最终,法院判令王先生按照该房屋的实际成交价格1160万元向女儿小王全额赔偿。 王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。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,全面认同了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及判决结果上的正确性,裁定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