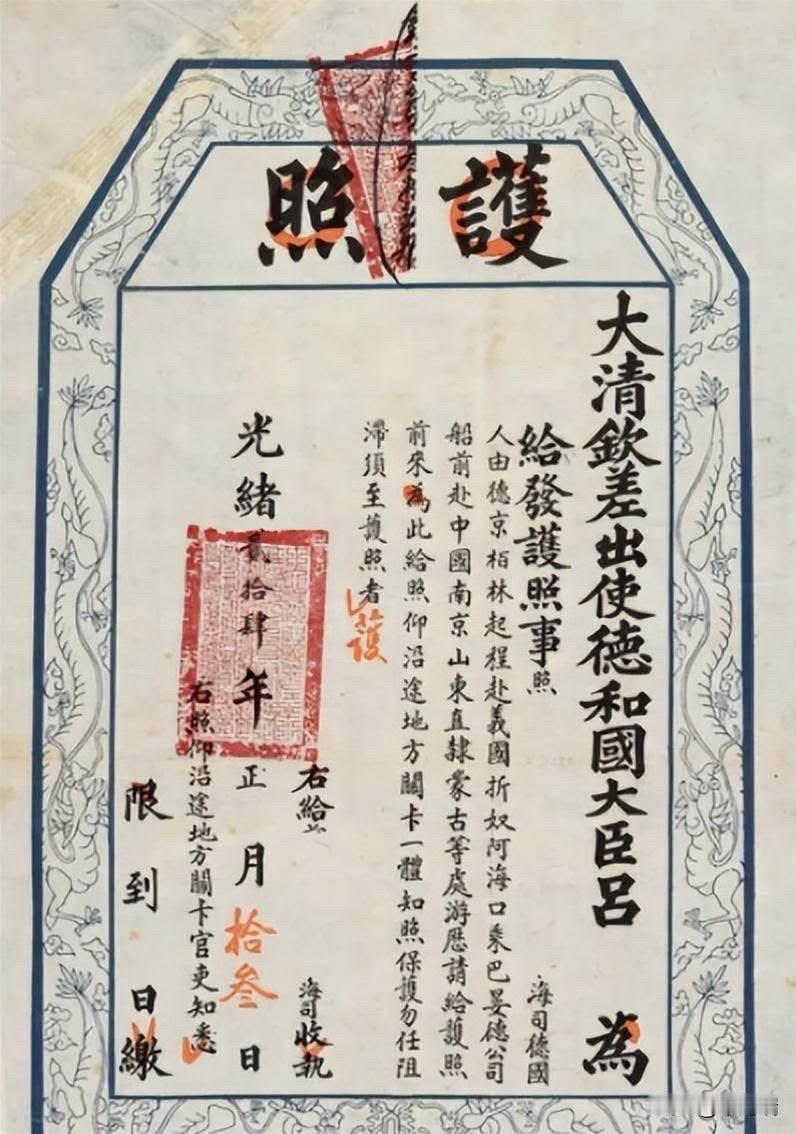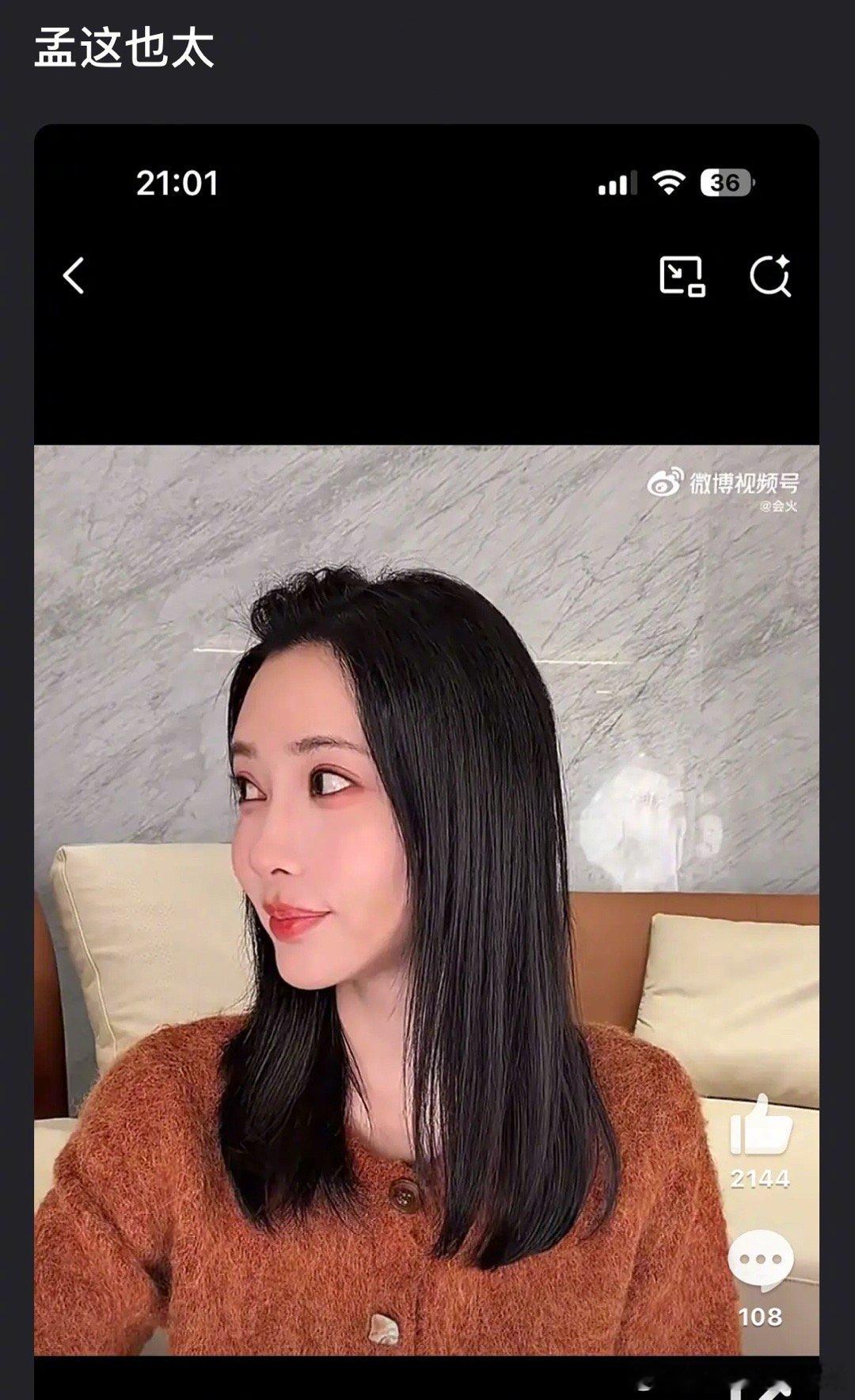[微风]1956年,国学大师钱穆,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。新婚夜,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,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,不禁流下了眼泪。 1895年钱穆在无锡出生时,哭了整整三天三夜,父亲钱承沛一边哄着这个婴孩,一边叹息:“此儿当命贵,误生吾家耳!” 这话像句谶语,父亲没能看到儿子显贵,钱穆12岁那年,父亲撒手人寰,孤儿寡母,家道中落,若不是母亲硬顶着压力不让他辍学,中国历史上可能就少了一位史学大家,多了一个无锡乡间的庸碌农夫。 钱穆这辈子,似乎总在和“丧失”做交易。 1928年,对他来说是个黑色的年份,第一任妻子邹氏难产,大人孩子都没保住,同年,一直如父兄般照顾他的长兄钱恩第也走了,那年钱穆刚过三十,还没来得及在学术界站稳脚跟,死神就先把他的亲情网络剪了个稀烂。 那种对生命无常的恐惧,逼出了他骨子里的求生欲,他常说“人生不寿是罪恶”,这话听着极端,却成了他后半生的行动指南。 从20多岁起,他就开始苦练静坐,如果不是这股子硬要把命留住的劲头,他恐怕熬不过后来的颠沛流离,更活不到95岁的高寿。 也就是在第一次丧妻的次年,他续弦娶了张一贯,这位苏州女师的校长,识字知书,给了他一段安稳的岁月。 可时代的大浪打过来,个人连朵浪花都算不上,1937年抗战爆发,钱穆只身流亡大西南,妻儿留守苏州,1949年政权更迭,他滞留香港,一道海峡,彻底把他和大陆的妻儿变成了“生离”。 这一别,就是半生。 在香港的日子,钱穆是个精神上的贵族,生活上的难民,他创办新亚书院,那是为了给中华文化留条根,但日子过得那是真苦。 也就是在这个当口,胡美琦出现了,她是新亚的学生,原本只是仰望讲台上的先生,如果不是1952年那场几乎要了命的意外,两人也就是师生一场。 那年钱穆在台北演讲,礼堂年久失修,屋顶的水泥块轰然坠落,直接砸在他脑袋上。头破血流,当场昏迷。 这一砸,砸断了钱穆的傲骨,也砸开了胡美琦的心门。 钱穆在台中养病那四个月,胡美琦不仅是护工,更是唯一的精神支柱,彼时钱穆已是花甲老翁,且家中有妻,胡美琦才二十出头,风华正茂,钱穆懂礼教,也知分寸,伤好后一度躲着胡美琦,不想耽误人家姑娘。 但胡美琦有着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决绝,她不看年龄,只看灵魂。 最终,才有了1956年钻石山下的那一幕,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“老夫少妻”的风流韵事,而是两个在乱世中飘零的灵魂,为了生存和学术传承,缔结的一种深度契约。 婚后的日子证明了这一点,对于晚年的钱穆来说,胡美琦早已超越了“妻子”的定义,她是他的“眼”,也是他的“手”。 长期的伏案工作,让钱穆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,晚年几近失明,对于一个以读书写作为命的学者,瞎了眼就等于判了死刑。 这时候,胡美琦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,在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里,人们常能看到这样一幕:钱穆口述,胡美琦笔录,那些晦涩深奥的理学概念,经由失明老人的口,变成妻子笔下的墨迹。 震惊学界的百万字巨著《朱子新学案》,就是在这种近乎悲壮的配合下完成的,没有胡美琦这副“肉身支柱”,钱穆的学术生命早在1970年代就该画上句号了。 1990年,95岁的钱穆在那间没有冷气的卧室里安然离世。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真正的和解,发生在死亡之后,胡美琦成了那个“未亡人”,她用了余生整整22年,整理出版亡夫的全集,满世界推广他的学术,直到2012年,她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 这时候,钱家做出了一个极具人情味的决定。 钱穆与原配张一贯所生的子女们,并没有因为历史的隔阂而排斥这位继母,相反,他们感念胡美琦对父亲晚年的照顾,将她的灵柩接回了无锡老家。 太湖之滨,钱穆的墓旁,最终多了一个位置。 “生当同衾,死当同穴”,这句古话,在这对相差34岁的夫妻身上,以一种最曲折的方式应验了,这场婚姻,背负过原配家庭的眼泪,经历过贫民窟的困顿,扛住了失明的绝望,最终在时间的冲刷下,得到了伦理与亲情的双重谅解。 参考:钱穆先生与苏州——《钱穆家庭档案》新书苏州发布 江南时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