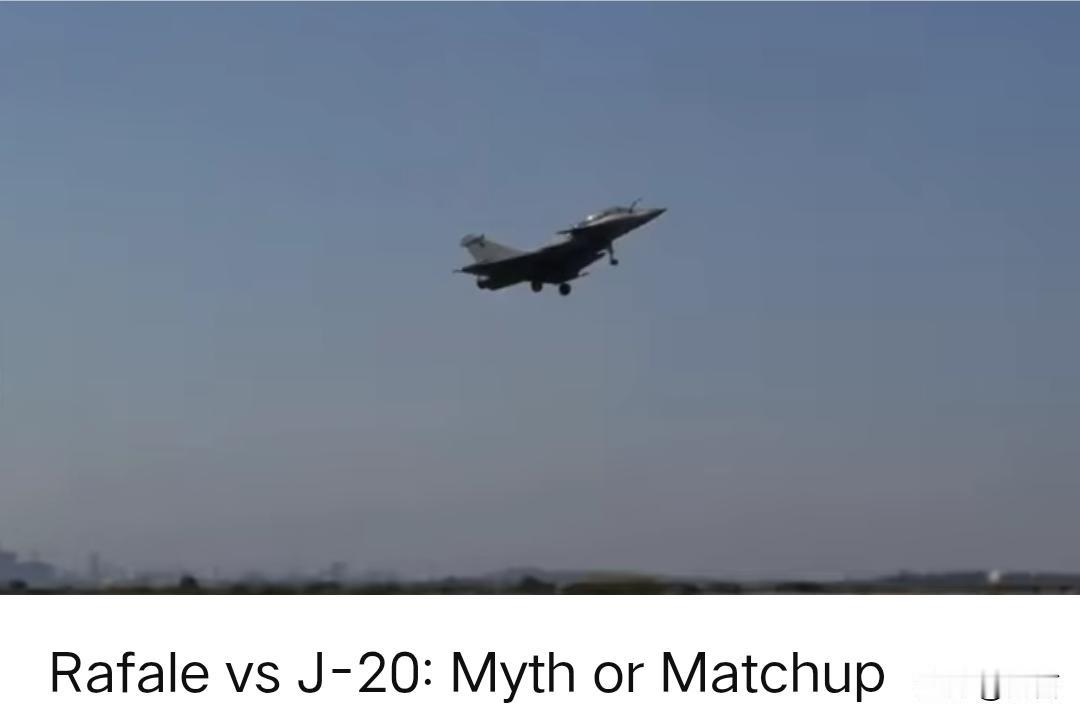1991年边防巡逻,我把水壶让给一个快渴晕的喇嘛,他喝了三口,突然抓住我:年轻人,今夜12点前必须撤离这片荒漠 我是1989年入伍的边防战士,1991年正驻守在西北边境的荒漠哨所,那年我刚满二十岁,那次巡逻是我和班长执行常规边境线巡查任务。九月的西北荒漠根本没有春秋之分,白天地表温度能突破五十摄氏度,滚烫的沙粒粘在作训服上,磨得皮肤生疼,我们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,是荒漠里唯一的活命水源,每一口都要省着喝。 那天我们已经徒步跋涉了八个小时,班长的水壶早就见了底,我的壶里也只剩浅浅一层底水,连润嗓子都不够。走到一片乱石滩时,我瞥见沙地上瘫着一个人,走近才看清是位穿着破旧藏袍的喇嘛,他脸色蜡黄,嘴唇裂得翻起了血皮,整个人虚弱得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,明显是长时间缺水陷入了半昏迷状态。 我没丝毫犹豫,直接拧开自己的水壶递到他嘴边。在边防待久了都懂,荒漠里见死不救是最狠心的事,哪怕自己渴着,也不能看着同胞熬不过去。喇嘛的手不停发抖,凑着水壶只喝了三口,就猛地把水壶往我怀里推,嘴里念叨着不能多喝,反复说够了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没关系,他突然用尽全力攥住我的手腕,指节都绷得发白,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急切,盯着我一字一顿地重复,今夜十二点之前,必须撤出这片荒漠,一刻都不能耽误。 我当时只觉得他是脱水产生了幻觉,这片荒漠我们巡逻了上百次,除了风沙、乱石和稀疏的骆驼刺,从来没见过任何突发危险。班长也快步走了过来,拍了拍喇嘛的肩膀,轻声安慰说我们熟悉路线,天黑前就能返回哨所,让他别担心。 喇嘛看我们完全不信,急得从沙地上撑着身子坐起来,他说自己常年在高原荒漠转经,对天地间的异动格外敏感,这片沙地底下一直在轻微震动,沙层的湿度和硬度都不对劲,不是普通的风沙天气,是要发生能吞噬一切的灾害。 我们年轻气盛,又有着常年巡逻的经验,压根没把这番话放在心上,只当是老人中暑后的胡话。我们谢过他的提醒,整理好装具就继续朝着巡逻终点走去,走出几十米远,我回头看了一眼,喇嘛还坐在原地,朝着我们不停挥手,嘴里还在喊着撤离的话。 走了不到两公里,我最先察觉到异常。原本纹丝不动的沙地,开始出现细碎的起伏,零星的小石子莫名滚动,空气里的燥热突然变成了沉闷的压抑,连风都停了,整个荒漠静得可怕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莫名想起喇嘛急切的眼神,忍不住拉了拉班长的衣角。 班长是驻守边防五年的老兵,比我敏锐得多,他抬头看了看天,原本湛蓝的天空已经蒙上了一层暗黄色,远处的天际线泛起诡异的土雾。他没有丝毫迟疑,当即下令掉头,全力往哨所方向撤离,没有多余的指令,脚步却快得惊人。 我们拼了命地奔跑,荒漠里没有固定道路,全靠记忆辨别方向,嗓子干得像要冒烟,双腿沉得像灌了铅,却不敢有一秒停歇。身后的沙地震动越来越明显,耳边开始传来细微的轰鸣声,那是荒漠发怒的前兆。 晚上十一点四十,我们终于跌跌撞撞冲进了荒漠边缘的安全哨所,值守的战友还没来得及问话,身后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声响。我们扑到窗边望去,刚才巡逻的整片荒漠,被数十米高的沙墙彻底吞噬,十二级以上的强沙尘暴裹挟着碎石,横扫了整个区域,连远处的沙丘都被削平了大半。 后来气象部门通报,这是当地百年不遇的特强沙尘暴,受灾区域内无一生还可能。我们靠在墙上,浑身被冷汗浸透,要是晚撤离半小时,此刻早已被埋在百米厚的沙海之下,连尸骨都找不到。 我们第二天返回寻找那位喇嘛,想当面道谢,却再也没见到他的身影,乱石滩上只剩一串他掉落的木质佛珠,被风沙埋了一半。三十多年过去,我早已退伍回乡,成家立业,可那串佛珠我一直带在身边。 我总想起1991年的那个下午,三口救命水,换来了一句生死提醒,素不相识的陌生人,用自己的经验救了我们两条命。边防战士守着边境线,守护着国土安宁,而普通百姓的善意,也在不经意间守护着我们。 荒漠的残酷让人敬畏,人间的善意更让人铭记,这场生死际遇,成了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记忆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