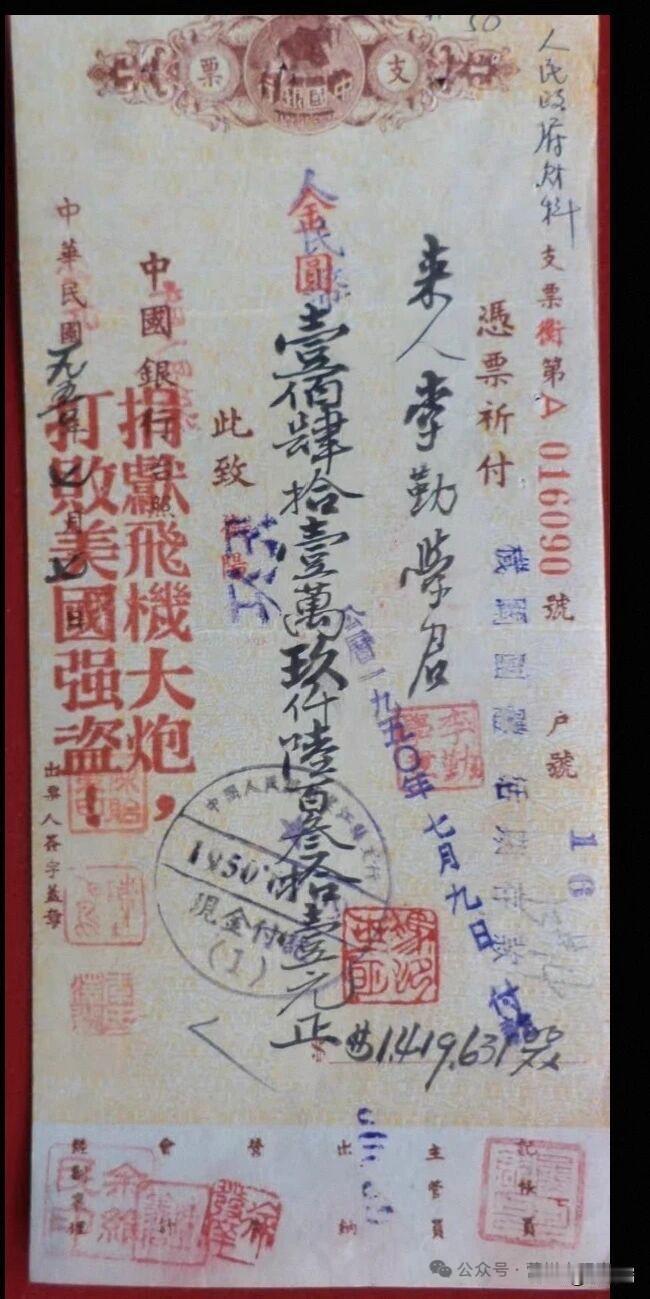1981年,74岁的粟裕大将,向中央请求“我想回家乡看看”。经过一番讨论,中央拒绝了将军的请求。将军眼含泪水,满脸悲凉。 那泪水砸在病号服的手背上,也砸在在场所有人心里。人到了这个岁数,心里那点念想就跟野草似的,压了一辈子,到快入土的时候反而疯长。可中央为啥不答应?是真不近人情吗?咱们得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。 粟裕想回的那个家,在湖南会同,一个叫枫木树脚村的小地方。他十七岁那年离开家,说是出去求学,实际上就是跟旧家庭决裂,跟那个给他定下亲事、想把他拴在田地上的父亲彻底翻脸 。谁能想到,码头一别,竟是永别。后来他父亲因为受他牵连,东躲西藏,死在了外头。这事儿在粟裕心里是个疙瘩,几十年解不开 。 其实他这辈子不是没机会回去。解放后他在南京主政,离湖南也就几步路的事儿。当时他老娘被接到南京住过一阵,母子俩二十多年没见,老太太摸着他的脸直掉泪。按理说,把娘送回去的时候顺道拐一趟,也就是多踩一脚油门的事。可那时候他脑子里装的啥?是解放台湾、是剿匪、是国防建设。他一听说回一趟家得要一个加强连护送,得惊动地方政府,得花钱,立马就把念头按下去了 。他心里头有杆秤,那头是公,这头是私,公私一称,私的那头永远轻飘飘的。 到了1981年,这杆秤终于歪了。人躺在病床上,脑血栓、高血压、心肌梗死挨个来,太阳穴跟针扎似的疼——那是1930年在水南战役里钻进脑袋的三块弹片在作怪,这几块铁在他颅骨里藏了半个多世纪,后来火化时才取出来 。这时候他再想回家,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那个劲儿了,就是想死之前,脚底板再沾一沾故乡的泥,眼睛再瞅一眼屋后头那棵枫树。 中央那帮老战友看了他的请求信,心里头比谁都难受。特别是胡耀邦,他咋拒绝?不拒绝行吗?从北京到会同,两千来里地,那时候的路况,火车倒汽车,汽车换拖拉机,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,路上万一出了事,谁担得起这个责?那不是送他回家,那是送他上路 。 这拒绝里头,其实藏着另一层意思:国家把这位老将看得太重了。重到不敢让他冒一丁点儿风险。可这份看重,落在粟裕眼里,却成了彻底的悲凉。他懂,他都懂,就是懂了才更难受。 这件事儿让我想起现在的人。咱们现在想家了,高铁飞机,朝发夕至,朋友圈一发定位,就算“到此一游”了。可粟裕这一辈子,打了那么多胜仗,救了那么多人,最后却输给了一张回家的车票。他不是没条件,他是不肯用那个条件。他觉得因为自己回家,让地方上兴师动众,让乡亲们夹道欢迎,让国家掏钱,那是罪过 。 所以那天他含着泪,什么也没说。只是从此以后,病房里的粟裕话少了,眼睛却总往南边看。 1984年,他走了。家里人按他的遗嘱,把骨灰分了两份,一份撒在他打仗的地方陪战友,一份终于带回了会同,埋在了那棵大树底下 。离家六十载,回来的时候,不过是一捧灰。 说到底,中央当年的拒绝,是心疼他;可这份心疼,也成了他最后的遗憾。这种矛盾,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太多了。他们把最好的自己给了这个国家,把最亏欠的自己留给了家人,到最后,连落叶归根都得掰成两半算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