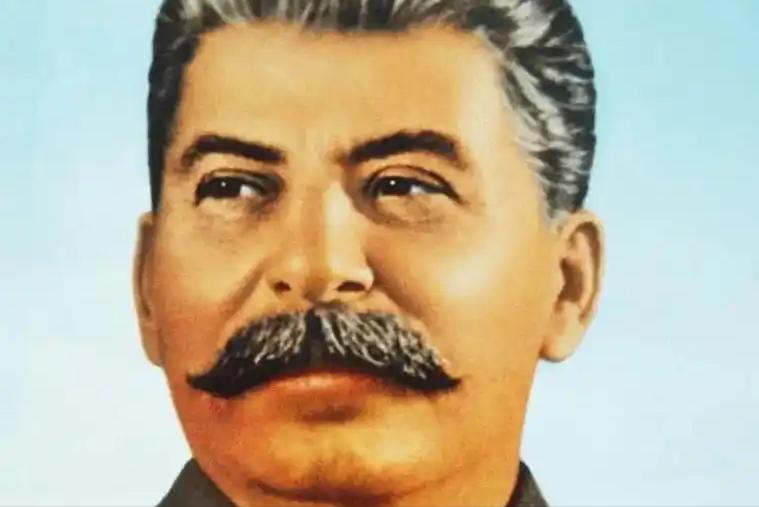有人养麻雀,不为了吃肉,就盯着它屁股底下那点粪,晒干了,捻成粉,一斤能卖上百块,可就这么个小东西,在五十年代,是要被全国清剿的头号“害鸟”。 一个冬天的早晨,天才蒙蒙亮,老陈已经提着小铲子挨个蹲在麻雀笼前头,目光专注,动作轻,小心翼翼地把一撮撮灰白色的粪便归拢进一个瓷碗里。 屋里不大,却散发着一股特别的味道,说不上恶臭,却也绝对不好闻,但老陈的眉头一丝没皱。 他干翻过的活不少,给人砌砖、卸车、在山沟沟里下过煤井,也在城边的废品站里扒过钢筋。 但他一说起现在这行,就让人听得两眼放光:“这不是屎,这是白丁香,一克几块钱,一斤上百!” 谁能想得到,50多年前,在镇上的广播喇叭里,这玩意儿的主人还是“人民公敌”。 1958年春,天刚暖,苏北一个叫青墩的村子,村支书脑袋上缠着白纱布,拉着全村人站在稻田边上,左手拿锣,右手掂扫帚,准备对天干一仗——打一场“响声震飞雀”的仗。 那时候,麻雀是“四害”之一,列在老鼠、苍蝇、蚊子前面,一周前镇上发通知,要大家齐上阵,“人不拼鸟,粮食就没命!” 村里小孩爬上树掏窝,大人上山围猎,锣鼓震天,麻雀没地方落脚,个个飞到累死,记录里说,那一年,北京一天打了八万只,全国范围不到两年灭了16亿。 但有些后果,很快显现。 麻雀从田野里消失了以后,虫子先觉察了,谷子的叶开始发卷,被绿色的小虫咬穿,红薯地里冒出一大片蝼蛄,不出一个农忙季。 村里看得明白,虫子比麻雀更贼:“原先一只麻雀吃麦粒,我们紧张;现在十虫抢一穗,连苗都啃光了。” 类似的报道很多:黄河滩上蝗虫啃光苞谷,那曲地区跳虫爆发;连远在东北的黑土地都窝了一批进口的“东风螺”。 一个局外人如果听到这事,可能会以为这不过是哪部纪录片的帧剪,但全国吃过麻雀少的苦——是实实在在的历史。 到了1960年,情况无法忽视,麻雀悄悄地从“黑名单”里溜出来。 报纸上不多做解释,公文里也极少有澄清,但一些当初积极“驱雀”的地区,突然接到通知:去苏联进口点回来。 他们不会料到,这成群结队坐火车来的“树麻雀”,后来变成了现在我们城墙瓦楞上看到的灰褐色小家伙。 麻雀活下来了,很顽强,比人想象中聪明,它适应了新的环境、熟悉了城市的光怪,等到了一个它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新机会——它那点儿屎,成宝了。 “白丁香”,从《本草纲目》到一些残破的民间医书里,都有零星提及,说它“性温,味苦,入脾肺”,擂末和药草调制,能“利湿消食,去翳明目”,女眷熬汤洗澡可以清疹散毒。 这东西属于中医界里一个窄门道,慈禧用过它洗脸,有传说说那年宫中太监不懂收集法,结果用普通麻雀粪冒充,结果被怒斥,大量和珅旧藏都被拍卖换回一勺真货。 真假难辨,这段历史真假参半,但市价是真的压死人。 一只麻雀,吃料、喝水,养殖成本不高,但它一天拉的屎就那么点,干燥处理后没几克。 晒干、研磨、筛粉都是技术活,还得一手好眼神识真假,这就意味着,正常养几百只麻雀,一周收来的“白丁香”,还不够做一瓶中成药。 这个矛盾就出现了——养鸟不是为了吃肉,是为了屎,但屎得像药,一点不能糊弄。 老陈抱怨:“死两只,心疼倒不心疼,耽误的是一礼拜的产量,哪天拉稀了更糟糕。” 麻雀不能惊,不能短水短料,甚至温度稍一波动,它们就不拉屎。 这养殖,还真不是谁都能干。 2018年,江苏句容开过一个麻雀合作社,三年不到,黄了。 官方报告上说“市场反响一般”,可业内人知道,问题不是市场,是产出完全无法规模化。 麻雀,不像鸡鸭那么容易管控,它把自己看看得比我们还高:一见你靠近就立马静音装死,不吃不喝,等你转身了再蹦出半壳蛋皮。 那年北京四环边一家公司试图用全自动养殖设备干这行,没头半年,设备倒是调好,但鸟不合作,拉稀、拼命啄铁网,后来没办法,只好撤了场地。 问题来了,这一克上百的“黄金屎”,到底谁在买?吹是能吹,但卖得掉吗? 中药材市场上、私家药膳馆、少数正规中医院的秘方里,白丁香常年榜上有名。 “药柜里定制处方,麻雀粪不是高频项,但有。”一个南京中医院的药剂师低声说过,“真正用到它的,一年也就四五次,但药效确实有特殊反应,清毒止斑,抑菌也有效。” 这不是说全面替代市场,只是说明——它是真的有需求,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个“边角料”的世界。 从被全民喊打,到物以稀为贵,是麻雀自身的逆袭吗?说不上。更多的是人的认知越走越回头。 科学鼓吹理性,但很多有价值的传统却经不起添加剂和工业流程的侵蚀,“粪便入药”,听起来低级,但却能在绿山鲜草里找到万物互通的意义。 心理学有一句话:“你害怕的东西,未必不是你依赖的根源。” 麻雀吃粮,人恨;麻雀吃虫,地乐;麻雀消亡,生物链哀;麻雀复返,屎进药堂。 尊重生态,并不是因为我们多文明,而是因为不尊重它,我们吃不了兜着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