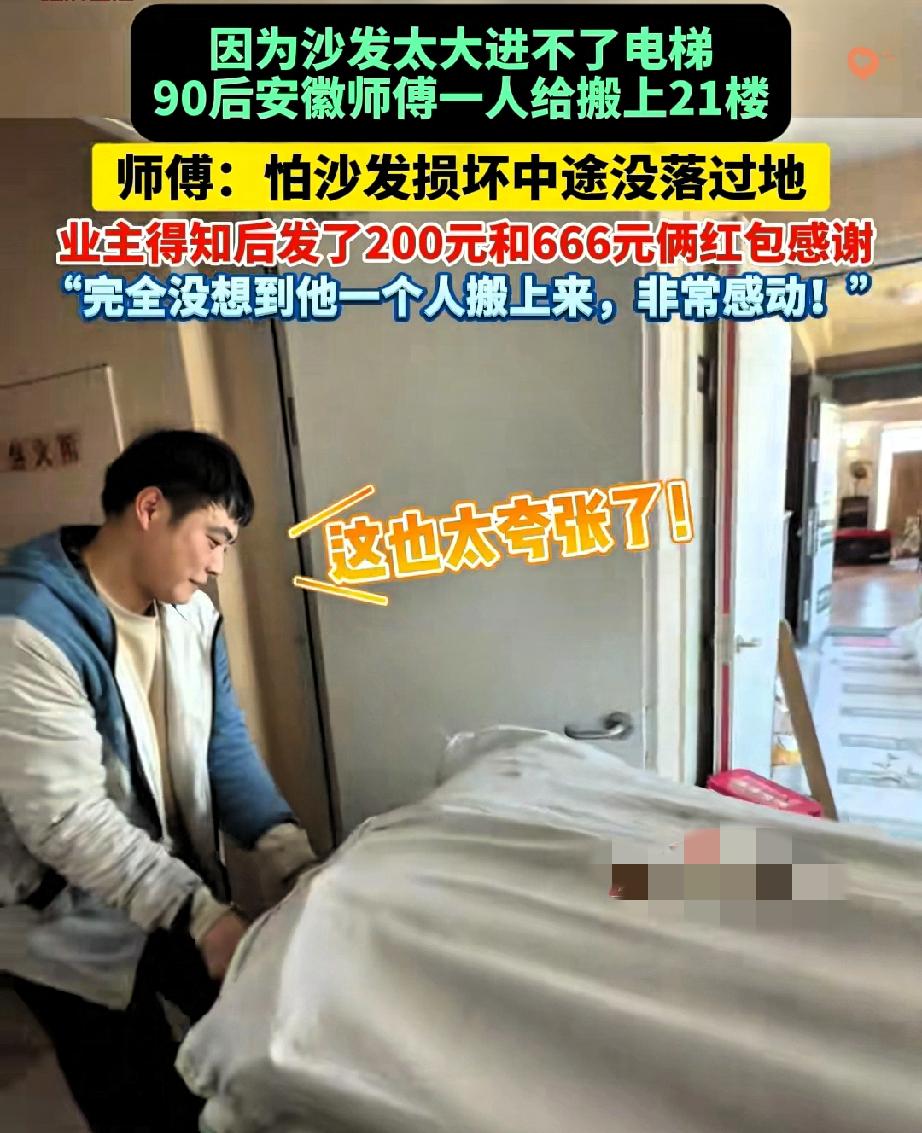1953年,民兵连长秦改朝在南京出差,走到雨花台附近街巷,听见一对卖烟的商贩夫妻吵架。女人骂得凶狠,男人低声回嘴。那男人说话带着一股熟悉的口音,还带点沙哑,尾音一拐。 秦改朝的脚步钉住了。这口音太熟了,熟得让他心口猛地一揪。不是南京本地的腔调,也不是他老家山东的味儿,那是……晋西北!对,就是晋西北山沟沟里那种裹着黄土、拐着弯的土话。1948年冬天,在太原城外围打阻击,他班里有个小战士就是这口音,总把“喝水”说成“豁水”。那小子才十七,牺牲前夜还念叨着打完仗回家吃莜面。 卖烟的男人背对着他,身子佝偻着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。女人还在数落,大概是嫌他收错了钱,或者烟匣子摆得不好。男人只是“嗯”、“啊”地应着,间或含糊地回一两个音,那沙哑的尾音,像被砂纸磨过。秦改朝当过兵,耳朵尖,他听出那沙哑不全是吵架上火,更像是一种旧伤,或者是……长时间不敢大声说话留下的痕迹。 1953年的南京,城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解放才四年,百废待兴,也鱼龙混杂。雨花台那地方,更是个特殊的所在,埋葬着无数英烈。 一个有着浓重北方口音的男人,为什么会流落到千里之外的南京,在街头卖烟为生?他经历了什么?秦改朝心里翻腾起来。他是民兵连长,职责里就有警惕可疑分子的成分。可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攥住了他——那口音勾起的,是战火纷飞年代里关于故乡、关于战友的记忆碎片。 他慢慢走近几步,假装看烟。男人的脸转过来了,黧黑,布满风霜的皱纹,眼神躲闪,看见穿着干部服的秦改朝,下意识地缩了一下。就这一缩,让秦改朝看得更清了。那不仅仅是小贩见着“官家人”的畏缩,那里面有更深的东西,是惊慌,是长久担惊受怕后养成的本能。男人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淡淡的旧疤,被皱纹掩盖着,不太显眼。 “老乡,听你口音,不是本地人吧?”秦改朝尽量让语气平和,递过去一支自己的烟。男人接烟的手有点抖,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,把头埋得更低:“早年……逃荒,乱走,就落这儿了。”女人也住了嘴,警惕地看着秦改朝。 逃荒?晋西北到南京,这荒逃得可够远的。而且1953年,大局已定,社会正在清理和安置流散人员,像他这样有劳力、口音独特的异乡人,当地政府一般会过问,安排个正经生计或遣返原籍,怎会一直在街头摆小摊?秦改朝没再多问,买了包烟,转身走了。他能感觉到,背后那两道目光一直追着他,直到拐过巷口。 那天晚上,秦改朝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。那口音,那道疤,那惊慌的眼神,在他脑子里拼凑。他想起在部队时听过的传言,有些在战场上被打散了的兵,或者家乡被敌人报复待不下去的基层干部,一路南逃,隐姓埋名,生怕被清查时说不清历史。他们像断了线的风筝,飘到哪里算哪里,用尽力气只想埋掉过去,当一个没有任何前史的“新人”。 那个卖烟的男人,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?他低声回嘴的忍耐,他眉骨的旧伤,他沙哑的嗓音,还有那句轻飘飘的“逃荒”,可能都藏着一段不敢触碰的往事。他或许曾是个民兵,或许是个支前民工,甚至在更早的混乱年代里,有过更为复杂的经历。 新中国成立的光明普照大地,但阳光总有照不到的缝隙,一些被时代洪流裹挟、冲刷到边缘的个体,就蜷缩在这些缝隙里,靠着最卑微的营生,守着或许永不能言说的秘密,默默活着。 秦改朝最终没有回头去找他,也没有向当地反映什么。他只是一个过路的出差干部。他把那包买来的烟抽完了,味道很呛。他想起雨花台的纪念碑。 历史记载了轰轰烈烈的牺牲,而那些沉默的、隐入市井的、带着伤痛和秘密活下去的人,他们的故事,谁来书写?他们的恐惧与生存,又该如何安放?那个晋西北的口音,像一根细细的线,一头连着战火与故乡,另一头,系在1953年南京街头的一缕廉价烟丝上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