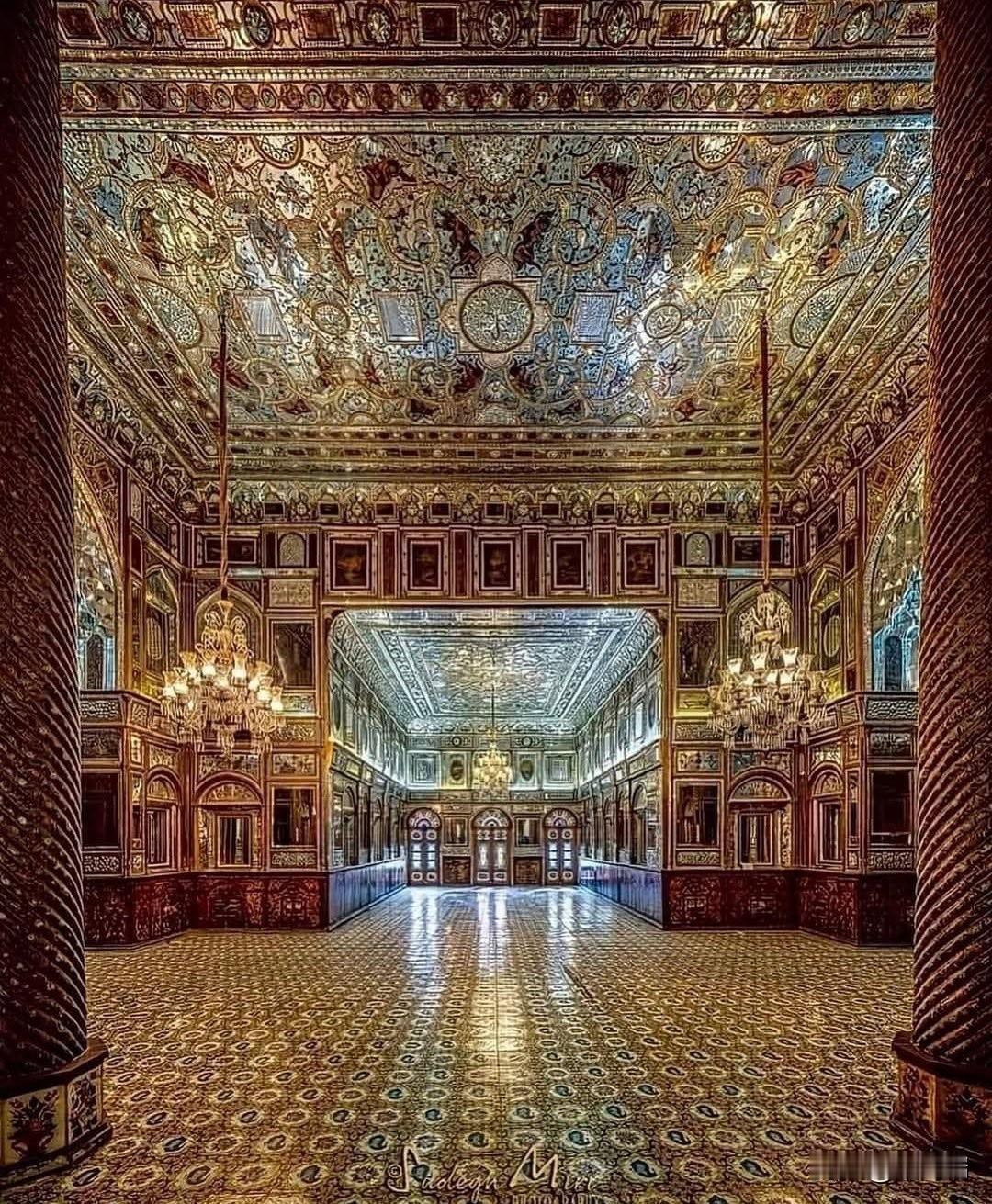1917年,刘文典到北大教书。一天,辜鸿铭问他:“你教什么课?”“汉魏文学。”刘文典恭敬地回答。“就你?”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。 1917年,刘文典带着对古典文化的迷恋走进北大。当时校内中西之争激烈,辜鸿铭衣着古旧,自负通中西,对西学情有独钟;刘文典则在角落里讲汉魏文学,既无名气,也缺著作。 那声“教古典文学?就你”,像针一样扎进心里。刘文典没有回嘴,只是把这口气压回书房,关门读书。 几年“闭关”,换来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横空出世。梁启超称其为《淮南子》研究的上乘之作,胡适罕见地用文言写序,鲁迅也掏钱买书。 北大课堂上,那位当年被轻视的青年讲起汉魏文人,能把遥远时代讲得活灵活现,学生听得如临其境。辜鸿铭偶尔去旁听,先是出于好奇,后来被那一份扎实与新意打动,图书馆里再遇时,只用极克制的一点头,承认对方并非“就你”那么简单。 成名并没有让刘文典安分。1928年,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,把对学问的执念搬进了校务。北伐期间,蒋介石打算来校“视察”,刘文典觉得大学不是衙门,礼节可以免,索性没露面。 等到学潮爆发,蒋介石把人叫去训话,刘文典当场点烟,听完“交出闹事学生”的命令后,只回一句“你是总司令,就管好你的兵;我是校长,学校的事情由我来定”。 这句话砸下去,他换来的是一个月黑牢和被迫离任,也把“狂人”的名头传遍学界。 关押期间,胡适、鲁迅等人纷纷出声力挺。走出牢门时,刘文典对记者说,如果连学术都要向权力低头,读书人就没脸再自称读书人。这种硬气,不是临场发挥,而是一整套人生选择的延伸。 到了西南联大,刘文典的“怪”和“狂”被学生看得更清楚。上课时声音低得听不清,却固执要在烟雾缭绕中讲《庄子》,学生只好围着坐得很近。 有人抱怨,他干脆丢下课本走人。空袭时,众人忙着往防空洞奔,他跑到半路又折回去,把视力不好、行动不便的陈寅恪扶下来,一边自嘲“跑是为了《庄子》”,一边默默用行动表达敬重。 刘文典的“狂”并不等于目空一切。他痛骂黄包车制度不近人情,却在课后坐上车回家,留下一句“我不坐,你们就没活干”,比课堂上再激烈的谴责更尖锐。 日本人抄家时,他昂着头拒绝说日语,撤离之后又埋头翻译日文资料,说要让国人真正看懂对手。 在课堂上,刘文典把汉魏文学和庄子讲得像家常话,又故意塞进几句“怪话”。学生问他为什么非要这样,他说,学问若讲得平平顺顺,没有一点让人拧眉的地方,那就不叫学问。 为了讲好一篇《月赋》,他把课排在夜里,借着月光让学生体会文字里的景致;冬天则抱着一本《庄子》蹲在湖边石凳上,看得忘了起身,用古书里的世界抵挡现实的寒意。 建国后,刘文典戒了鸦片,在云南成了唯一的文科一级教授。那时他已没有当年的锋芒,却仍坚持对经典的守护。 无论是在北大讲坛,还是在西南联大校舍,抑或在边远西南的课堂,他始终把汉魏与庄子当作与时代对话的工具,而不是躲避现实的借口。 1958年,刘文典离开人世。留在纸面上的著作不算多,留下的故事却在学生和同行口中说了几十年。有人记得那句“学问岂能因人改动”,有人记得为学生与总司令拍桌子的身影,有人记得夜半月光下讲《月赋》的声音。 回看这一生,刘文典的“狂”,其实是对学问与骨气的双重执念。被轻视时,用作品说话;被权力压时,用沉默和不合作抗争;被时代抛在角落时,仍顽固地守着几部古书。 正是这一份不肯弯的劲,让汉魏文学从嘲笑声中走向重视,也让后来人知道,知识分子的脊梁,不是写在头衔里,而是挺在选择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