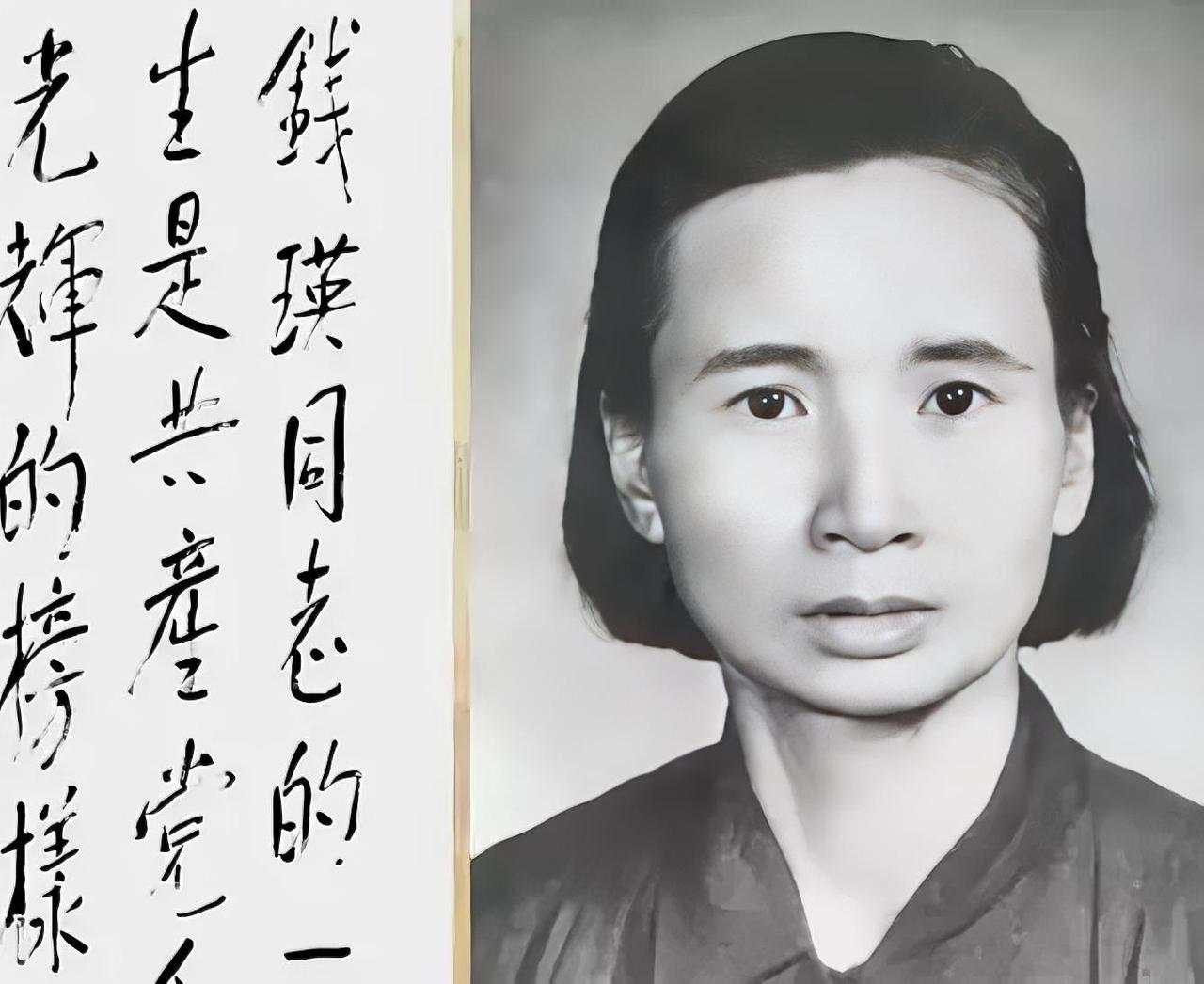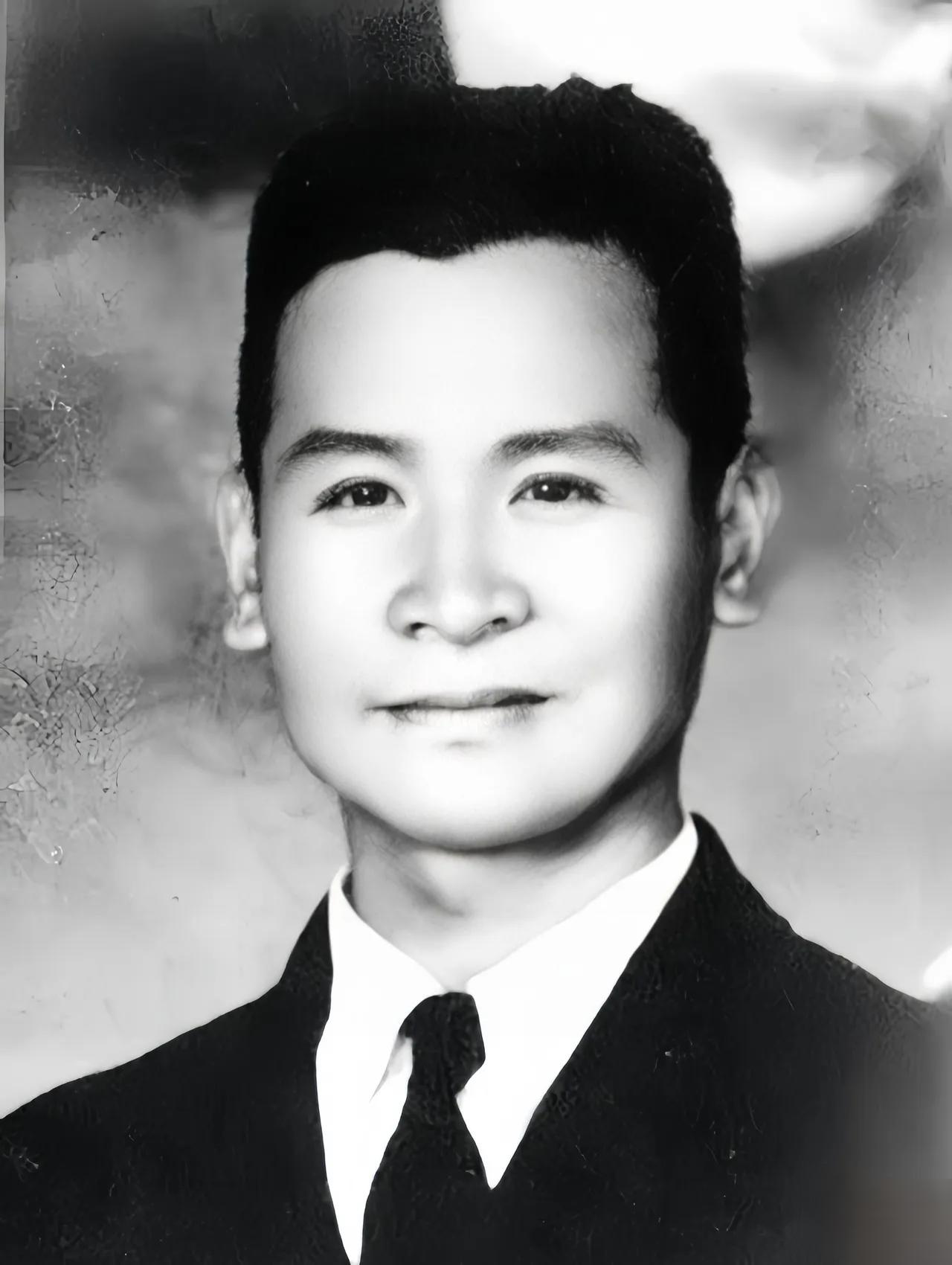1948年,天刚擦黑,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闯进地下党的联络点,额头上全是汗。联络员老陈正要关门,被这人一把抵住门板。男人喘着粗气说:“电台暴露了,特务已经在路上!”老陈没松手,盯着他问:“你谁?”男人急得跺脚:“我是‘山雀’!老刘的上线!赶紧撤,他们要抄窝子!” 老陈的手没松,指节都攥白了。1948年的南京城,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抓人,地下党联络点三个月换了两个,每一次接头都提着脑袋。老刘是联络点的发报员,三天前刚带着电台转移到这里,“山雀”这个代号,老刘只提过一次,说上线是个“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钻缝的人”。 “老刘给你带过什么话?”老陈的声音压得极低,眼神没离开男人的脸。男人抹了把汗,扯下鸭舌帽,露出额角一道浅浅的疤痕:“上个月月圆夜,他说‘秦淮河边的桂花该开了’,要我多备些‘纸张’。”老陈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话是接头暗语,“纸张”指的是密码本,只有他、老刘和“山雀”三人知晓。 后背的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,老陈猛地松开手,指尖还残留着门板的凉意。他没工夫寒暄,转身就往里屋冲,油灯被带起的风晃得直颤,照得墙上映出的人影都跟着发慌。“山雀”也不含糊,紧随其后抄起床底的木箱子,厚重的木板撞得地面“咚”一声响,里面的电台零件相互碰撞,发出细碎的哗啦声。“老刘呢?”老陈一边往密码本上裹油纸,一边头也不抬地问,指腹蹭过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暗号,指尖都在发紧。 “被盯上了!”“山雀”的声音带着喘,额角的疤痕在灯光下更明显,“我送他到巷口,看见三个穿黑大褂的跟着,他故意拐进夫子庙的戏班子,让我先过来报信。”老陈的心沉了沉,夫子庙人多眼杂,老刘想脱身难如登天,但此刻根本容不得他多想——屋外已经传来隐约的皮鞋声,笃笃笃,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 他拽过墙角的旧棉袍套在身上,又把电台箱子塞进装白菜的竹筐,外层铺了层湿漉漉的菜叶,一股青涩的寒气扑面而来。“走后窗,”老陈压低声音,伸手去拔窗闩,木质的闩子被汗水浸得发涩,“巷口王大爷的拉煤车在等,他车板下有夹层。”“山雀”点点头,扛起竹筐就往外挪,脚步放得极轻,却还是能听见竹条摩擦的沙沙声。 刚翻出后窗,就听见前院的门板被踹开的巨响,伴随着特务粗声粗气的呵斥:“开门!查户口!”老陈下意识地按住“山雀”的肩膀,两人贴着墙根蹲下身,巷子里的煤烟味混着夜色,呛得人嗓子发紧。拉煤车的轱辘声由远及近,王大爷佝偻着腰,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梆子戏,看似漫不经心,路过两人身边时,却用袖子悄悄递过来两顶旧毡帽。 “往南走,过了朱雀桥就安全了。”王大爷的声音裹在风声里,轻得像一片落叶。老陈和“山雀”扛起竹筐,混在晚归的行人里慢慢挪动,身后的联络点已经亮起刺眼的手电光,特务的喊叫此起彼伏,吓得路边的狗都在狂吠。“山雀”攥着竹筐的手青筋暴起,老陈能感觉到他在发抖,不是怕,是恨——这南京城的黑夜太漫长,多少同志的鲜血都洒在了这青石板路上。 走到朱雀桥时,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,晨雾中能看见远处秦淮河的水波。老陈停下脚步,回头望了望来时的方向,联络点的方向已经没了动静,不知道老刘是否平安。“山雀”把竹筐放在地上,掀开菜叶摸了摸电台,低声说:“只要设备在,我们就能继续发报。”老陈点点头,指尖划过密码本上“秦淮桂花”的暗语,忽然想起老刘说过,等革命胜利,要一起去赏河边的桂花。 1948年的南京,黑暗还未褪去,但总有人在刀尖上行走,用勇气和信仰点亮微光。那些藏在暗号里的约定,那些隐在夜色中的坚守,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,而是实实在在的牺牲——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,或许只留下一个代号,但正是这些平凡人的挺身而出,才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