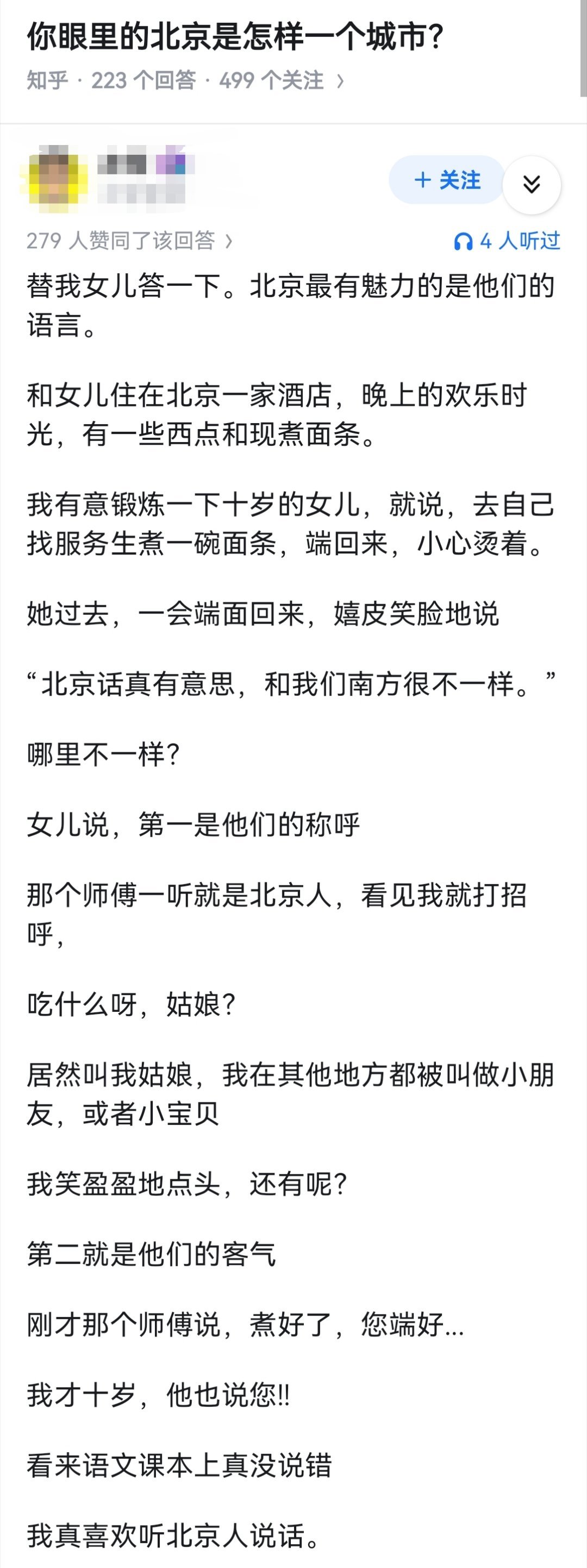1986年7月,晚年病重的邓稼先换上中山装,在病房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,12天后,他永远离开了。 病房窗子半开着,风一阵阵钻进来,吹得床头那张纸起了边。 邓稼先躺着,脸色蜡黄,衣领却还拢得规矩。一九八五年他被确诊直肠癌,住院后动了三次手术,疼痛几乎天天拽着人走。止痛针从一天一针加到一小时一针,身体还出现大面积溶血性出血。人都这样了,他嘴里惦记的还是那句话: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 更让人发愣的是,他的名字在社会上真正“响”起来,竟接近他离世前的那段时间。两弹元勋、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,做事做到了顶尖,却把自己藏得很深,像把门栓插死,外头很难摸到门缝里的光。 这条路并非凭热血硬冲。抗日战争胜利那年,他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,回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当助教。助教干得不久,心里总想再学点更硬的东西。 到了一九四八年,他远赴美国普渡大学学物理。 一九五零年八月拿到博士学位,材料把时间钉得很细,博士学位到手第九天,他就踏上归国的船,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。 回国后日子一度安稳。 一家住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宿舍,妻子许鹿希在北医上班,他常骑自行车去接她。一九五四年女儿邓志典出生,一九五六年儿子邓志平出生。 可这点烟火气,到了后来,只能偶尔掀开一角看看。 一九五八年,他接到一项特殊任务,有人用一句话概括:为国家放个大炮仗。 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,设两个研究室,他任理论研究室主任。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打过比喻,说龙头在二机部,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,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。 绕来绕去,落到邓稼先身上,就是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。 条件苦到什么程度,材料没卖惨,直接把工具摊开:电子管计算机、手摇计算机、计算尺,算盘也得顶上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早轮廓,就在一遍遍计算里磨出来。 一九六二年底,他领导起草第一颗原子弹理论方案,还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;他常往实验现场钻,跟实验人员对着方案和测试结果反复推敲,盯着理论部把预估和分析做扎实。 两年后,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整,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巨响炸开,强光一闪,蘑菇云冲天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“东方巨响”震了世界。没来得及歇,他又扎进氢弹研究。 三年不到,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 保密把人和家隔开得厉害。三十四岁那年,他回家对许鹿希说要调动工作,明天就走。妻子追问去哪、做什么、做多久,他只回“不能说”。 后来外头有人说他与妻子分开二十八年,电话不通、信不写。材料把这说法往回拽了拽:隐姓埋名不等于断亲。只要回北京开会或被中央领导召见,他会和家人团聚;他亲手料理父母后事;前后花三个月辅导儿女参加高考;星期天还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饭。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,他因工作在北京待了三个月,亲自辅导孩子。 教科书买不到,岳母劳君展送来一本自己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。劳君展曾在法国勤工俭学,还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过。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说教材好。同事兼邻居于敏也在身边,孩子遇到疑难更爱去问于敏,觉得讲得深入浅出。 几个月苦战,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姐姐学医,弟弟学工。 他并不冷硬。许进看他,觉得姑父爱买书、爱看电影,游泳、乒乓都来,京剧更是心头好。看戏常临时起意,买不到票就去门口“钓票”,举着钱用京腔问有富余票吗;下馆子等座也有小窍门,盯哪桌菜快上齐,守在那桌后头,不慌不忙。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,他在北京去世,享年六十二岁。 更扎眼的是数字,他作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总负责人,国家奖金合计二十元,原子弹十元,氢弹十元。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六年这二十八年,我国共进行三十二次核试验,其中十五次由他亲自指挥,全部成功。 他走后,许鹿希仍住在北太平庄那栋普通平顶式住宅楼里,水泥地面、白灰墙,两张布沙发、写字台、小书橱,陈设简单得像没换过季。 墙上贴着没装裱的七个字“两弹元勋邓稼先”,张爱萍手迹;小镜框里的半侧遗像斜靠书橱顶上。 许鹿希受访时说得很淡,却很硬: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,他该被准确表达,她不能容忍吹捧。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,中国政府发表声明,当天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,次日起暂停核试验。一个多月后,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。 同一天正是他去世十周年纪念日。 病房那股风还在记忆里转,纸边起着角,像有人轻轻按住,又松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