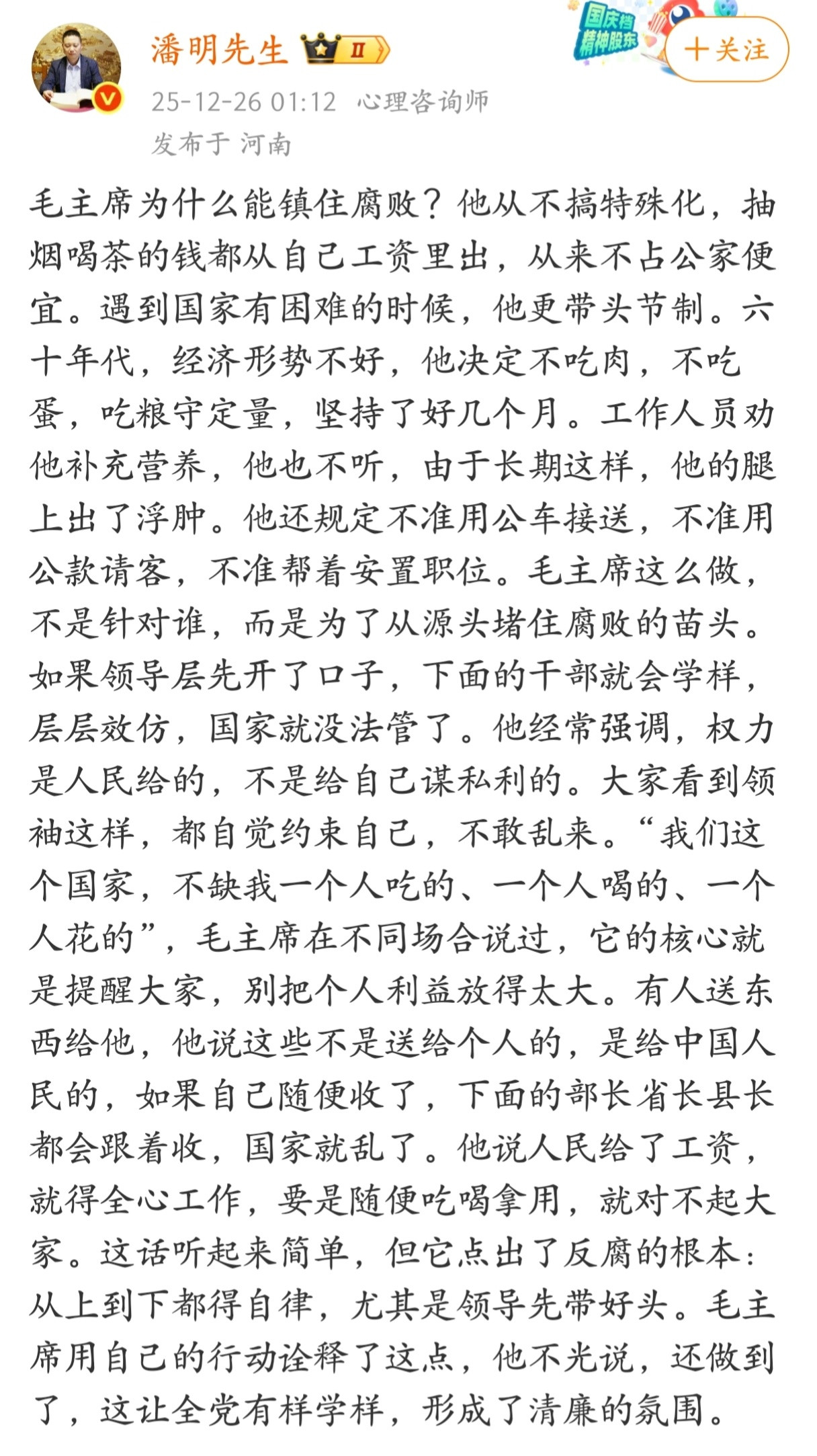毛主席的五大遗憾: 第一:双亲去世时未能陪伴身边; 第二,台湾没有解放。 第三,青藏铁路未能通车; 第四,未能实现骑马走江河的愿望; 第五,接班人选择的波折。 先说第一个,双亲去世时未能陪伴身边; 一九一九年那次“来晚了”,成了毛主席一辈子最软也最疼的地方。 母亲文七妹,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生在湘乡大坪唐家圫,原名文素勤,后改名文其美,在同族姐妹里排第七,乡亲都叫她“七妹”。她十八岁嫁到韶山冲,丈夫毛顺生是个小农,几亩薄地,家里一群人吃饭,全指着她的辛苦:天没亮起火,天黑了还在水边洗衣,屋里屋外一刻停不下手。 婚后她生了七个孩子,五男二女,有四个没活过襁褓。 白布一次次盖上小小的身子,她这个娘心里早就发虚。 到了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出生,她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压在这个伢子身上。 让他拜七舅妈做干娘,又上南岳向观音许愿,说孩子长大成人必来还愿,还领着他拜“石观音”为干娘,从此家里多了个“小名”叫“石三伢子”,自己吃起“观音斋”。在外人眼里这是“迷信门道”,在她心里,是能抓住的护身符。 文七妹没念多少书,对人却有自家尺度。 性子软,看不得穷人挨饿,经常背着丈夫接济乡亲。毛泽东六岁到私塾读书,有一阵子每天带走的午饭多了,回家却总喊饿,她追问几句,才知道学堂里新来了个叫“黑皮伢子”的同学,中午没饭吃,他把自己的饭对半分了。 对紧日子的农户来说,这样做是“亏本”;在她看来,这是值得偷着高兴的事。 毛顺生不认这一套,觉得“损己利人”不划算,为此夫妻俩吵过不少回。 后来毛泽东跟斯诺回忆,说家里像有两“党”:父亲是“执政党”,母亲、弟弟和他是“反对党”,有时连雇工也站到“反对党”那头。 话听着轻巧,意思却不轻:一边主张多替别人想,一边主张多替自家算,这种拉扯,在孩子心里早给各自排了队。 一九一八年夏天,他准备从长沙北上北京,听说母亲在外婆家养病,托人请医生开方寄给舅父。 一九一九年,母亲淋巴腺发病,他已在湖南一师任教,赶回韶山,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,住在河西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,亲自端汤递药。 那张全家去照相馆拍的合影,就是这次治病时留下的,也是她一生唯一一张照片。 十月,长沙正闹“驱张运动”,他忙得脚不沾地,突然收到家信,说母亲病危。 他连夜带着弟弟毛泽覃往韶山赶,等跨进家门,棺材盖已经合上两天。大哥毛泽民说,母亲临终前嘴里还一直喊着儿子的名字。人还在路上,亲人已经入棺,这点时间差,从此成了心里的死结。 守灵的几夜,他坐在灵前,对着昏黄油灯写下《祭母文》,又写了两副灵联。 文里记下母亲五十三岁去世,“生有七子,七子余三”,一条条写她待人“博爱”、行事整饬、不说诳话、不存欺心,也写到“有志未伸,有求不获”,一辈子操劳,带着遗憾离开。 没多久,他在写给同学邹蕴真的信里,把人分成三种:损人利己的,利己而不损人的,可以损己利人的,说自己的母亲属于第三种。 一九三六年,他在延安对斯诺谈起母亲,仍旧那句评价:心地善良,为人慷慨厚道,随时想接济别人,可怜穷人。前后十几年,口气没变,这种不变,本身就是一份纪念。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,毛主席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。 二十多年前,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回乡考察农民运动,站在毛震公祠前夸农会“好得很”,高呼“农会万岁”,还对乡亲说:“三十年后革命不成功,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。”这一回回来,革命早已成功,父母却在山坡上睡了四十年。 第二天清晨,他走上故居对面的楠竹圫山坡,到父母合葬的坟前拜谒。 随行人员毫无准备,就近折了几枝松叶递给他,他接过来,轻轻放在坟前,深深鞠躬三次,伫立很久,只缓缓说了句:“前人辛苦,后人幸福。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一句熟悉的名言,在这里带上了给父母回话的味道。 下山之后,他回到上屋场,在父母生前住过的屋子里站了好一会儿,对着墙上的照片轻声喊:“母亲,您的儿子回来了。” 转头他跟身边人感叹,父亲那时得的是伤寒,母亲颈上长了个包,“穿了一个眼”,只因为那时候医术不发达,要是现在,两个人都不会死。 话说得平平,却藏不住心里的遗憾。 回到松山住所,他对罗瑞卿说,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,不信鬼神,“生我者父母,教我者党”,这两头都要承认,下次再回韶山,还要去看看父母。 几句话,把亲情、信仰和欠下的心愿拴在了一块。 五大遗憾里,关于双亲这一条看着“私事”,在他心里,却一直压着。 韶山楠竹圫山坡上的风一年年吹,吹过刻着《祭母文》的石碑,也吹过新中国那些没赶上的事。 一个把一生交给天下的人,心里始终给父母留着一块座位,那块座位上,静静放着的,就是这种说不出口、又忘不掉的遗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