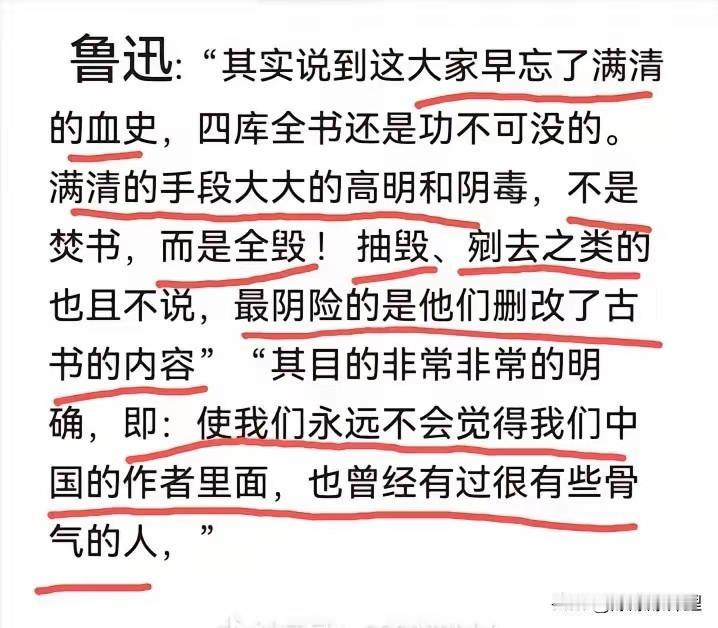1922年,闻一多回家结婚,因嫌弃妻子没读过书,大婚当日,他不洗澡不换衣、不迎接新娘,也不入洞房。 谁知不久后,他却给妻子写信:我的心肝,我想你想得要死…… 这场婚礼像出拧巴的戏,闻一多躲在书房里,任凭家人在外喊破喉咙,就是不肯换上那身红绸马褂。 他刚从清华毕业,满脑子都是“自由恋爱”“妇女解放”,眼前这场父母定下的婚事,在他看来就是旧时代的裹脚布。 可爹妈堵在门口抹眼泪,说他不娶,高家姑娘的名声就全毁了,最后还是被两个堂兄架着,才算完成了拜堂仪式。 新婚夜的煤油灯亮到天明,闻一多在书房啃冷馒头,隔壁房间的高孝贞没合眼。 她知道丈夫嫌弃自己,可第二天见着公婆,还是替他打圆场:“他读书太累,喝了点酒就睡着了。”后来闻一多在日记里写:“她替我撒谎的时候,手都在抖,我却连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口。” 这桩婚事早在十年前就埋下伏笔,13岁的闻一多刚考上清华,爹妈就跟同乡高家换了庚帖。 他写信反抗,说“男女平等,婚姻自主”,爹回信就四个字:“孝道大如天”。 留美预备学校的五年,他读易卜生,写白话诗,以为能挣脱这枷锁。 直到1922年夏天,家里拍来电报:“母病,速归完婚”,他揣着一肚子火回去,才发现母亲好好的,就等他点头。 真正的转变是在婚后第三个月,闻一多偶然翻到高孝贞藏在枕头下的识字本,歪歪扭扭写着“一多”两个字。 他突然想起自己在清华演讲时说的“妇女要解放”,脸一下子红了。 第二天他跟爹妈说:“送孝贞去武昌女校读书吧,她该有自己的日子。”爹妈骂他疯了,他却铁了心,亲自送她去报了名。 高孝贞上学后像换了个人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课文,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,手指头冻得通红也不吭声。 半年后她给闻一多写信,居然用了白话:“今天先生讲《木兰辞》,说女子也能上战场,我想起你说的‘独立’,原来不是空话。”闻一多拿着信笑了半天,回信里第一次叫她“贞妹”。 那时候鲁迅刚跟朱安分居,郭沫若娶了张琼华五天就跑了,我觉得闻一多的不同在于,他没把包办婚姻当成不可解的死结,反而从自己身上找答案。 他教高孝贞读《诗经》,她陪他改诗集,两个人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半夜。 留美那三年,他写了73封家书,有42封开头都是“吾爱贞妹”。 1937年抗战爆发,闻一多带着一家老小往西南联大跑,高孝贞把嫁妆里的金镯子卖了,换了粮食和车票。 在云南乡下,她踩着泥路去买菜,回来还能跟闻一多讨论《楚辞》的韵脚。 有学生去家里拜访,看见他们共用一张书桌,台灯下两个脑袋凑在一起改稿子,活像两个同学。 闻一多后来在课堂上说:“爱不是找个完美的人,是跟一个人一起变完美。”这话像在说诗,又像在说他自己。 当年那个躲在书房抗拒包办婚姻的青年,最后把“父母之命”过成了“琴瑟和鸣”。 高孝贞晚年回忆,说闻一多最常跟孩子讲:“你妈才是我最好的老师,教我怎么把责任过成日子。”书房里那盏煤油灯,后来一直摆在他们家最显眼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