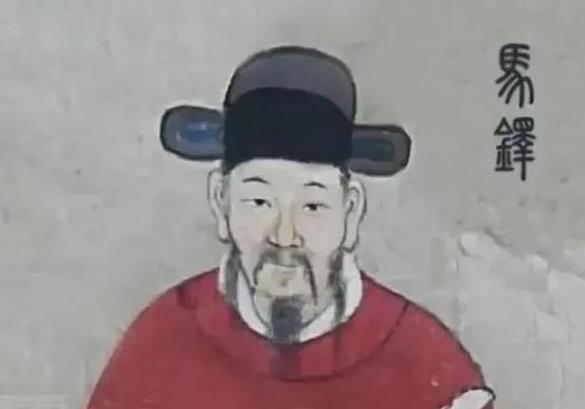[微风]1411年春,马铎在进京赶考的路上,看到有一个女子的尸体在路边暴晒,他于心不忍,脱下长衫盖在了女尸身上并且将女尸挪到一旁安葬,谁知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 永乐九年,福建长乐的雨似乎就没停过,把进京的官道浇得泥泞不堪,对于四十五岁的马铎来说,这已经不知道是他第几次踏上赶考的路途了,只是这一次脚步格外沉重。 邻里凑出的盘缠沉甸甸地压在心口,而离家时母亲借债得来的十两银子,伴着那句“这趟若还不中,就回来种地”的最后通牒,让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 走至建宁府郊外,湿冷的空气里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臭味,马铎凑近一看,竟是一具遭人遗弃的女尸,青衣已随风化得破烂,尸身就这样赤条条地暴晒在天光之下。 常人遇此多半会掩鼻疾走,生怕沾了晦气,可马铎愣是在原地站了半晌,想起自己年近半百却功名未立,这孤魂野鬼无人收殓的凄凉,竟像镜子一般照进了他此时狼狈的心境。 心头一软,马铎做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举动,他解下了身上唯一的长衫——那可是他预备到了京城体面见人的行头。 细软的布料盖住了女尸的青白身躯,随后他不顾读书人的斯文,直接跪在泥地里,徒手在槐树下挖了起来,足足掘了三尺有余,才小心翼翼地将人安放进去。 又折了一根刚抽芽的柳枝插在新翻的土包上算是立碑,马铎躬身一拜,低声喃喃:“姑娘莫怪,仓促间只能这般委屈你。若有来世,盼你别再受这份孤苦,投个好人家去吧。” 那一刻,他并未发觉自己系在腰间的钱袋不慎滑落也埋进了土里,没了长衫御寒,他只能裹紧满是补丁的短褂,迎着渐晚的凉风继续向前。 待到抵达京城客栈的那晚,因囊中羞涩连盏灯油都舍不得点,马铎裹着薄被迷糊入睡,恍惚间,眼前不再是逼仄的客房,而是一间幽静的茅舍。 那个面色如纸却眉眼温婉的女子正在炉前煮茶,炉火明明灭灭,她口中却念着些奇怪的句子, 那女子并不提报恩二字,只是在那水汽氤氲中轻吟:“寒夜多蒙到妾家,炉中无火未烹茶。” 紧接着,她抬头深深看了一眼马铎,语调变得郑重,似在提点又似谶语:“郎君此去登金榜,雨打无声鼓子花。” 与此同时,更离奇的声音在梦境边缘回荡,像是一位老妇在耳边絮叨什么“青鞋绣菊”的上联,又夹杂着关于“问政安民”的严肃论述,要他谨记太宗贞观之治的宽仁典故。 次日醒来,梦境竟清晰得如刻在脑中,尽管腹中饥饿难耐,马铎还是鬼使神差地将那几句诗文与治国之策在心中反复咀嚼。 转眼殿试大开,永乐皇帝朱棣端坐龙椅,威仪赫赫,那年的考题出得极为刁钻,既考学问更考急智,这不仅仅是笔墨文章的较量,更是一场关于才情与胆识的博弈。 由于备取考生的身份有些特殊,加上没了体面长衫,马铎在一众衣冠楚楚的举子中显得格外寒酸。 福建同乡林志,此时正是风头无两的夺魁热门,早已对状元之位势在必得,谁知永乐帝并未按常理出牌,反倒饶有兴致地指着手中折扇,随口抛出一联:“白扇画梅,日日迎风花不动。” 这一瞬间,朝堂寂静,有人冷汗直流,有人搜索枯肠,唯独马铎脑中灵光一炸,梦中老妇的那句低语脱口而出:“青鞋绣菊,朝朝踢露蕊难开。” 工整且意境相衬,引得永乐帝眉梢一挑,皇帝来了兴致,目光扫向殿外的铃儿草,又出一题:“风吹不响铃儿草。” 这简直是为马铎量身定做的局,他毫不迟疑,昨夜那女子如同咒语般的诗句响彻大殿:“雨打无声鼓子花。” 不仅是对仗工整,随后在策论环节,当问及“安民”之策时,马铎更是将梦中所得与平日里的切肤之痛相融,引经据典谈及轻徭薄赋与百姓疾苦,每一句都戳中永乐帝对于“仁政”的期许。 林志虽才高八斗,言辞犀利如刀,但在马铎这种如有神助的从容面前,终究还是乱了阵脚,尤其在看到马铎将那段灵异奇遇挥洒成文,卷首那句“清明有雨,行人掩孤魂”更是凄美绝伦。 最终,金口玉言,马铎高中状元,当永乐帝询问何以得此奇句时,马铎不敢隐瞒,跪陈荒郊埋骨一事。 皇帝听罢,感叹此人不仅才高,更是心诚意坚的吉人,不仅赐了进士及第,更授翰林修撰,然而,真正传奇的并非这一时的荣耀,而是马铎之后的人生。 这位于穷困中走出的状元公,一生都践行着“民本”二字,任国子监祭酒时,他力主减免寒门学子的费用,常言“十年寒窗一纸卷,不如荒丘一抔土”,告诫后生为官先为德。 家族之中,母亲改嫁李家,后来异父弟李骐也中了状元,面对世俗对“一门两姓状元”的宗法争议,早已看透生死的马铎大度上书,称“父母无前后,兄弟各有缘”,不仅让母亲归宗李氏,更是主动划清了墓地界限,成全了李家的体面。 晚年的马铎淡出了朝堂的喧嚣,回到福建后,他没有再去探寻什么鬼神之说,只是挑来了石灰和石块,亲手在那坟前立了一块像样的碑,碑上只刻了一句那是他一生命运转折的谶语:“雨打无声鼓子花。” 信源:《裨史类编》卷二十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