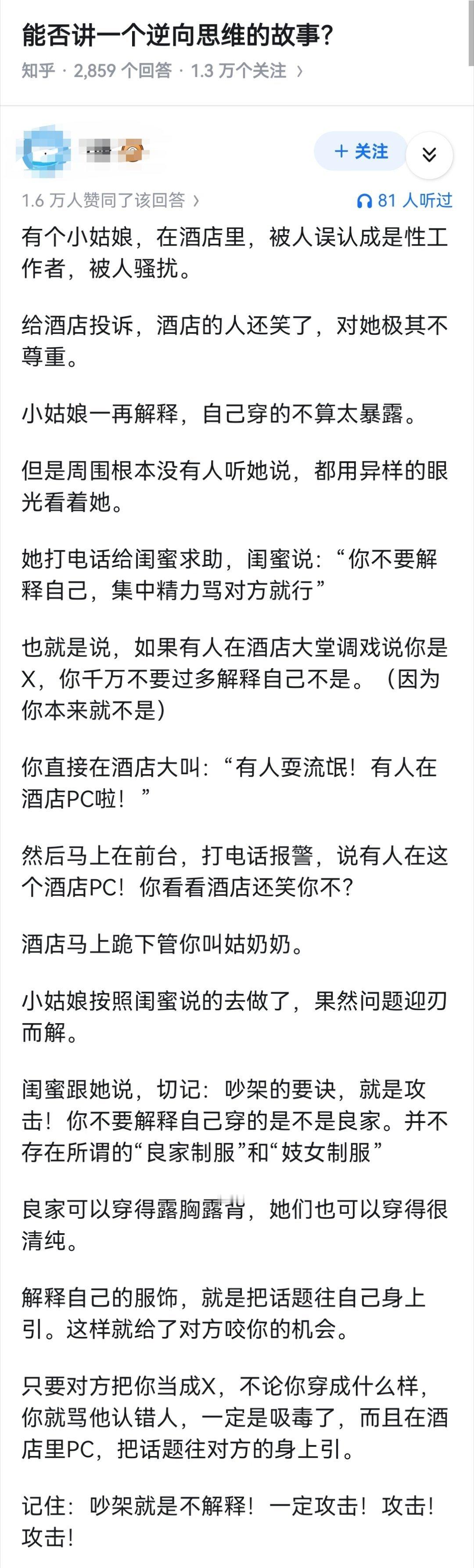1960年,北大才女王承书狠心抛弃丈夫和孩子后不辞而别,从此音信全无。17年后,当满头白发她出现时,孩子们愣住了,随后悲痛大哭:“母亲,您受苦了,您是我们的骄傲!” 1912年,上海一户书香人家添了个女儿,取名王承书。父亲是留学归来的进士,母亲出自扬州何园,家里满柜子中外典籍。 别人家小姑娘玩布娃娃,她最爱钻到书架底下翻书,对数学、物理格外上心。四岁半进私塾,后来考进贝满女中,再到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,成了全班唯一的女生。 在那个“女子学理工”都稀罕的年代,她从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。白天泡在教室和实验室,晚上抱着参考书熬夜啃。 1934年,她以全系第一毕业,拿到象征最高荣誉的斐托斐金钥匙奖,又继续念硕士,1936年拿到学位留校当助教。 战火燃起,她和师生们背着资料,一路从北平辗转南京、武昌、桂林、贵阳,最后落脚昆明的西南联大。别人抢行李,她死死护着那几箱资料。 1939年,她和同样痴迷物理的张文裕成婚,两人最大的浪漫,就是在昏黄灯下推公式、聊问题。 1941年,她争取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奖学金。学校有“不收已婚女学生”的老规矩,她凭成绩和推荐信硬生生闯过关,拜在乔治·乌伦贝克门下,专攻气体分子运动论。 1944年,她拿到博士学位,提出“王承书–乌伦贝克方程”,在国际物理界崭露头角,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,看上去一切光鲜而安稳。 可她心里始终惦记着远方那个满目疮痍的国家。1949年前后,她悄悄把多年搜集的书刊拆成三百多包寄回北京。 1956年,她和丈夫带着一箱箱资料回国,进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,在北大上课,不久又调入原子能研究所,投身热核聚变理论研究。 1959年,她到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三个月,回国路上就在火车上翻译聚变专著。紧接着,中苏关系急转直下,专家撤走、图纸带走,中国的核事业被硬生生掐住咽喉。 1960年前后,钱三强来找她,说得很直接:国家要搞高浓铀,苏联人走了,只能靠自己。 她明白,这意味着要离开北京、离开课堂和公开的实验室,更要离开丈夫和孩子;从此之后,她的名字不会再出现在论文和报道里,去向成谜。 那晚,她写下一封很短的信,只说要出远门,让家人保重,没提“原子弹”“铀浓缩”这些字眼。信压在桌角,她提起简单行李轻声关门,等丈夫和孩子看到信时,她已经在驶向西北的路上。 最终,她在戈壁深处的504厂安顿下来。眼前是黄沙、碎石和刺骨的西北风,住的是土坯房,实验室设备简陋,计算全靠纸笔。她带着一群年轻人,从零开始啃气体扩散法,用六氟化铀一点点分离铀235和铀238。 一场沙尘暴突然袭来,黄土灌进厂房,她第一反应不是躲,而是扑过去护住那摞算满公式的记录本,让沙粒在脸上划出血印。 风停了,她拍拍身上的土,又坐回桌前接着算。她对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咱们吃这点苦,是为了以后不再看别人脸色。” 无数次反复实验、调试,1964年1月14日,气体扩散厂终于产出第一批高浓铀,比计划提前,为当年10月16日的那朵蘑菇云,送上了关键燃料。那天,她在戈壁某个角落仰头望向远方耀眼的光团,没有多说一句话。 这一走,就是17年。家里只有一张她早年的黑白照片,丈夫独自把孩子们拉扯大,逢年过节只能对着照片说想念。她那边,守着实验线和管道,把所有情绪都压进厚厚的演算纸堆里。 1977年冬天,她头发已白了一半,悄悄站在北京家门口。门开的一瞬间,孩子们愣住了,眼前这位瘦削的老人,与记忆中那个年轻母亲已经难以重叠。 认出她的那一刻,哭声一齐涌出。她伸出微微发抖的手,把孩子们一一搂进怀里,只一遍遍说:“妈回来了。” 任务逐步解密后,她把能讲的那一段经历,缓缓说给家人听。后来,她没有选择功成身退,又投入到新一代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中,带着年轻人啃离心、激光分离这些新课题。生活里,她依旧简朴,把积蓄捐给希望工程,说“教育好了,这个民族才有明天”。 1994年,她在北京安静离世,把遗体留给医学,把书和资料留给后人。很久以后,人们才一点点拼出她生命的轮廓:从燕京课堂上的公式,到戈壁深处的管线,再到她悄无声息的背影。 她并非生来披甲的英雄,只是那个年代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在“国家需要”四个字面前,她悄悄放下了个人、家庭和名声,用一生完成了自己最朴素的心愿——为国家鞠躬尽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