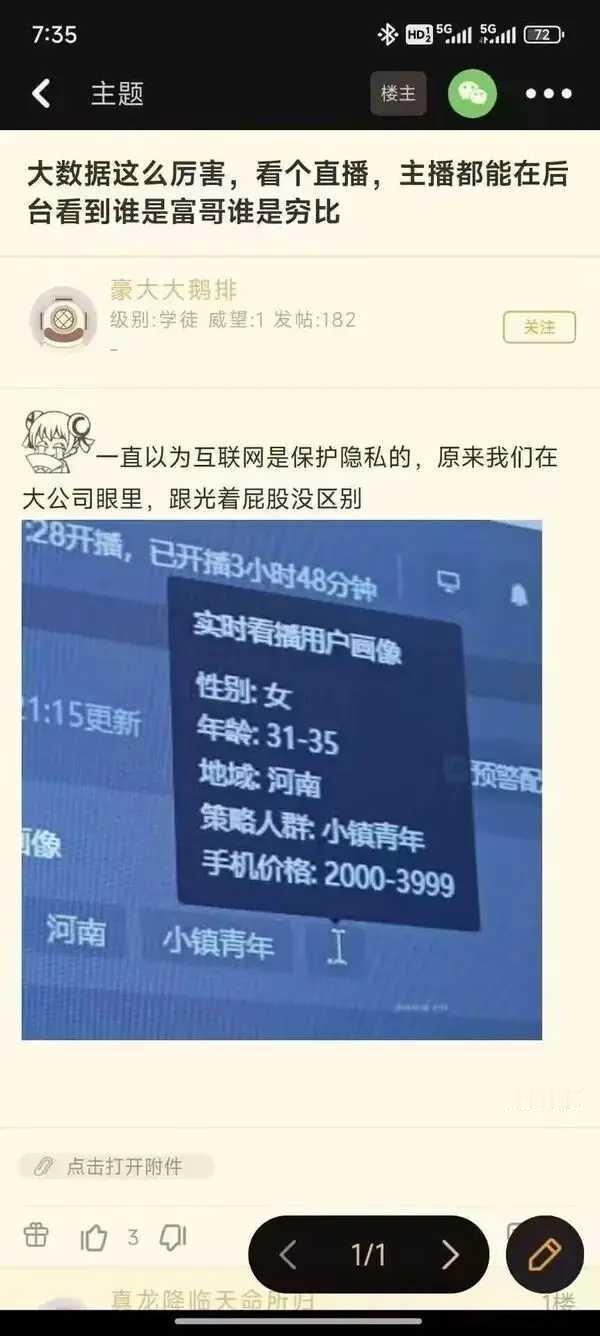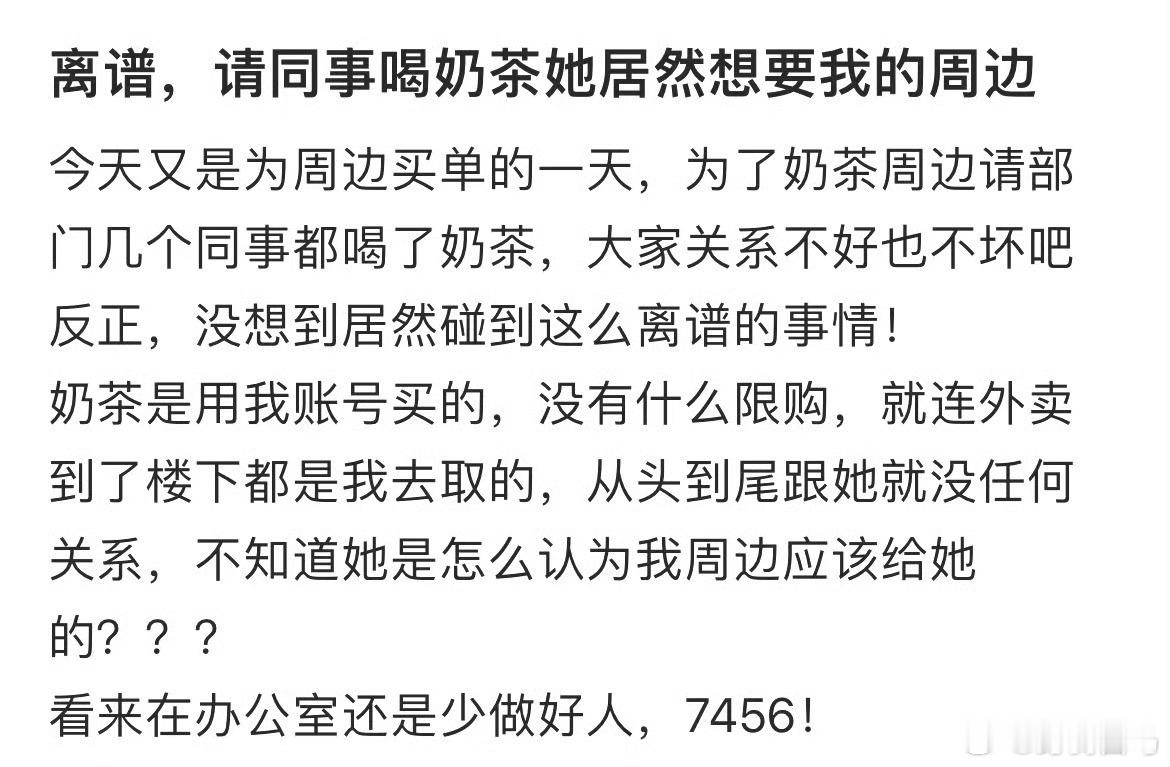大伯家有钱有势,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,我一个都没接。倒不是故意怄气,是真怕他开口——上个月家族聚餐,他坐在主位上,晃着酒杯说要给我安排进他朋友的公司当主管,“月薪两万,朝九晚五,比你现在跑销售强十倍”。我当时笑着婉拒, 裤兜里的手机震第三下时,我正蹲在路边啃包子,辣椒油溅到了白衬衫袖口。屏幕上“大伯”两个字亮得刺眼,像极了上个月家族聚餐时,他腕上那块闪着光的金表。 大伯家是真的体面。堂哥毕业就进了他安排的国企,表姐嫁的人是他生意伙伴的儿子,连我妈都常说“你大伯一句话,顶你跑半年销售”。可我总觉得,那种“体面”像裹着糖衣的药片,甜是甜,咽下去未必舒服。 上个月的包间里,水晶灯的光落在他油亮的发顶上,酒液在玻璃杯里晃出细碎的光,旁边堂哥夹菜的筷子顿了顿,我妈偷偷在桌子底下踩了我一脚——他刚说完“主管位置给你留着,明天就让人事联系你”,满桌的目光都聚过来,像探照灯似的。 我当时笑得脸都僵了,端起茶杯碰他酒杯:“大伯,我现在的工作刚有点起色,上个月还签了个大单呢。”声音发飘,连自己都听出底气不足。他“嗤”了声,没再逼我,只是把酒杯往桌上一放,杯底和桌面碰撞的脆响,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 其实我哪是有起色?上周为了跟一个客户,在暴雨里站了四十分钟,鞋子全湿透,回到出租屋发现热水器又坏了;昨天月底冲业绩,熬夜改方案到三点,打印机还卡纸,急得差点哭出来。这些事,跟大伯的“月薪两万”比,确实像他说的“不值一提”。 可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接电话? 裤兜里的手机终于安静了。我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,有点噎。想起签单那天,客户拍着我肩膀说“小伙子靠谱”,想起工资到账时给我妈转了五千,她发来语音里带着哭腔的“我儿子长大了”——这些瞬间,像散落在路边的小石子,硌脚,却实实在在踩着地。 也许大伯是真的为我好,像他说的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”;也许他只是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“罩着”晚辈,就像小时候他总给我塞红包,说“拿着,大伯有钱”。但我怕的不是钱,是那份“罩着”背后的沉甸甸——怕有一天在公司受了委屈,不敢辞职,因为“这是大伯安排的”;怕过年回家,亲戚们围着问“大伯给的工作怎么样”,我得笑着说“挺好的”,哪怕心里堵得慌。 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,我看到大伯的头像,还是去年春节拍的全家福,他站在最中间,笑得一脸威严。我摸出手机,点开对话框,手指悬在输入框上半天,只打出“大伯,刚在忙,没看到电话”。 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,风卷着落叶从我脚边跑过。袖口的辣椒油渍像朵难看的花,可我突然觉得,比起那件熨帖平整、却可能永远带着“大伯给的”标签的衬衫,这件溅了油的白衬衫,好像更适合现在的我——有点脏,有点皱,却裹着一颗还在跳的、自己的心脏。
两天,一个连,最后只剩下11个人。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?这支部队的祖上,是在
【18评论】【8点赞】